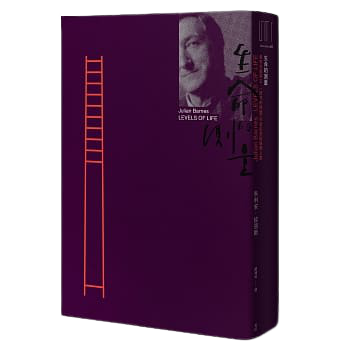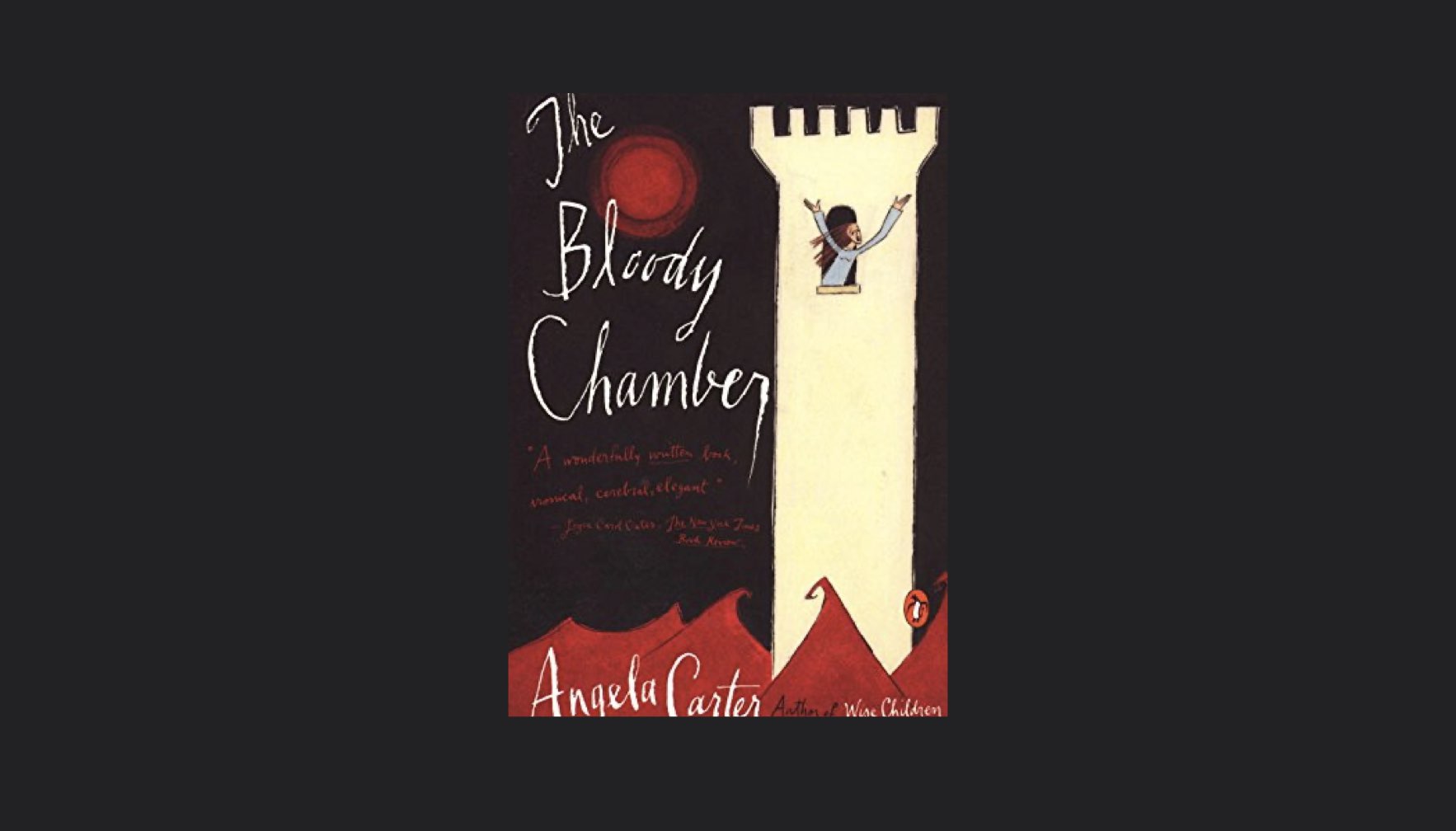朱利安.拔恩斯(Julian Barnes)是享譽英語文壇的名家,曾三度入圍布克獎,終於第四度以《回憶的餘燼》(The Sense of An Ending)奪冠,據說當年評審團只用了三十分鐘就無異議決定,將當年已更名為「曼布克獎」的榮譽頒給了拔恩斯這本「薄薄的」小說。
拔恩斯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充滿後現代風的小說崛起文壇,國內中譯本已絕版的布克獎入圍之作《福婁拜的鸚鵡》(Flaubert’s Parrot)最可做為這時期的代表。
據說大文豪福婁拜在書寫他經典之作《簡單的心》時,為了細節描繪更栩栩如生,案頭果真放了一隻鸚鵡時時觀察。拔恩斯以此為發想,描寫一位退休醫生竟然發現不只一間博物館宣稱當年那隻鸚鵡已做成標本成為館藏。接下來主人翁從尋找鸚鵡身世轉而揭開了不同版本的福婁拜生平。
這本小說的敘事虛實夾雜,三條主線彼此對照呼應。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文學史上功成名就的福樓拜,另一方面我們也驚訝發現,文豪一生被病痛折磨,飽受無愛喪親之痛,也曾潦倒挫敗……等等這些不為人知的一面。小說中第三條線則是福婁拜本人的手扎書信。拔恩斯利用反傳統的敘事法向讀者提問:要如何認識真正的福婁拜?他的一生究竟是快樂還是悲傷的?甚至,凡人如你我,又如何體認自己的人生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
拔恩斯的作品總是充滿著深思熟慮,觀察敏銳,文字簡潔準確,但探索的主題卻經常帶著憂鬱的哲學式命題。讓他獲得曼布克獎的《回憶的餘燼》,看似回歸了比較寫實的敘事,但對人生的偶然與巧合,記憶的不準確與感情的不可測,仍是充滿了他一貫的主題層疊交錯。
故事描述一退休老翁突然接到一封律師通知,他大學時期的女友母親,三十多年前曾短暫有過一面之緣,卻在遺囑中留給他一份意外的遺物,是他自殺過世的高中死黨的日記。高中死黨後來曾一度與她的前女友交往,讓主人翁非常妒恨,也因此兩人斷了聯絡。但這本日記為何會又出現?經過歲月的洗禮,我們真能說得出哪些記憶真正改變了我們的人生?哪些記憶其實是為了趨吉避凶而被改寫?
這本《回憶的餘燼》以短短的篇幅,卻承載了異常沉重深刻的主題,冷靜優美的文字如滴水穿石般沁入讀者心扉,感人力道還遠勝許多洋洋灑灑數十萬字的小說,是小說形式的完美展現,更是拔恩斯晚年後的另一個藝術高峰。

在介紹拔恩斯的這本新作《生命的測量》之前,先回顧了《福婁拜的鸚鵡》與《回憶的餘燼》,目的就是讓讀者認識拔恩斯是個什麼樣的作家。
不同於許多作家的文字充滿了賣弄與表演性,喜歡語不驚人死不休,拔恩斯的作品總是節制而意在言外,用文學創作對人生扣問,卻從不顯得耽溺或自我重覆。而且,他總是能夠發揮了文學最純粹的力量,並不張牙舞爪先設定了議題,而是藉著文字的迂迴交疊折射,呈現出生命種種更幽微的面向。
《生命的測量》的英文書名 Levels of Life,生命中的層層疊疊,似乎就是他小說作品的最佳形容。然而,這回他寫的不是小說,而是他親身經歷的悲慟,關於結縭三十年的愛妻無預警離世的無盡哀傷。
曾經,閱讀《回憶的餘燼》對我是一次救贖,拔恩斯測量回憶的書寫引導我,讓我對自己的生命有了另一種回顧的眼光,體會到悲傷是一種出口,經過真正面對悲傷才能與自己和解。然而,儘管當時我對拔恩斯何其準確的文字感到驚異,我並不知道這本二〇一一年的作品,其實是寫在他二〇〇八年喪妻之後。
直到讀到這本《生命的測量》,我才瞭解拔恩斯為何會寫出《回憶的餘燼》,又為何等待了七年,他才終於在作品中首度直接面對了老年喪偶的悲慟。
因為拔恩斯是個思考型的作家,他必須與自己和解,與死亡和解。雖然這份傷慟對他而言永遠不會消失,但是他卻因為這份傷慟讓他重新看見生命的面貌,甚至是,文學的療癒力量。

將兩個從未結合過的事物結合在一起。世界就此改變。當下或許無人發現,但無所謂。世界終究是改變了。
就從這幾句話開始,拔恩斯拉開了一個以高度為座標的生命圖像。
就如同《福婁拜的鸚鵡》的拼貼方式,三段故事分別以天空、水平面、地底為隱喻,一段是半紀錄式的報導文學,一段是以真人為本的虛構,一段是作者自傳性散文。
第一章「高度之罪」,上場的都是十九世紀的真實人物,皇家騎兵隊的伯納比上校、知名女演員莎拉.伯恩哈特、以及發明高空攝影技術的納達爾,熱中於熱汽球升空飛行是三人的共同點。飛行是人類的夢想,高度某種程度滿足了人類對自由冒險的本能渴望。熱汽球、飛行、攝影、還有納達爾與久病的妻子攜手五十五個年頭,這些事情有何關聯?讀者必須耐心玩味拔恩斯所安排的這些線索,一步步體會拔恩斯對悲傷的深刻認知。
第一章結束在高空攝影發展的極至,那就是從外太空拍到了地球的面貌。一九六八年阿波羅八號負責駕駛登月小艇的安德斯少將事後回憶:「相較於非常粗糙、凹凸不平、破敗、甚至於無趣的月球表面,我們的地球相當多采多姿、美麗又細緻。我們每個人都驚覺到我們越過二十四萬里路來看月球,其實值得看的是月球。」
人類尋尋覓覓,挑戰實驗創新,以突破高度作為追尋夢想的指標,真正換得了幸福快樂嗎?
於是拔恩斯帶著我們從高空回到地面。
第二章「平平實實」,On the Level,也可做「在地面」、或「同一高度」解。拔恩斯虛構了伯納比上校與女演員莎拉.伯恩哈特之間一段無疾而終卻讓伯納比刻苦銘心的愛情。熱戀也像登上熱汽球高飛,也同樣是「將兩個從未結合過的事物結合在一起」,但就像熱汽球有墜地意外的危險,愛情也同樣隱藏著悲劇的可能。女演員宣稱自己不相信婚姻,不願回到地面與上校「同一高度」,但後來卻閃電下嫁他人,空留遺憾的伯納比則在一次戰役中被敵人以長矛穿頸而亡。
所有的愛情,到頭來都是悲傷的故事。

從報導文學、虛構小說、轉進第三章「深度的迷失」(The Loss of Depth),拔恩斯開始娓娓到來他的喪妻之慟。
與他牽手三十年的愛妻,從診斷到死亡只有三十七天,我們才明瞭拔恩斯多麼羨慕在第一章出現的納達爾,與妻子五十五年廝守,並有八年的時間因愛妻久病他們隱居相伴,納達爾能有溫柔照顧侍病的機會。
從痛不欲生曾一度計劃自我了斷(後來自殺成為《回憶的餘燼》中重要的情節),到接受你愛一個人有多深有多長,失去對方後的悲傷也同樣深同樣長,拔恩斯如手握手術刀般,一層層剖切進傷慟的更底層。
人生至此,從年輕的好高騖遠,到有幸與某人一路同行,到其中一位葬身六呎之下,這是人生的階段,也是對生命三種不同層次的體會。在悲傷中,我們也隨著記憶下沉,沉到記憶底處,直到以前快樂時光的攝影留念,「似乎變得比較不像原版,比較不像生活照的本身,而像是照片的照片。」
如果攝影都是不精確的,那麼「我」又該如何記憶?拔恩斯或許已經提供了答案:在文字裡。
他最終記得的,不光是自己的故事,而是幫我們每一個人記住了愛與痛苦、升空與墜地、哀悼與孤獨。他寫下了那些生命中我們不善面對的,並且讓失去變成另一種生命的測量刻度。
將兩個從未結合過的事物結合在一起。世界就此改變。當下或許無人發現,但無所謂。世界終究是改變了。
相信每位讀者在掩卷時,一定會對這幾句話低迴沉思良久。
讀者與這本書,也是兩個從未結合過的事物在這當下結合了在一起。
靜靜地,一切都將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