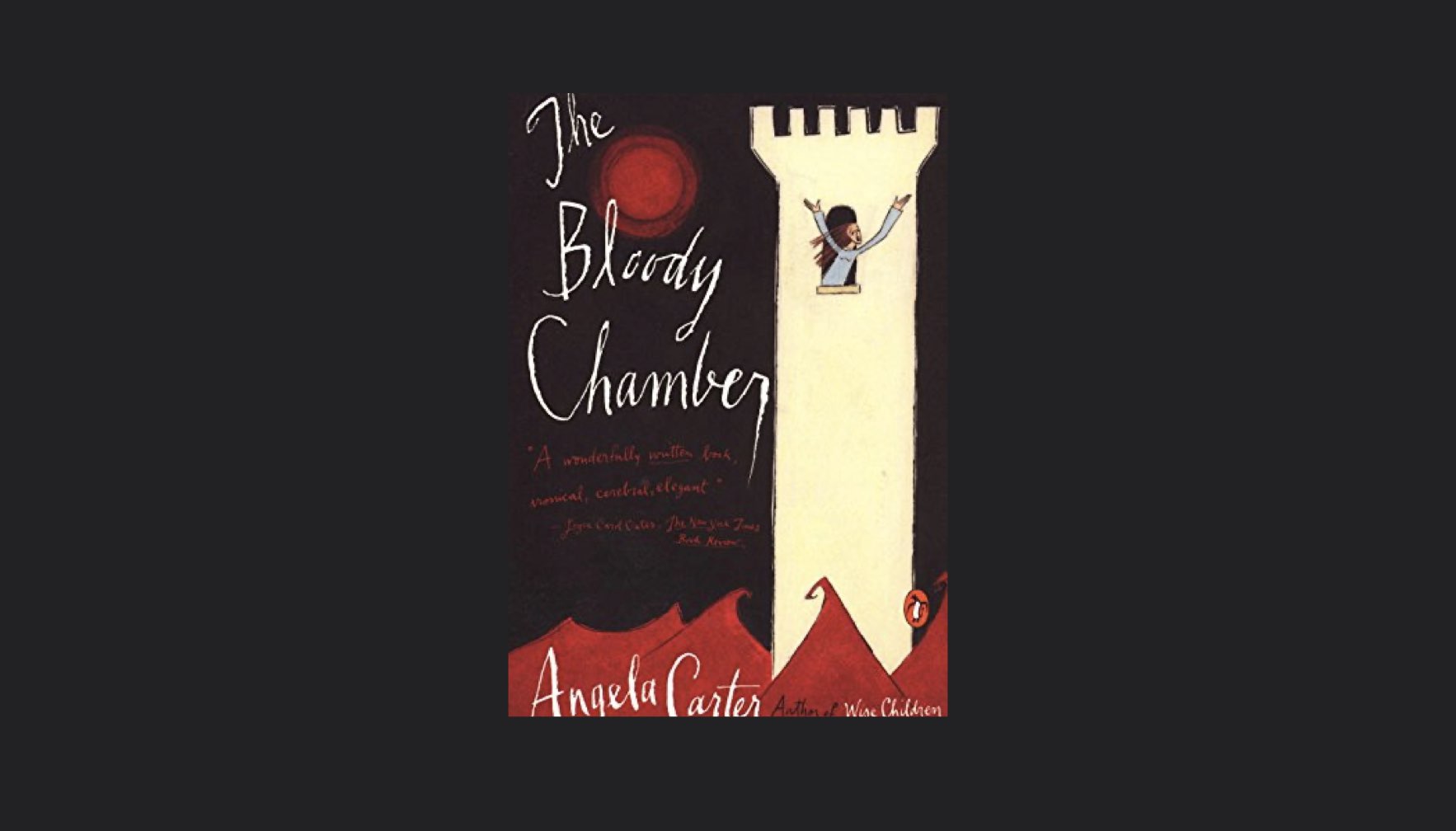《伸子》是一篇變色的愛情童話。大多數的浪漫愛情故事,如果不是王子搭救被巫婆囚禁在高塔裡的公主,就是千金小姐愛上窮小子,歷經重重波折與考驗,終於證明這世上存在著真愛。童話故事總結束在戀人相擁親吻的瞬間,繁花與彩帶繽紛飛舞,天使拍著翅膀吹奏祝福旋律──然而,如果有一天,終於在一起之後的某一天,有人驚覺彼此個性存在著不可彌補的差異,而且不愛對方了呢?
這當然不是童話世界內會冒出來的疑問,卻是《伸子》值得「日本近代文學第一流作品」稱譽的理由。掙脫家庭的束縛、來到紐約留學的伸子不顧親友勸告、不惜與家人決裂,終於在回日本後爭取到與戀人佃的婚姻與生活。婚後,宣稱將支持伸子實踐志業的佃負責工作家計,伸子卻在這不需做家事、不需生育後代的平靜生活中,慢慢察覺二人之間日漸擴大的裂縫,終究做出離開佃的決定。
魯迅對於新時代的性別解放運動,曾提出「娜拉走後怎樣」的疑問:缺乏個人自覺與社經條件的女性解放,可能只是悲劇的複製。幾乎同時期的日本,《伸子》自剖經驗,娓娓道出個人自覺的產生需要歷經試煉,那不是一個玫瑰色的幸福結局,而是一場又一場對於玲瓏心靈的捶打。在《伸子》長達五年的情感生活中,關係的破裂、愛情的褪色這些讓人懷疑個人價值的變化,都不是因為第三者介入、家長作梗反對、現實社會的壓迫等明確可見的外在因素所致。
「比起說明佃是個多令人不滿的丈夫,唯一需要的就只有伸子自身宣告『我已經無法愛他了』、『我無論如何都不想跟他做夫妻』的勇氣。」──伸子的自剖誠實到令人吒舌。佃絕非惡人,紐約的長輩朋友雖勸阻伸子與其相戀,但也都沒有明確指出佃的人格缺失與不良事蹟。伸子母親擔心佃想利用聯姻攀附自家權貴,似乎也沒有發生。他甚至不干涉伸子來去娘家、鄉間老家、訪友的行動,並立誓「完全獻身於妳」、「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口口聲聲「只要讓你幸福,我就會做」,這樣一個不吝表達愛,寬容大度的丈夫,伸子到底不滿些什麼?或者進一步說,伸子有沒有在婚姻關係中感到寂寞不滿的權利呢?
伸子與佃之間戀情的開始與結束,都因為「病」的催化。第一次,伸子在紐約得了致命的流行性感冒,意識混沌之際感覺到佃的親吻,二人關係遂正式發展為戀人。第二次生病的是佃,在伸子提議分居以重新思考關係之後,佃出示咳血手巾,暫時挽留了伸子。突如其來的病痛打破了日常秩序,凸顯肉身的脆弱、生命的無常、個體的孤寂不安,迫使人面對自己的存在樣態。
佃的吻,遞補了病中伸子所渴求的母親懷抱,暗示著他將成為照顧伸子的家人。而當伸子發現佃是在以生病來挾持自己僅剩的情感,竟暗自期待佃病死,以自然解決彼此之間的僵局。轟轟烈烈的戀情至此,幾乎僅剩不堪,但伸子的心境卻明晰地令人動容。她沒有嘲笑佃行為的滑稽,而是剔骨削肉式地剖析自我戀情中依賴、人道恩義的成分,一步一步走出被許諾的恬適家園,並將自己煩惱、思索的心境,化為「獨立」女性的姿態。
這樣的決定對於伸子,不、對於任何真實愛過的個體而言都不容易。伸子的時代從小教導女性應當「認份」,而優異的家境與高等教育只讓她遭遇困境時必先歸責自我,甚至相信憑著努力可以改變一切。說到底,伸子前往紐約、與佃結合,都是出於逃離母親控制的期待。
然而,「獨立」並不是從一個家庭投入另一個家庭而已。伸子的覺醒與行動,當然有賴於優渥家境的支援──缺乏經濟能力,遑言個人獨立?同時不可忽略的是伸子的自我期待──「更深更廣地瞭解人們的生活,在死前完成一部傑出的小說」。即使是困頓艱難的時刻,伸子的心眼都對周遭環境高度開放──灑遍紐約大道的金色陽光、庭園裡盛開的山茶花、高懸冷冽夜空的明月、護理師走動時露出的裙擺顏色。伸子的世界不只有佃、也不只是自己,正因為對世界的熱愛與自覺,伸子終於找到了能讓自己高歌的聲音。
《伸子》出版之際,作者名叫中条百合子,此時她已經離婚,正準備與女性友人前往蘇聯,開啟另一段身為左翼作家的人生。與即將入獄的左翼運動家宮本顯治結婚後的她,因為曾撰寫楊逵〈送報伕〉的審查意見,其姓名才被部分臺灣讀者所認識。《伸子》中對於個體與社會期待的省察,是那關懷普羅階層、殖民地處境的女性革命家的誕生基礎。非常個人化、也因此具有絕對的普遍性。伸子訴說自己苦惱與思辨的聲音,穿越革命思潮風起雲湧、戰火焚城的巨變年代,其豐沛的情意在細膩的詩情描寫中,對著仍在愛與自我中掙扎的廿一世紀讀者,緩緩襲來。
本文作者為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