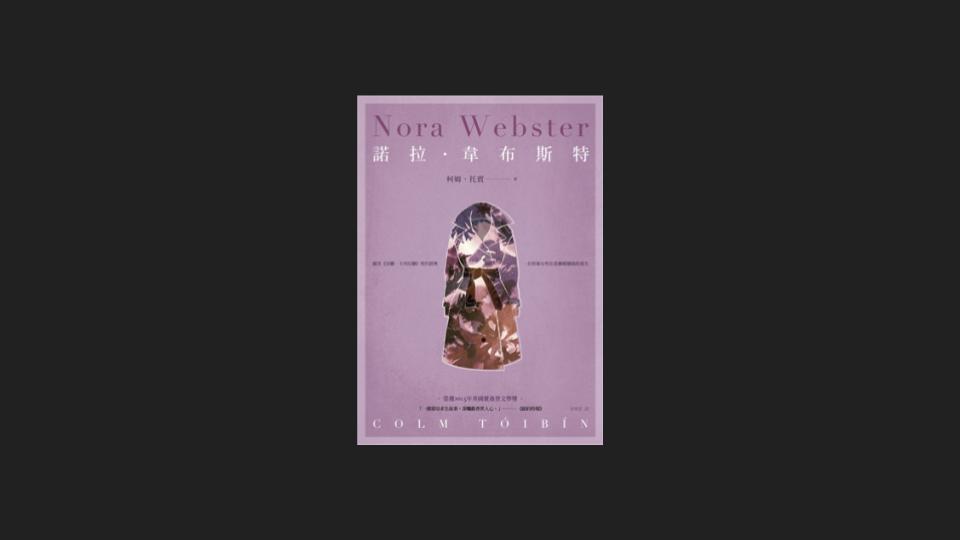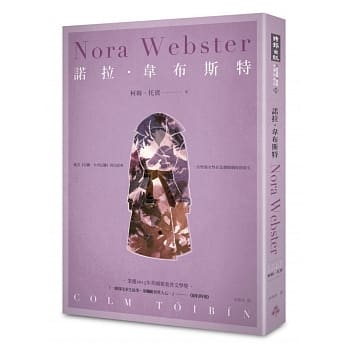自一位向風車衝撞的騎士誕生之後,小說成為人們進入他人心靈的甬道。往後,人們雖清楚甬道總會抵達到最熟悉的盡頭。但在百轉千折的甬道所嚐到的是一種不用言語,以內在心智去契合的滋味,這種滋味造就了一群嗜讀小說的人。
樂於向世界對話的人,外在的光芒有時與內在的能量,常互相爭奪光彩。這樣性格的小說人物所說的故事總是高潮迭起,吸引人們樂於圍著爐火與他們。然而相對另一種性格的人們談論自己使他們頭痛。與人交談每一秒鐘都與奪門而出的衝動交戰著。柯姆.托賓筆下的主角幾乎都是這類型的人,或著說是他選擇樣的主角,按他自己的話,他在乎內向性格的人,心裡那股寂靜的力量。
愛爾蘭作家柯姆.托賓的新作,評論者認為他做了一個人性上勇敢的挑戰,描繪出一位與自己母親遭遇上極相近的女性。一個極力控制外在情緒的寡婦──諾拉‧韋布斯特。柯姆‧托賓以諾拉一日又一日的生活場景,為讀者燉出一種平淡卻深刻的滋味,讀過《諾拉.韋布斯特》的人曉得,它摻著諾拉無言的悲痛、四名子女的不安、親戚友人大量的提點及關懷。
故事從與一棟避暑小屋的告別開始,失去男主人的避暑小屋對女主人是無聲的提醒。但售屋的舉動卻意外的觸動子女們的神經,使得喪父帶來的生活改變,先從失去夏日的一座小城堡開始,父親成為回憶,小屋將是他人的屋宅。
諾拉先關注並照顧眼前二名稚子的心情波動,在外地求學女兒們則需依賴她們的理解。售屋收入可以短暫支撐著丈夫的位置。接著諾拉的大伯安排了機會,使她重回婚前的工作崗位;諾拉的少女時期是在鎮上批發商行裡工作渡過,直到遇見丈夫墨利斯,她才能脫離母親的管束。她知道沒人明白自己當年離開那間辦公室的意義,那裡曾是她的牢寵。
諾拉願意為了子女而重入商行,有形的辦公室枷鎖由固定的時間支配;但關於丈夫墨利斯的一切念頭,是她無形之中所攜帶的牢獄。生活是活著的賭盤,如果下愈小的賭注,它就給你日複一日,不痛不癢的結果。
諾拉對於給一位陌生客人吃閉門羹的念頭,在她拉開了門後打消了。上一秒的念頭是丟棄的賭注,開門邀請客人入內才是大一點的賭住。生活給了諾拉一個新的局勢,她開始與丈夫生前沒有交集的人們來往,他們不是行為惹人非議者,只是小鎮生活素來簡易,習慣是最高指導原則,丈夫墨利斯的習慣是諾拉過去的生活之重心。
因新朋友的引薦,諾拉開始收集喜歡的黑膠唱片,持續學習歌唱技巧,這些轉變給她最大的自由即是──暫離亡夫:
音樂正牽引他離開墨利斯,遠離兩人從前的日子,遠離母子生活。追根究柢,這種現象並非墨利斯不懂音樂,也並非音樂從不是兩人共通的興趣,而是向蘿莉學習歌唱的感受很強烈──在隔音室裡,她能自我獨處,墨利斯無法亦步亦趨,甚至死後也無法跟過來。

生活的難以預料已令人咬牙切齒,他人的攪和更是束手無策的關鍵原因。無技可施的,往往他人不是單純的旁人,而是有著親緣關係的人。他們甩著與我們相連的血緣臍帶,在我們的情況於他們眼裡不妙時,纏在我們身上,微笑地說這一切都是為了更好的明天。
諾拉習得獨處的自在之道。同時間,她所賺的微薄薪水及寡婦年金,不足她四名子女的學費開銷,短缺處均來自大伯及大姑的援手。他們皆未婚且疼愛自己的弟弟與弟媳所生養的四名子女。只不過種種對姪子姪女們的寵愛,常常越過諾拉管教子女的界限。
大兒子沒與她商量,便收下大姑為他打造的一座攝影暗房,蓋在諾拉的家中;大女兒想向她借用一筆為數不少的金錢去倫敦置裝及旅行,並承諾她領到工資後還她,諾拉在意的是大女兒對金錢的態度,但大伯、大姑及自己的二位妹妹,都支持女兒這個外出計畫。自己的二個妹妹──也就是子女的阿姨們──向來也是比自己與孩子親暱。諾拉肩負單親父母對子女的雙重責任,照顧及約束。但親友們之於子女們,是朋友們般的存在,同時還聲援並資助他們的興趣,這一點,母親諾拉真的很不討喜。
身為讀者,大量地讀到作者托賓對於主角人物白描的內心感受,它們經常就是一個狀態詞,接著沒有其他陳述。以單字和短句的少量對話,這些對話與天空雲層深處傳來的悶電響聲差不多,在與諾拉對談的人之間,總是來得突來後,輕聲的結束。借用一句紀大偉老師所說,柯姆‧托賓的風格確是「憋」,確實不是討一般讀者的青睞。
可處在柯姆‧托賓的寂靜世界裡,我發現,這裡的規則不是拋棄話語,而是蒸餾話語。話語不是用來做生活的填塞。
觀察人物角色能放大至言語之外的角度,托賓筆下的角色與作者一樣喜好靜靜的觀看並留意細節。透過托賓的文學作品,我得到了貼近不語者內心的經驗。不語者不是拒絕話語,而是悲痛無法消化,直致失語。如同諾拉的大兒子東諾,他的結巴始於寄居在姑媽時,在姑媽家裡苦等父母的歸來,然而一天天的過去,大人巨大的背影傳來的沉默,吃掉了他的話語。直到遠離父親回憶充斥的教室,母子決心一同渡過轉學的適應期,東諾終在一所沒有父親執教的學校站穩腳步,令諾拉寬了心。
翻開《諾拉.韋布斯特》的合理期待,可視它為一道家常菜,用料簡單,靠細火慢烹,讓每一個文字都飽滿十足的生活淡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