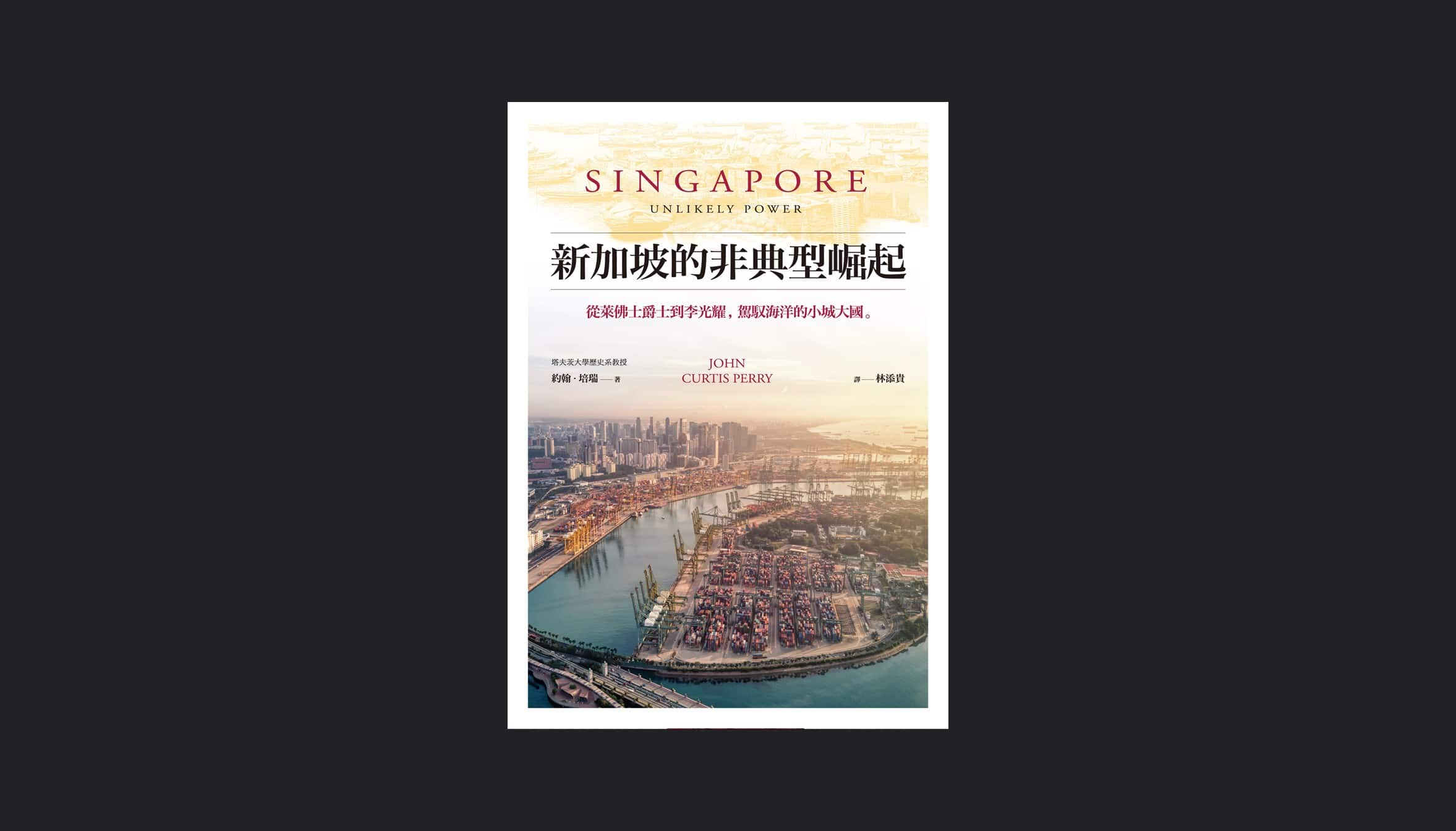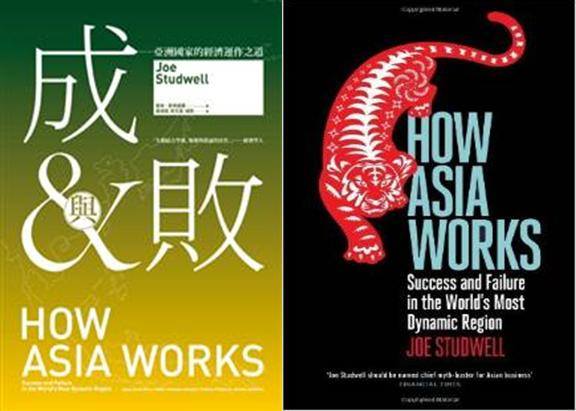在華文世界,「新加坡模式」經常引發爭論,對其愛恨者皆有。從「新加坡模式」歌頌者角度看, 「新加坡模式」不乏神話色彩── 在強人李光耀的領導之下,精英政府能強政勵治,故此新加坡雖為小國,但仍享有極高的國際聲譽及影響力,其國民生活富裕,人人安居樂業。
由是觀之,「新加坡模式」乃善治模範,為民眾福祉著想,各國家領袖都應複製「新加坡模式」。厭惡「新加坡模式」的論者卻認為,新加坡奉行家長式管治,社會自由被踐踏,民眾意志不被尊重,故此「新加坡模式」不可取。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新加坡模式」想像並非全無道理,但仍不足以完整呈現「新加坡模式」的本貌。
具體而言,上述「新加坡模式」想像問題有三:第一,這些想像僅從新加坡管治精英的角度去理解新加坡,民眾一概被視為滿意政府所有作為、毫無情緒的被動追隨者,他們在「新加坡模式」之中的角色因而甚少被認真探究;第二,新加坡獨立建國至今已逾五十年,執政黨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PAP)一直能夠一黨獨大,且在可見的將來,這種國家政治局面仍會延續下去。問題是,政府擁有威權力量、能使民眾屈從並非新加坡威權政治史之全部;第三,「新加坡模式」面對何種威脅?為何如此?有何解方?這同樣是上述「新加坡模式」想像無法解答的問題。
從《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看新加坡威權管治神話
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所著的《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下文簡稱《新加坡模式》),是有助於破除「新加坡模式」神話迷思、從新加坡在地視角透徹認識「新加坡模式」不可多得的入門讀本。
陳思賢是新加坡本土政治學者,活躍於新加坡公民社會,曾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前副院長。有別於一般想像,陳思賢在書中的基本觀點,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之所以能夠長期執政、一黨獨大,首要倚重的並非政府所擁有的威權力量,而是能說服大眾接受執政黨家長式管治的「新加坡故事」論述。
可以說,「新加坡故事」論述之建構,其實也是新加坡城邦國家建構工程的核心一環。官方「新加坡故事」論述強調,國家細小,欠缺資源,生存基礎脆弱,時刻面對各種威脅, 故此需要強勢精英政府居中協調與善用資源,若非如此,社會便會分裂與動盪。為求國家生存,新加坡政府以實用主義哲學(pragmatism)與用人唯賢精神(meritocracy)這兩大原則行事。這種管治哲學強調兩點:第一,國家之生存不應受某一特定意識形態與道德價值觀所羈絆;第二,國家必須廣納「人才」。
於全球化體系之中、在民主政體漸受質疑的時代,陳思賢的觀點(即「論述為新加坡建國根基」) 其實頗具啟發性。按此觀點,新加坡政府的霸權地位並非絲毫不受任何挑戰,民眾並非全然被動,新加坡威權政體並不如外界所想像般牢不可破。陳思賢特別指出,新加坡擁有雙重身份,既為全球城市(global city),也是國族國家(nation-state)。
這種國家雙重發展定位已引發種種社會矛盾,官方「新加坡故事」論述之魅力已不如前。正因為此,近年來新加坡政府努力修正論述、調整官民關係,例子有二:第一,在 2012 年,新加坡政府舉行全國對話,廣邀民眾就國家發展目標與策略各抒己見; 第二,近年新加坡政府重新詮釋實用主義哲學與用人唯賢精神,希望藉此減少民怨。
「新加坡學」的三堂管治課
《新加坡模式》仿如「新加坡學」之精要。按陳思賢的梳理,對於「政治秩序之建構」與「何謂善治」這兩大課題,「新加坡學」有三大啟示:「新加坡學」告訴我們,論述是建國基石。
《新加坡模式》的一大要旨,是論說新加坡的內政與外交發展方向如何受官方「新加坡故事」國家發展論述影響。對內,「新加坡故事」有助鞏固威權管治的民意基礎;對外,「新加坡故事」可增強國家的國際軟實力,既有助國家招商、刺激經濟增長,亦可進一步提高新加坡政府的威望。
自 2019 年六月起,香港爆發流水革命(Water Revolution ),新加坡政府精英頻頻對此表態,這多少能夠說明論述與威權政體之維繫有何關係。我曾為此撰文〈新加坡模式的政治哲學──從香港流水革命期間新加坡對港評論說起〉,文內的主要觀點,是新加坡傳媒與精英的發言對象其實不是香港人,那些言論基本上是「新加坡故事」的另類演繹, 其內容多少附有內政外交功能。
新加坡傳媒與精英借用香港事態,不斷提醒新加坡民眾,強調在任何情況下,民眾都不能對抗政府,官強民弱才可讓社會健全發展及避免分裂,這其實都是「新加坡故事」的要點。新加坡治國精英之所以需要如此借題發揮演繹「新加坡故事」,是因為近年來新加坡社會怨氣已現(下文會詳細闡述這一點),香港時局或會令新加坡民眾重新思考「政府— 社會關係」,屆時「新加坡故事」的公信力或會受挫,政府的威權管治可被撼動。
說到底,「國家」並非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能隨民心思變而浮動的人文哲學概念。在後李光耀時代,觀察新加坡國內的政治論述變化, 對理解未來新加坡政治發展趨勢不無助益。
第二,「新加坡學」告訴我們,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式全球化與本土生活息息相關,廣受讚頌的新加坡管治模式已受新自由主義管治思維蠶食。《新加坡模式》不時提到,新加坡擁有雙重身份──新加坡既是全球城市,也是國族國家。如上文所提,這種國家發展雙重定位已衍生矛盾,且矛盾愈演愈烈。
陳思賢指出,配合新自由主義式全球化,已漸成新加坡首要的國家發展目標,隨之而來的結果,是外來人口增加,生活成本上漲,本土民眾的生活壓力有增無減,新加坡多元社會分裂風險日增,官員形象日益脫離民眾,民怨為此漸起,國家建構工程為此受阻。
新自由主義奉市場至上, 並強調各國應奉行自由貿易政策,容許全球資本自由流動,對市場應少作干預。陳思賢分析,在這種管治模式下,權力不免會集中於政商精英手中,社會力量進步力不免會步向衰敗,民主政制不免會變得徒具形式──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不難接觸自由與公平選舉,但認真且具成效的政治議論會漸變得稀有,威權政治會被鞏固,這正是社會學家高署(Colin Crouch)所描繪的「後民主」(post-democratic) 新自由主義世界的景象。
陳思賢進而認為,「這種『後民主』狀態已漸現於新加坡,這會使新加坡模式變得不再獨特。」新加坡官員行事已愈加受市場邏輯主導,他們對民間疾苦逐漸顯得無動於衷,加上新加坡政府一直排拒福利國家管治模式,在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民怨爆發並非不可能發生。
在此背景下,新加坡實用主義哲學與用人唯賢精神不免變質。實用主義哲學本來就有貶抑政治理想與價值觀、過於簡化複雜世界之問題,在市場至上管治意識下,抱持實用主義哲學的新加坡官員更傾向以金錢衡量一切,政府服務大眾之精神不免會變得薄弱,政府會更抗拒扶貧福利政策。
與此同時,政府愈加傾向倣效商界、愈加視高薪為招攬與挽留「人才」的主要手段,至於政府「人才」是否各具不同背景,則被認為無關宏旨。陳思賢繼而指出,新加坡用人唯賢精神現已淪為精英主義(elitism),並在本書附錄文章之一〈如何平息新加坡高薪養廉政策爭議?〉問:
新加坡政府也已察覺,新自由主義式管治已引發民怨,例子之一,是執政黨在 2011 年大選遭逢挫敗之後,總理李顯龍宣佈,政府將會檢討官員高薪政策。
第三,「新加坡學」告訴我們,就算從新加坡實用主義哲學角度看,永續威權政治也不見得對新加坡國家發展有利。在全球化趨勢之下,世事愈加變幻無常,要延續新加坡榮景,國家便需更具韌性, 新加坡社會必須壯大、具自信、有朝氣、能自理、能自立。換言之,香港模式其實也有值得新加坡模式學習之處。
論者經常將新加坡與香港管治模式相提並論,但兩者不無差異──在香港模式之中,社會較強、政府較弱,新加坡模式的基本特點則相反。事實上,早在 1990 年代,新加坡政府便已開始宣揚積極公民(active citizenship)與公民社會(civic society)意識。政府期望公民能自發互助、主動解決社區問題,並認為國家若能如此便可更具韌性,更能適應愈趨多變的全球環境。
但陳思賢也有指出,這種期望容易落空。按其分析,經歷長年家長式管治之後,新加坡民眾已具「權威性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公民意識較薄弱,較難實現政府的積極公民願景。陳思賢說:
陳思賢甚至在本書另一附錄文章〈「新加坡故事」與希臘神話── 論新加坡公民社會復興之必要〉引用希臘神話裡有關自戀的故事,分析新加坡政府強勢、社會積弱的問題何在。文內一段說:
民眾透過互聯網愈加能夠接觸更多資訊、觀念、意識形態、價值觀,政府的反應 卻是自我防衛心態更強,更趨堅持己見。早在 1980 年代,美國著名學者傅高 義(Ezra Vogel)便以『大男人式用人唯賢精神』(macho-meritocracy) 形容人民行動黨政府的管治風格,這其實是中肯見解。」
需要補充的是,新加坡社會其實並非全然被動,全無自理能力。於 1990 年代末,新加坡社會就曾主動籌組「工作委員會」(The Working Committee, TWC),進行各種自下而上的社會管理實驗,但為免受國家規訓,這個組織已自行解散。事實上,新加坡管治精英對香港流水革命的反應已說明,即使新加坡社會復興對國家發展有益,那也是知易行難的事。
補遺──「新加坡學」的另外兩堂管治課
不過,作為「新加坡學」之精要,《新加坡模式》仍有可作增補之處。在此拋磚引玉,稍為補充兩點,使「新加坡學」更完整。
「新加坡學」同樣能夠告訴我們,全球華人之中華性(Chineseness)各異,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視角理解各地華人身份意識不無虛妄。隨華語語系(Sinophone)研究之興起,中國大陸人與全球各地華人的身份意識差異開始更受注意。華語語系研究的要旨,是破除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中國文化霸權觀,並強調經歷不同文化與歷史脈絡洗禮之後,世界各地華人與中國大陸人的身份意識與價值觀已有分別。
2016 年,在報章評論〈華文譯名以甚麼作為標準〉之中,新加坡學者廖建裕曾論說新加坡華人文化發展何以應當自立於中國大陸。他說:「各國的國情有別,譯名也需要由本國的國情而定,不能一味跟著一個國家走。像早期的東南亞華文譯名與詞彙,曾經豐富了中文的語彙,為中華文化作出了貢獻。如果一味遵循,對於世界華文的發展,不會有好處。」
到了 2017 年,新加坡政府進一步演繹這種文化自立論。同年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開幕,在開幕致辭中,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強調,身處新加坡多元文化社會的華裔,其中華性已有異於中國、香港、台灣的華人。2019 年香港流水革命爆發期間,東亞與東南亞華文媒體探討新馬乃至印尼「大中華膠」的文化源起與影響,其實也算是一種華語語系式思考。
事實上,就算在新加坡國內,新加坡華裔亦非鐵版一塊。如陳思賢在書中所指,新加坡華裔可概分為兩類,即受英文教育與受華文教育的華裔,他們的文化性格與世界觀各異,新加坡導演陳哲藝的 2019 年電影新作《熱帶雨》多少也有觸及這一點。我們甚至可以說, 曾經歷英帝國統治的新加坡是熔煉乃至觀察中華性流變與特質的有趣實驗室。
我曾在《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下文簡稱《雙城對倒》)第二章〈何謂中國人──海外華人身份之辯〉論及近世英帝國海峽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s)「海峽三傑」乃至中國南來文人邱菽園案例,探索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身份意識想像。海峽殖民地由馬六甲、檳榔嶼和新加坡組成,可視之為新加坡的前身。伍連德、林文慶、宋旺相是「海峽三傑」,他們分別為第一至三代土生華人。
伍連德是醫生, 曾在二十世紀協助中國撲滅鼠疫,為此中國國際名聲得以重振,但最終伍連德沒有應邀在中國留居, 反而回到檳榔嶼落地生根。林文慶也是醫生,他對中國文化頗具情懷,且曾任中國廈門大學校長,最終在新加坡去世,當時新加坡報章稱頌他為「偉大老人」(Grand Old Man)。
宋旺相是律師,曾與林文慶合辦《海峽華人雜誌》(Straits Chinese Magazine),推廣現代思想,亦著有《新加坡華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History of Chinese in Singapore),著作已成為新加坡華人研究之重要文獻。
邱菽園是中國南來移民,但他與「海峽三傑」的身份意識有三點共通處:一,他們的本土情懷同樣鮮明;二,他們同樣稱頌英人管治,亦多少接受中國文化;三,受自身政治觀與本土情懷影響,他們與中國大陸保持某種距離。
從 1980 年代至近年,台灣與香港都受「中國結」與「本土結」論爭所羈絆,與此同時,新加坡近年也受中國「銳實力」(sharp power)[1] 威脅,故此重溫「海峽三傑」與邱菽園的身份意識案例,對台灣、香港乃至新加坡都不無啟示。
「新加坡學」同樣能夠告訴我們,過去仍未過去,如何為英治定性,其實極具現實政經發展意義。《雙城對倒》終章所歸納的「新加坡模式」的八個特徵,基本上都與新加坡官方所宣揚的英殖時代史觀有關,這其實也呼應了《新加坡模式》的要旨,即論述為建國之本。
新加坡政府珍視英治歷史遺產,視英語為國家連接世界的重要媒介而非「殖民地語言」,沒有以民族主義史觀將之貶抑, 是因為政府認為,與世界之連結度是影響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國家若不視世界為其腹地便將難以生存。從新加坡政府的角度來看,視英治歷史為新加坡建國資產,能方便國家向西方世界示好,連接世界,吸納技術與資本。
是以在 2019 年,新加坡政府隆而重之紀念英人開埠歷史兩百年。總理李顯龍如此解說英治歷史對新加坡建國的意義:
沒有 1819 年,便不會有 1965 年,2015 年的五十週年國慶便將無從談起。1819 年為我們的國家歷史締造了可能。
與新加坡一樣,台灣與香港同樣曾經歷殖民管治,如何以實用主義思維善用殖民時代遺產,是台灣與香港可向「新加坡模式」學習之處。
結語:「新加坡學」對世界的貢獻
說到底,理解「新加坡模式」,對反思論述如何影響現實政治、善治與社會自主有何關係、本土獨特身份意識如何成形、新自由主義式全球化如何衝擊本土管治等重要管治課題皆有裨益。這是「新加坡學」對世界的思想貢獻。
(本文作者著有《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並為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
.png)
作為「全球城市」與「國族國家」,新加坡的雙重身份如何令「新加坡模式」漸現疲態?
新加坡社會能否壯大,為何是新加坡的未來國家發展重要議題?
陳思賢將從本土民情角度書寫「新加坡模式」原貌,破除「新加坡神話」迷思,分析「新加坡模式」在後李光耀時代面臨的危機。《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是立足本土﹑解構「新加坡模式」成敗得失的必讀入門書。
[1] 銳實力與軟實力意思相反,軟實力是指國家透過自身魅力贏取國際合作的能力,銳實力則是指國家利用人員與資本等滲透方式進行操縱性外交的能力。另見鄺健銘:〈即使活在中國「銳實力」的陰影下,澳洲也絕不妥協〉,《關鍵評論》,2018 年 1 月 2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