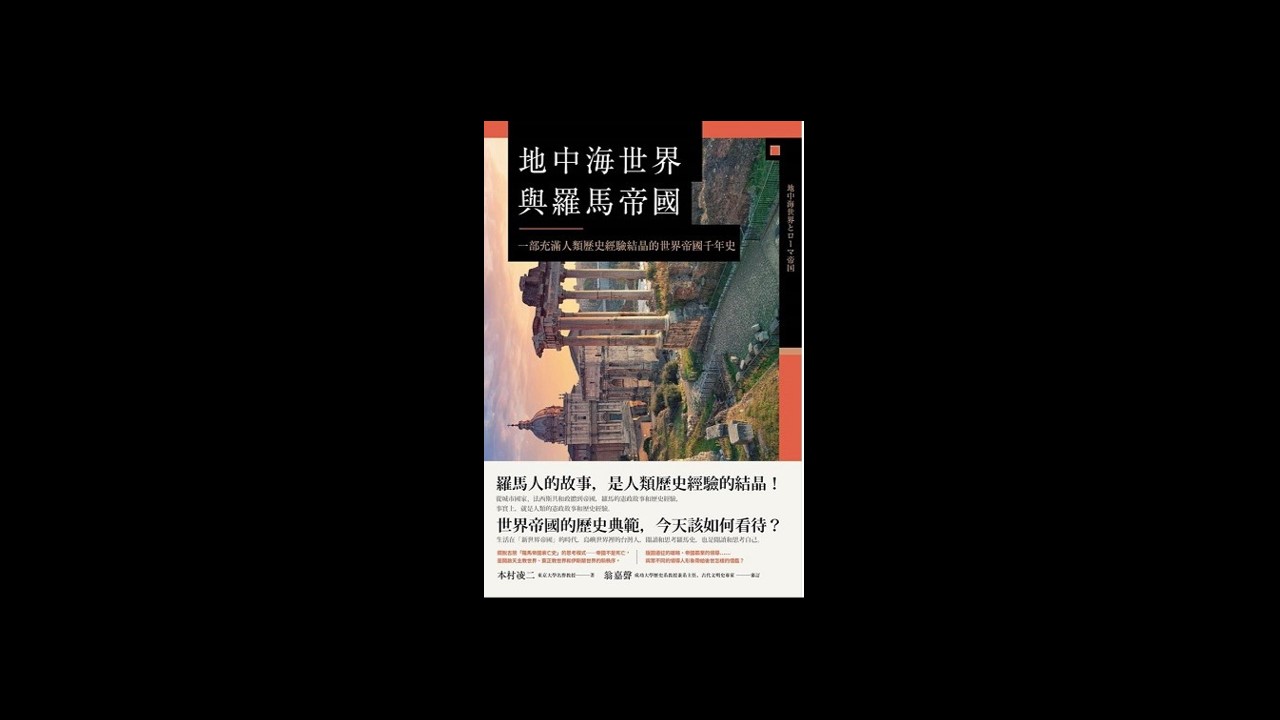希臘時期的史地學家史特拉博(Strabo, 約西元前 64 至西元 24年)在他著名的十七冊《地理學》中,第三冊獻給伊比利半島,他描述伊比利半島的幅員像一塊側身撐開的牛皮。
閱讀約翰・克勞(John A. Crow)的《西班牙的靈魂》像在看「庖丁解牛」,看他如利刃的筆力游刃有餘,縱切橫剖西班牙的骨骼與肌理、體與靈、魂與肉、血與髓;也像醫師在診斷把脈,柔軟溫和的指尖檢視西班牙的任督二脈,以及她的悸動與呼吸。我相信只有像克勞這樣的學者,才有可能如此愛深責切,認識那麼深、批判那麼真,針砭她無可救藥的習性,卻執迷不悔地愛她的靈
約翰・克勞在 1929 至 30 年間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彼時正是西班牙詩人羅卡在哥大進修一年的日子,完成《詩人在紐約》的超現實主義詩集。克勞在馬德里攻讀博士學位時,再度與羅卡相遇於「學生書苑」(Residencia de Estudiantes)。
西班牙第二共和時期(1931-1939 年),他在 1933 年於馬德里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博論是《英國浪漫主義者所見的西班牙》。克勞與羅卡結緣是開展他西語文化研究大樹大林的枝枒;羅卡慘遭殺害、成為內戰亡魂的悲劇是他嚴判西班牙的鐵證──西班牙總以「一種荒謬的衝動,擺脫她最有潛力的知識分子」;1937 至 74 年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兩度擔任系主任的教研學涯是豐厚他長期深耕的養分;時而回到西班牙,接觸人群,親炙她的泥土,嗅聞她的味道,感受她的脈動,體驗她的變與不變,跟著時代的腳步訴說西班牙,讓他這部於 1963 年完成的著作,截至 1985 年一版再版,迄今依然讓學界和普羅大眾認為是認識西班牙的極佳典範。
不惟如此,綜觀西班牙的本體仍難以透視這個民族的容顏與內在,克勞在 1946 年出版、更膾炙人口的著作《拉丁美洲的史詩》(The Epic of Latin America),橫跨地平線另一端,審視西班牙殖民近四個世紀的新大陸,以去歐洲中心化的視界,環視拉美殖民與後殖民的蛻變,讓他這本《西班牙的靈魂》穿越時空,益見鞭辟入裡。
克勞在《西班牙的靈魂》裡,猶如效法十九世紀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壯遊」(Grand Tour)南歐的旅程,跨世紀漫遊西班牙歷史的進程,字裡行間闡述的內容多元,涵蓋歷史、文學、藝術、建築、宗教、政治及族群。
他的筆觸夾議夾敘,時而學術,時而散論;時而引經據典、旁徵博引(西文作品、英美各家譯作、學術論述交互運用),時而信手捻來、放諸四海,個人辯證思索穿插佐證,猶如課堂講演侃侃而談。他將古典和民間文學交錯並置,尤其西班牙中世紀的文學、故事詩及民間歌謠。長期以來,少見像克勞這樣的學者如此深刻的描述與讚頌。
克勞的原著以西班牙的根與花為標題,解讀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宿命與民族性:眼見已腐朽的根,卻繁花燦爛;花朵凋零枯枝敗葉當兒,卻見莖上綠芽盎然新出。
歷史縱軸上,克勞勾勒西班牙這塊牛皮從遠溯希臘、迦太基的時代紮營奠基,歷經羅馬帝國的盛衰、兩個世紀的西哥德統御、八個世紀穆斯林的輝煌與驅逐、天主教國王的大一統與新大陸殖民、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的世代更替;從黃金世紀到殖民帝國衰頹、拿破崙入侵、二十世紀初的分崩離析、第二共和的不共不和,到鬩牆之禍的內戰,直至佛朗哥獨裁近四十年。開放的明君無法代代接力,閉鎖的昏君卻是多而綿延。眼看她起高樓,眼看她宴賓客,眼看她樓塌了。
克勞讚許,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像西班牙一樣,在 1492 年有限的時間內,同時發生多件劃時代的關鍵事件;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某個時刻,擁有像西班牙這樣無限的潛力和活力。但是,他也洞悉,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啟蒙運動時的西班牙沒有被啟蒙,法國大革命時沒有被影響改革,經歷工業革命卻未工業化的停滯。她像一座大山,對人類巨大的衝動可以無動於衷,依然屹立不搖,生存在她的記憶,她的老靈魂裡。弔詭的是,她的弱點常常是成就她的偉大的所在。
橫軸再看這隻奔放的鬥牛另一張臉:現代西方沒有一個國家像西班牙一樣,經過三教(猶太教、伊斯蘭、天主教)九流(殖民地擴及拉美和遠東)的洗禮、衝突與融合,造就她的豐富與多彩多姿;未經琢磨訓練的西班牙人,卻能創造出偉大的藝文,並且始終擁有難以摧毀的深刻尊嚴和力量。
從這兒,我們看到了西班牙的本質:為了理想和意志堅持的吉訶德,騎著瘦弱駑鈍的駑辛難得(Rocinante),穿越廣袤荒漠般的黃土地,疾呼他對國家的救贖。克勞在這本著作裡,無疑將西班牙文學的傳統與經典帶到一個至高無上的優勢位置。他在每一章節引用西班牙作家的作品為註記,從中世紀的「智者」阿方索十世到二十世紀的小說家塞拉,作為他闡述剖析西班牙的佐證。每個引言的另一面,都是這些知識分子對西班牙最深沉的省思與真摯的愛。
克勞點出了西班牙幾個根深柢固的精髓與傳統,成就其煜煜輝赫的盛世,也導向她矛盾的悲情。首先是流浪漢文學。克勞刨根直言這是根植於西班牙早遠牧羊人的傳統,也源於猶太、摩爾人遷徙漂流的生活型態。
這是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在牧人值季節變換交替時,或是畜牧趕集、護衛著千隻羊群遊於市時看見的奇觀。流浪漢文學的萌芽以至臻於成熟,沒有在西班牙的文學史上斷裂過:從中世紀的故事詩、文藝復興、巴洛克時期的流浪漢小說的原型《小癩子》、《騙子外傳》、《古茲曼‧阿發拉契》到巔峰作《吉訶德》,從玩世不恭、風流成性、四處獵豔的唐璜到奇情異想的吉訶德,從九八年代的在地旅行文學、書寫卡斯提亞的家國情懷到一九六〇年代的「說西班牙」(Contar España)在地風土民情書寫的高峰,都是流浪的本質、旅行的實踐。
西班牙作曲家馬金納・那羅(Pascual Marquina Narro)1923 年所譜的西班牙進行曲〈吉普賽西班牙〉(España cañí),該是描述這個流浪漢傳統最佳的寫照:
向來就是吉普賽,花朵的詩篇
眼中的火焰,點燃了熱情
這是我的西班牙,最勇猛的土地
吉普賽西班牙
克勞認為流浪漢的性格和文學「是非常人性化的抗議,是西班牙人存在痛苦的表現,是在世界和現實不斷向前流動之際,自我在矛盾中的視野」。這也呼應了西班牙史學家狄亞茲・布拉哈(Fernando Díaz-Plaja)超越百萬銷售的《西班牙人與七原罪》(The Spaniard and the Seven Deadly Sins)的剖析,西班牙不斷在實踐與反省、上下滾動的漩渦裡跳躍。
另一個西班牙的特點就是宗教的濡染覆被。西班牙從中世紀被征服與再征服的歷史中,從殖民帝國的征服與衰頹中,宣教永遠居於優先地位,是信仰的核心,也是維繫政經與統治的權杖,連帶幾世紀影響著新大陸千百族群的信仰。
因此,文學裡,中世紀曼里奎的《祭父詞》,醒悟生命匆匆,推崇死後歸主榮耀的靈魂永恆;十七世紀聖女大德蘭和聖若望十字的神秘主義,力行靈修,體現與主心靈合一的狂喜;傑出的文人作家皈依成為神父修士的風潮,加上天主教引領了主政者治國的準繩,也影響了社會的氛圍與規範。迄今將宗教化為觀光,民俗節慶成為文化遺產的國家特色,牽動人民的愁緒、喜樂、魂與魄。
宗教的嚴謹紀律和流浪漢的隨遇而安,道出西班牙這個民族的矛盾與扞格,卻總能和諧又妥協。西班牙人以主之名卻又極致個人主義,不浪漫但極致感性,衝撞不可能的夢想。天主教的信仰,從宗教裁判所對人民行為與信仰的箝制,綿延幾世紀到內戰支持佛朗哥的力量。
教會永遠處在一個絕對主宰,擁有不可思議的力量,至善中有極惡,既是實踐的信仰,也是靈魂的永恆。過去到現在,這頭行如鬥牛、思如其國花康乃馨的西班牙,天主教國王與卡洛斯帝王的明君盛世恐不再現,但卻塑造了塞萬提斯、哥雅、羅卡、畢卡索,高高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克勞這本著作寫到 1948 年的西班牙,是一個美麗的休止符,也是他在本書所謂「一腳踩在過去,一腳踩在空中,等待著未來」的西班牙的分水嶺。
西班牙在 1986 年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今之歐盟),誓言成為歐洲的加州:陽光、大自然、海岸、觀光、士農工商、多種族群匯聚……希冀成為更富庶的「新西班牙」。我們且循著克勞的觀察與辯證來審視、比對後佛朗哥時期迄今四十五年來,由獨裁轉為君主立憲制的西班牙,審視加入歐盟迄今三十五年來,她的政經發展。後佛朗哥時期的西班牙已經不是克勞再回到西班牙所看到的情景。
皇家學院肩負起全球二十三個西語研究學院領頭羊的責任,對西語的使用更具彈性、與時並進,更尊重各國用字的傳統與特色,以及性別平權的考量。政黨政策上,也立法通過轉型正義的「歷史記憶法」;2019 年 10 月 24 日,佛朗哥的靈柩也已自烈士谷遷出。文化觀光更是引領西班牙經濟發展的烈焰,完整的配套策略吸引全球觀光客,永遠的數一數二。
西班牙走過奧運,經歷世界博覽會的巡禮與挑戰,她雖已非哥倫布旗幟下的日不落國,但也脫離拿破崙睥睨口氣的「非洲從庇里牛斯山開始」的偏鄉。誠然,歷史上每一次的朝代興替動亂中,向來率先追求自治的加泰隆尼亞和巴斯克自治區如今依然激進騷動,持續考驗著西班牙人民的抉擇。
這個智慧優於科學的民族,抱持死重於生的哲學的人民,她是否依然是巴洛克劇作家羅培.維加筆下的「西班牙,是她親生孩子的後母」,還是承襲祖先留下的諺語「不要放棄,繼續努力」的人民?我們左手握著克勞這本書,右手拿著我們的尺,繼續觀看西班牙這朵靈魂之花。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兼校長室特別顧問、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

但在回望歷史之時,克勞超越了政治上的紛擾興衰,而是藉由這片土地上無處不在的文學、藝術與建築,挖掘並強調歷史浪潮下西班牙人的思緒、情感與行為模式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