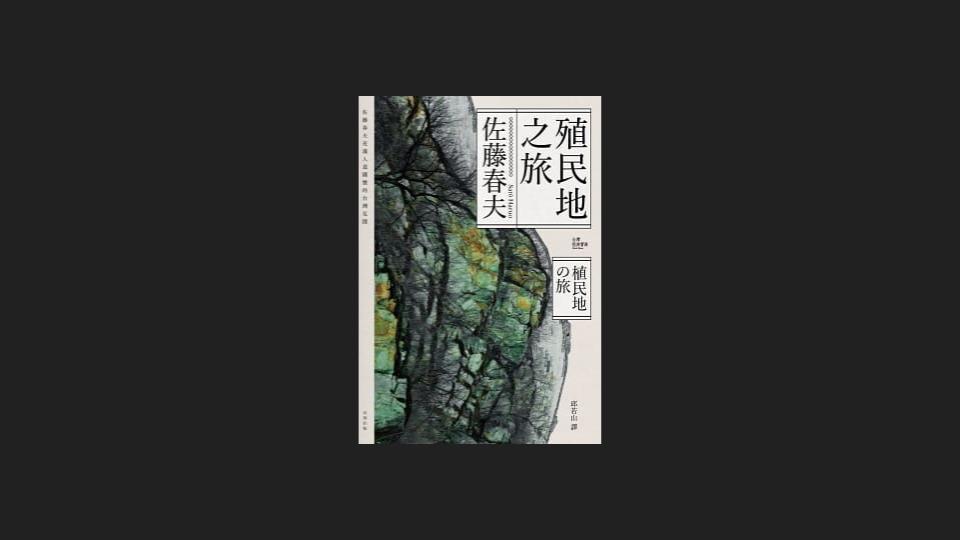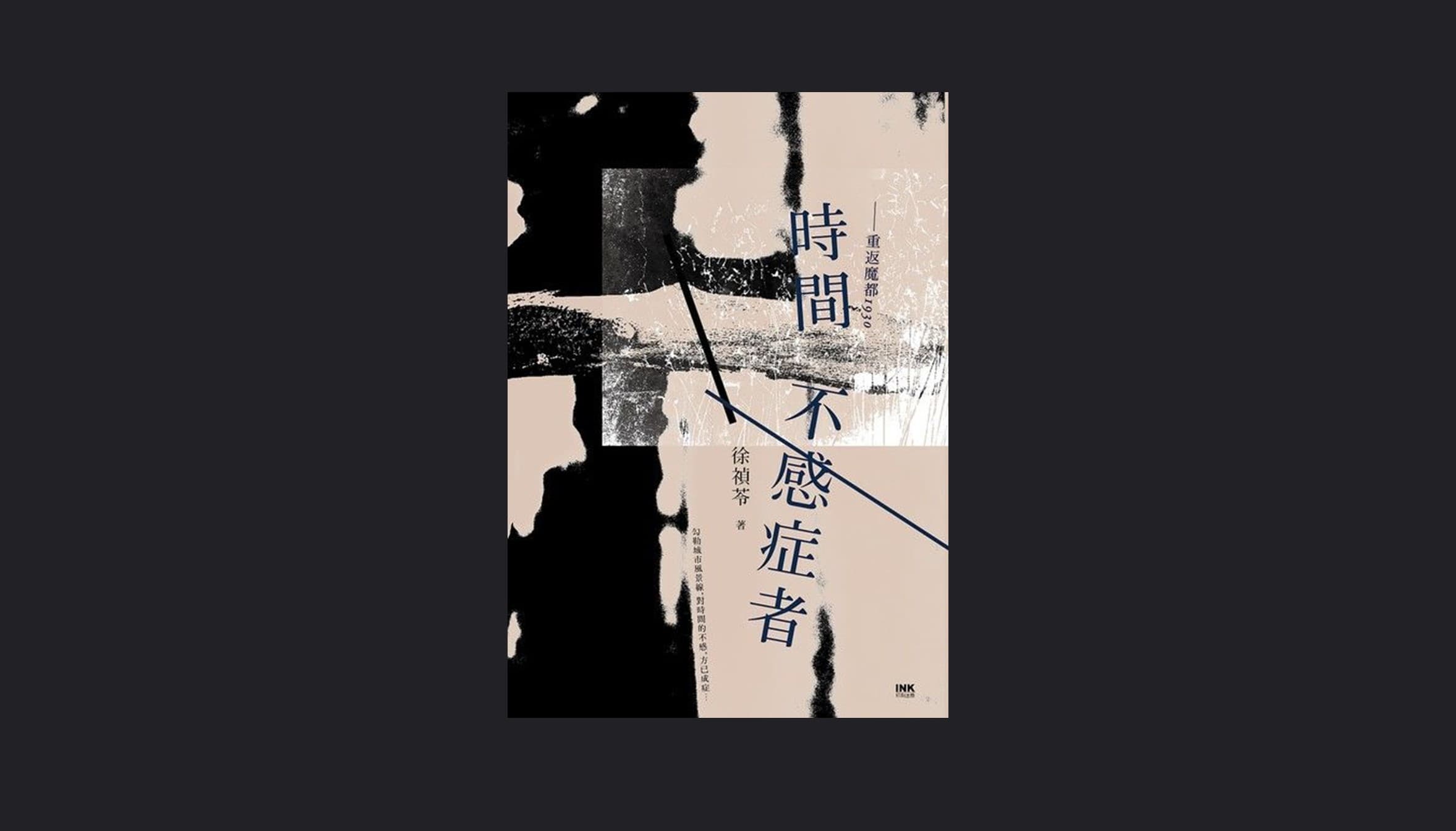在黑暗時代裡詩人何為?—德國詩人賀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
哲學家康德說,所有哲學工作最終都想回答三個基本問題:「我們能知道甚麼?我們應該做甚麼?我們可以希望些甚麼?」作為一個臺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面對「臺灣」這個臨界的、邊緣的場所(topos)──以及它所負載的那令人困惑、不快、乃至沉重到令人窒息的時空經驗,我常會忍不住地將這組康德哲學的問題予以歷史化,轉化成這樣具體、素樸的疑問:「關於臺灣,我們能知道些甚麼?我們應該做些甚麼?我們到底可以懷抱甚麼希望?」活在臺灣是一件拼命的事,作為一個臺灣人首先必須先和歷史搏鬥,存活下來了,我們才會有哲學。
在夾縫中,在黑暗中,在稀薄的空氣中,我們首先想知道的不是形上學的命題,而是我們自己的身體與容顏,因為我們想呼吸,想要手舞足蹈,想掙扎,想移動到有光的所在,想要活下去,我們想知道該怎麼做才能活下去,而我們又可以懷抱多少希望。
還有,當我們絕望時,我們的身體與容顏又如何扭曲。
作為一個臺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我總是忍不住地想要去揣摩、想像,想像那個時代到底是甚麼樣子,活過那個時代的他們到底在期待些甚麼,在希望些甚麼,又到底被容許希望些甚麼?他們懷抱希望時的姿態是甚麼?徬徨動搖時的神情是甚麼?絕望時的姿態又是甚麼?
我曾經嘗試在他們留下來的關於政治的手稿中──大多是斷簡殘篇──尋找蛛絲馬跡,然而這些壓抑、隱晦而曖昧的訊息固然顯露了他們行動的軌跡,他們作為英雄、敗者和叛徒的軌跡,卻看不清他們作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希望、徬徨、絕望的神情,他們掙扎的姿態。
這是政治史與政治思想史這類理性知識的限度,我們必須仰賴另一種知識,某種能夠碰觸歷史行動者的靈魂與鼓動的心的知識,來擴張我們對那個時代與那些前輩的想像邊界。換言之,我們必須超越思想史,進入精神史的層次,而為了進入精神史,我們不可避免地必須行經文學史的場域。
廖振富教授這冊《以文學發聲:走過時代轉折的台灣前輩文人》,就是一部引領我們走進臺灣精神史深處的文學史勞作。他在過往櫟社研究的堅實基礎上,辛勤發掘新史料,拉長時間軸,以工筆細緻而細膩地重建了從日治到戰後國民黨統治時期臺灣中部三個世代知識份子的精神歷程。
閱讀這冊精神史,這群臺灣知識分子在那個漫長的黑暗時代裡希望、絕望與徬徨交替與重疊的姿態與神情,清晰而生動地浮現在我們的心頭,讓我們彷彿與這些被歷史翻弄,但又不甘於被歷史翻弄的前輩們一起走過了這段困頓的荊棘之路。
櫟社第一代「吾學非世用,是為棄材,心若死灰,是為朽木」的自況是這段精神史的複雜原型──正如同櫟木辯證的「無用之用」,這群棄民也在絕望之中留存希望,遁世而暗藏用世之心,以傳統追求現代──因為古典漢詩是他們用以言志,甚至行動的主要媒介。在其後不同時期的歷史條件下,這個辯證、複雜、重層的精神面貌的各個不同面向與不同層次被分別凸顯,形成了這個中部知識社群精神史跌宕起伏的縱軸。
在蔡惠如「一生最愛多才智,恨無鴻鵠高飛翔。腳力翻雲,蹉跌尋常事」這段文字之中,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時代臺灣知識分子的豪氣干雲,躍然紙上。莊垂勝在太平洋戰爭時寫下「等閒莫道非時用,古幹凌空一核生」,表達了不改其志,延續傳統的志節,一系列的田園詩則隱晦表達了對日本戰爭動員的堅決抵抗。然而同一作者卻在二二八事件遇險後,對祖國幻滅,真正歸隱田園。閱讀他的晚年傑作「一爐湯正沸,山月度窗來」時,我不由聯想起吉田兼好的《徒然草》第五段那句深刻的話語:
以無罪之身而思一望配所之月。
於是我這個完全的古典詩素人會忍不住突發奇想:莊垂勝的《徒然吟草》(還有陳虛谷晚年的「來去無人知,但見花開落」),難道不是在向兼好的「無常觀」致意嗎?對祖國幻滅之後,這群知識分子的精神史之路終於已經走到了「無念無想」的諦觀境地了嗎?
當然歷史並未停留在這個時點,臺中知識分子也沒有因此全面終老隱遁,新的時間醞釀著新的不滿與勇氣,於是我們會再看到與莊垂勝同世代的葉榮鐘在六零年代以散文與述史再起,精神史的軌跡從谷底經歷了一次憤怒的跳躍與復甦,我們甚至還讀到了詩人少奇晚年的金剛怒目:
迎狼送虎一番新,浪說同胞骨肉親。軟騙強施雖有異,後先媲美是愚民。
最終,是臺中知識分子社群的第三代──莊垂勝的長子林莊生,溫柔地承接了他父祖輩的所有絕望中的希望,遁世中的用世,抵抗意志的萌生與摧折,無常的諦觀,憤怒的反擊,安靜細膩地梳理這一切交錯重疊的身影與姿態,然後把這些故事再娓娓道來,寫成幾冊書,彷彿像栽種幾株百年後的大樹,有用之用的大樹,用來懷念,用來記憶,然後轉身,走向一個新的時代──或者說走回了終於體現了臺中知識人百年前的初心,「天心自古從民意」的時代,從那裏,找到了下一階段臺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起點。
在黑暗時代裡,希望的根據是甚麼?希望的第一個根據,是記憶。從記憶中產生了意志,即使毫無根據也要懷抱希望,也要活下去的意志,朝向希望的意志。黑暗時代裡詩人何為?詩人見證黑暗,賦予意義。詩史作者紀錄詩人的見證,賦予詩的見證以新的意義,也就是記憶。詩的歷史,就是記憶的創造,就是意志的泉源,像臺灣人這樣,連單純地活著都得要拼命的,夾縫中的弱小民族的,朝向希望的意志。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從日治到戰後,短短幾十年間,
臺灣的政治環境以及社會氣氛產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
出生於臺灣,走過這些時代轉折的前輩文人,
面對劇烈變化的現實環境, 他們發出了什麼樣的文學之聲?
本書回顧臺灣前輩文人如何以文學呼應時代變局, 並從其作品中認識他們的涵養與視野, 以及想要脫困、突圍的韌性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