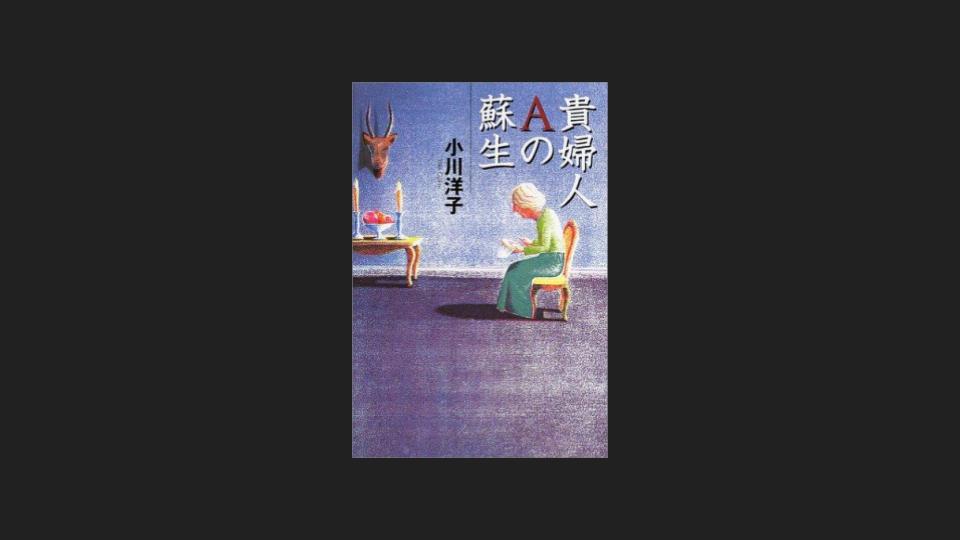「我是大食蟻獸。」生物泰然自若地回答。
怒火讓圓覺的臉色越發漲紅(略)他聲色俱厲地怒斥:「皇子您恐怕有所不知,才會混不在意地說出此等不負責任的言論。既然如此,我只得甘冒犯下 Anachronism(註:時代錯誤)錯誤的覺悟向您稟告,說到底,大食蟻獸這種生物要等到距今六百年後,待哥倫布的船抵達什麼新大陸之後,才初次被世人發現。這種生物怎麼會出現在此時此刻呢!此時此刻出現食蟻獸這事,豈不意味著時間與空間的謬誤嗎?皇子,請您想想看。」
就在此時,大食蟻獸從旁插口了。「不,沒有這種事。我們這種生物的存在還得受哥倫布之流的發現左右,這話真是太誇張,(略)我們一族可是比人類還早,就在這陸地上生活著。舉凡螞蟻存活之處,難道還有我們活不下去的道理?(略)我們一族發祥於新大陸的亞馬遜河流域一帶,從這兒看過去,恰好就在地球的正反面。」(略)
「也就是說,我們是相對於新大陸上的大食蟻獸而言的 Antipodes。(略)一如水中倒影總是倒立著那樣,在地球反面,有和我們如出一徹的生物,緊貼著我們的腳底,上下相反的存在著。這就叫 Antipodes。」
──引自《高丘親王航海記》

引文這段故事是《高丘親王航海記》第一節「儒艮」中的一小則插曲。
之後,這隻活在唐朝年間的東南亞一帶、滿口英文外來語的大食蟻獸,告訴年近七十歲的高丘親王,牠們一族有個傳說:當那鑲在蟻塚上、據說從海的彼端飛來的石頭孵化出飛鳥時,牠們 Antipodes(相反相對、正反面之處)一族就會悉數失去實體,消失無蹤。
而當親王按耐不住伸手觸碰石頭後,隔天,同行者竟已無一人記得他們曾經見過這樣一隻會說話的大食蟻獸。
1987 年刊行的《高丘親王航海記》裡,依著親王朝目的地天竺前進的腳步,將他不滿一年的最後旅行分為七段故事。一如各節標題所示,「儒艮」、「蘭房」、「貘園」、「蜜人」、「鏡湖」、「真珠」、「頻伽」等,每一段如夢似幻的故事裡都有一些充滿神話與宗教色彩、虛實難辨的奇幻生物出沒,好比說上文的那隻大食蟻獸。而這些奇異體驗又往往與親王近七十年人生中曾有過的各種關鍵回憶脈脈相關,於是,親王在海上往未知遠航的旅程,也彷彿是趟內面巡禮,向著自己的內心世界駛去。
活躍於二戰後的日本作家澁澤龍彥,今年適逢逝世三十年,他的小說作品不多,但在日本文壇留下的爪痕卻極深。與其說是因為小說成就,倒不如說是他奇異詭譎、頹廢夢幻的美學,透過隨筆與文集,使他成為日本文學史上甚為異端奇詭的存在。
他曾因引進惡名昭彰的薩德情色文學惹禍,甚至在 60 年代為此纏訟近十年。他還是三島由紀夫的好友,也是喚醒後世對幻想文學大師泉鏡花重新評價的關鍵人物之一,並用他獨樹一格的眼光推出多本異色、魔幻、頹廢的名家作品選集問世。
本書主角高丘親王(高岳親王)是日本平安時代初期曾真實存在的人物。歷史上的他,幼時遭政爭牽連,被廢太子,之後潛心修佛,歷經辛苦渡海入唐,一年後旋即出海求赴天竺,自此再無消息。那一年,相傳是西元 865年,即唐貞觀七年。後人傳說,他在馬來半島命喪於老虎之口,那邊還有他的紀念牌存在。
相對於史實,作為文學創作的《高丘親王航海記》裡,作者僅花開頭幾頁,俐落地寫親王對天竺嚮往的起點──那是始自他幼時和父親平城天皇的情人藤原藥子相處的體驗。同樣以史實人物為藍本的藤原藥子,一如「紅顏禍水」四字的表述,後人責備她非凡的女性魅力導致平城天皇與嵯峨天皇掀起政爭。本書裡的藥子也是幼時親王心中無人可比擬的存在,是不老的永遠的女人。有一晚,藥子與親王獨寢,她向著夜色拋出一顆夜光石,說:「去吧,飛到天竺去。」從此,「天竺」二字,便與藥子帶來的新芽初生般恍惚甘美的性體驗糾纏交融,永遠刻進年幼親王的身心靈裡。
在書中,高丘親王的人生始終向著天竺。即便最終他依舊沒能真正踏上天竺的土地,天竺仍是他一切生命想望的終點,也是所有的起點。
對親王而言,不論出現多麼奇異的事(例如引文,食蟻獸說話,自己的隨從一派自若地說著幾百年後的未來事),他都欣然接受,說「畢竟要去天竺嘛」。然而這趟前往天竺的旅程,雖然盡是奇異之事,但若稱之為刺激有趣的異境冒險譚又顯是過言,畢竟若要說這一共七節的種種奇人奇境帶來了什麼故事起伏,每節結尾卻又往往如船過水無痕,一點足跡不留的結束──一如沒人記得曾見過會說話的食蟻獸,除了親王自己,每一則事件都恍若從未發生過。
不消說,高丘親王在旅途中見聞的所有奇事,全都刻意留有「只是夢一場」的解讀餘地。種種神話中的生物、與寓言般神秘兮兮的夢境該如何解釋,固然大有辯論空間,但閱讀過程中我所嗅到的,則是貫串整本《高丘親王航海記》的死亡氣味。

細說前先讓我們仔細回想,你是否曾與半夢半醒的人對話過?是否曾從深沈的夢境底下,一口氣浮上到夢醒後的意識世界時,覺得分不清身在何處,感覺夢境與現實的邊界在那瞬間相互滲透?
又或是,你是否曾聽聞過將死之人在彌留時,彷彿夢境溢出心靈,斷片般的難解囈語?這樣的囈語往往沒有時間順序與前後邏輯,世界在囈語中錯置了過去與現在,也像年邁的老者忘卻了孫子兒女,渾以為自己仍在壯年。
他們有自己的時間進行,在腦內做他們最後的私密時光旅行──對我來說,整本《高丘親王航海記》就是這樣的零碎夢境,是將死的高丘親王自我人生的總清算。也因此,他在一段又一段夢裡忽老忽幼,重複幻視著年幼的自己與彼時藤原藥子的親密;在一次又一次與人的相遇中,望見藥子的身影,看見記憶深處打撈起的浮沫。也因此每一幕,都是似曾相識的「Déjà vu」。
作為澁澤龍彥最後遺作,《高丘親王航海記》也是他筆下唯一一部長篇小說作品。在高丘親王向著天竺航去的路途裡,有水中倒影般的食蟻獸,鏡面一樣的湖泊,鏡像般的兩侍童秋丸與春丸,以及無窮盡的大海原。這段鏡中鏡般無限反覆、迴圈,倒影也似的夢土之旅中,當然也依稀看得見澁澤龍彥將死之前的自我投影。
高丘親王在人生即將走入尾聲時展開的天竺之旅,既是邁向終點的旅行,亦是回歸於最初的溯行之路,而包圍這夢般一切的背景,則是南方無際大海的溫暖海原。此際,浮在水上航行的船隻,莫不是隱喻著人生命之初,漂浮於羊水中的最原始的感受。是塵歸塵,土歸土的死亡回歸,也像人一生際遇浮沈的縮影。
遊歷奇境,看見異人異象的故事,乍聽之下似乎與《格列佛遊記》或《鏡花緣》類似,但在我看來《高丘親王航海記》實則是完全異質的作品。它更抽象,更虛幻,更不具實體,更有黃粱南柯、須臾一瞬的溫柔惆悵,也更銳利地替人心抽象隱密的心思航路賦予了圖像化的風景,直抵人之所以需要幻想文學的核心欲求。
就像夢境總是理路不明,難以言說一般,要告訴他人《高丘親王航海記》的具體故事情節究竟是如何,實在是件很困難的事。只可惜本書尚未有譯本可供臺灣讀者閱讀,但他日若有機會得見本書譯本,《高丘親王航海記》會很適合陪伴讀者在失眠的夜裡,在半夢半醒之際,一天一段,一夜一夢地細細品讀。
日本文壇怪胎澁澤龍彥的遺作《高丘親王航海記》,寫的或許就是人之一生,試圖在似長又短的時光裡,追尋那永遠失落,最原初的甘美恍惚的夢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