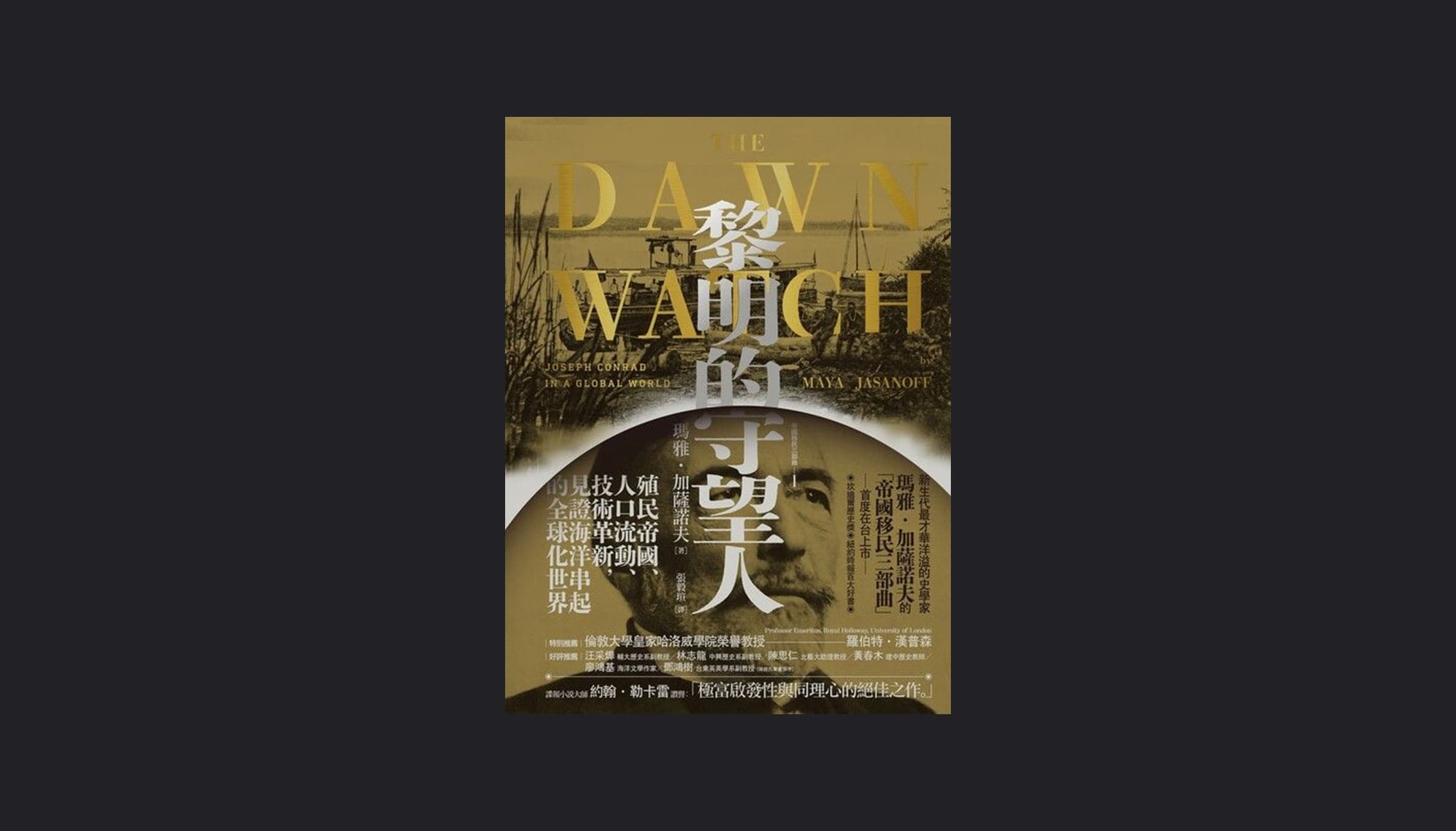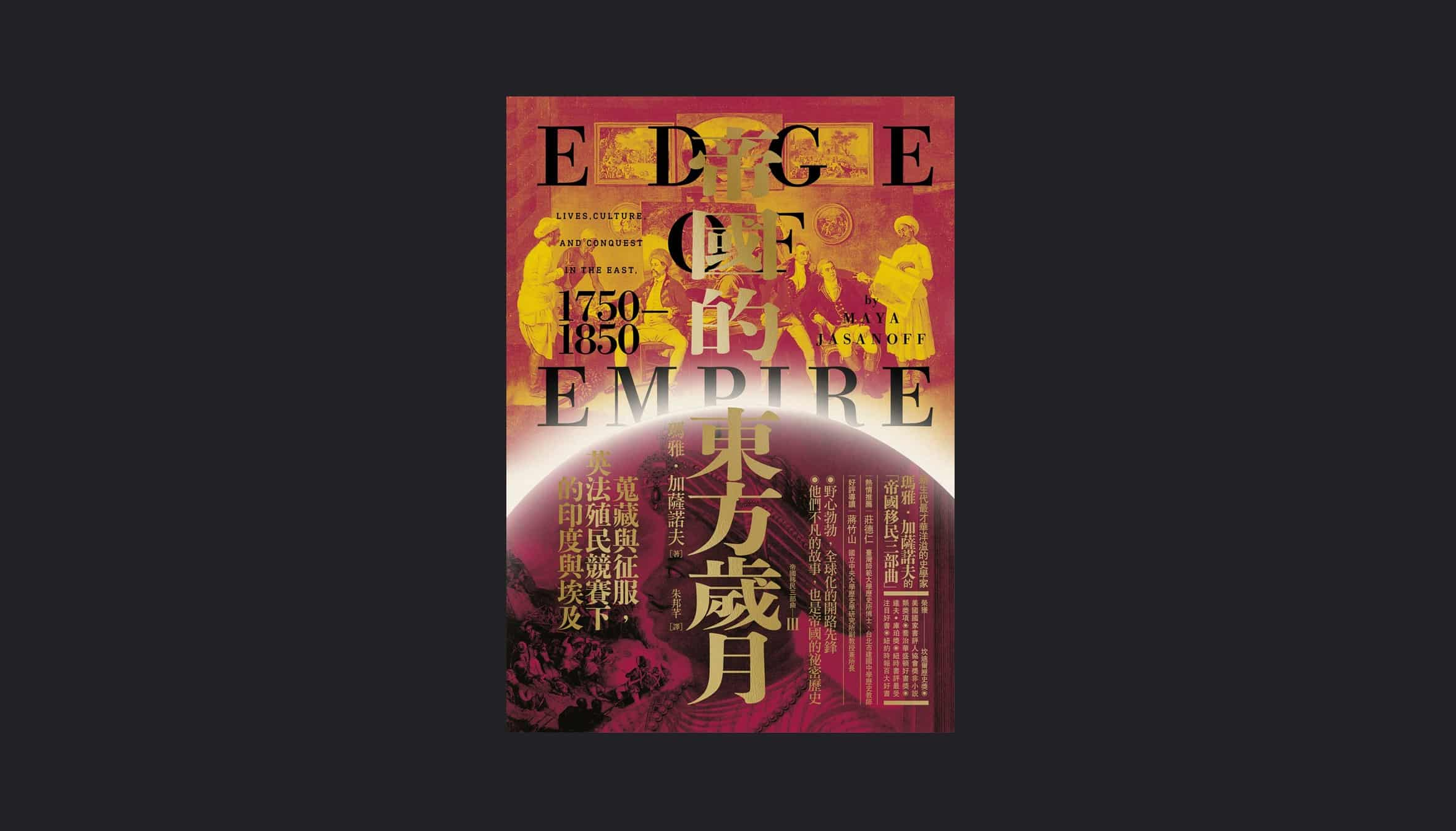「歷史進入小說」可以說是瑪雅.加薩諾夫在《黎明的守望人》一書中對康拉德小說的評論了。這裡的歷史指的是十九世紀末,由帝國主導下的全球化歷史。這個我們以為二十世紀末才出現的全球互相關聯的世界,實際上在康拉德的時代已逐漸顯現,並體現在康拉德個人生活經驗與小說中。
於是,作者瑪雅藉由描述康拉德的個人生平而同時在本書中書寫出一部十九世紀末全球史,也藉由分析康拉德的小說,說明他理解到的歷史,最終,作為一位受到全球化進程影響的個人,作者認為小說是康拉德提出個人安身立命的傳聲筒。
二十歲初頭就栽進航海世界的康拉德,無論他在船上、在殖民地、在等待下一艘啟航船班的空檔期時所待的世界金融中心倫敦,都處在新科技──運河、鐵路、電纜──帶來的新世界,這個而今我們以「全球化」一詞描述的世界,是發生在以海洋為聯結的地理空間上,而這讓康拉德有機會在倫敦、阿姆斯特丹、新加坡、金夏沙、東南亞海域、印度洋、剛果河等港口與船東、船運代理者、船員、各地碼頭工人與搬運工人打交道,他看到物品的全球流通,以及流通背後的跨國勞動力與歐洲的壟斷與征服,這些運作出一個十九世紀末的全球化進程。
儘管當時的康拉德無法名之這個世界、卻能以其小說掌握到,這就是作者瑪雅說的:
大英帝國已消失,康拉德的世界卻在我們的世界表面下散發微光。
作者在本書中為康拉德作傳,同時鋪陳一部十九世紀末的全球史,讓讀者既可以看到一位亡國貴族的命運正與全球化進程交錯影響,又能了解康拉德的小說是反映了十九世紀末正在或已發生在全球各地的歷史。
如作者認為康拉德立志「作為一個英國船員」,實則是倫敦當時是大英帝國全球海洋航線的中心地位,大英帝國擁有領先歐洲其他國家的船隻噸數,也不限制船員國籍身分,因此與其是康拉德選擇當一位英國船員,毋寧說是因為倫敦提供了外來移民者更多工作機會,可以說十九世紀末的倫敦,是今日任何全球化城市的寫照。倫敦的全球化還表現在它對歐洲革命份子以及各種政治革命主張的接納,這也是本書分析的第一部小說《密探》一書故事軸線。
當看似命運讓康拉德上船駛往東南亞時,這正是西歐帝國積極征服與殖民的區域,任何一位船員都會有機會到此見識帝國的遠東邊界。而康拉德日後負責在婆羅洲與蘇拉維西之間各港口運送物資(軍火與奴隸等),是因為婆羅洲已成為英國、荷蘭、西班牙等帝國與當地蘇丹統治者之間爭奪地盤與經濟利益的地方,這給當地帶來戰爭、叛亂與衝突,同時也成為海盜、走私或想尋求名利的人一個獲得成功的好地方。
如同本書分析的第二部小說《吉姆爺》中的吉姆,即是在這樣地全球歷史機運下來到東南亞與婆羅洲,最後悲劇性死亡。這是一個正轉變成全球命運與共的世界,無人是孤島。
當康拉德前往非洲剛果擔任輪船大副,這次的歷史機運是由比利時國王私心所主導的帝國野心,本書討論的第三部小說《黑暗之心》一書源自康拉德個人經歷,作為一位歷史人物,他正在經歷剛果正要發生的壓迫與恐怖,因此小說以「黑暗」名之,是康拉德的歷史體認,而作者以比利時安特衛普建城故事比擬比利時國王對剛果殘酷統治的雷同,讓裝點著工業文明的安特衛普,透露出其歷史本質是殘忍與暴力,如此呼應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一書中對「文明與黑暗」的反思,以及黑暗野蠻是否是本性(人性)的質問。
全球各地所發生的歷史,都無法不與歐洲帝國脫離關係,其背後動機無不是商品利益、帝國利益與在地權力結構糾結一起,有了這樣的歷史認知,則《諾斯楚摩》一書雖非出自康拉德個人經歷,卻能靠著朋友的口述經歷,而讓他寫出一本即將在中南美洲上演的政權革命、並預言美國帝國的誕生。
史學發展上,自新文化史學在史料上採取開放態度,讓研究歷史的材料沒有所謂優劣、可信與否的差異分別,如史家達頓曾應用過「童話」(口傳與印刷品)讀出十七至十八世紀法國農人的心態,因此小說文學是否適合以及可否作為研究歷史的材料,已無須贅言探討。
然而,研究小說文學的史學目的為何?它可以讓我們瞭解甚麼歷史?哈佛大學歷史學庫利奇講座教授瑪雅.加薩諾夫在《黎明的守望人》一書中提供了一個觀點:每位小說家都是歷史人物,每一位歷史人物包括你我都深受世界變化影響,儘管可能未能名之,但有些人會以小說形式、童話、歌謠、影視等媒介表達他們所意識到的世界,如小說家是藉由小說中人物的行動表達他理解到的「歷史」。
作者瑪雅在本書就是將康拉德視為歷史人物,認為他以小說形式捕捉到他理解的當下歷史,即帝國下的全球化。因此,呼應美國史家貝克(Carl Becker)所言「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那麼康拉德不過就是以小說形式作為一位歷史家書寫歷史。
然而,要如何證明康拉德小說中的「歷史」,幸好歷史學家長期對這段歷史有相當多基礎研究,提供了作者瑪雅描繪出一幅十九世紀帝國-殖民史、帝國主導的全球史,以及科技帶來的衝擊等歷史背景,以便讀者理解何以康拉德小說是以全球性為空間布局,以及理解小說中人物的命運是如何受到帝國主導的全球化影響,小說人物的行動與其結局,都源於帝國勢力對全球商品的掠奪所帶來的破壞、壓迫,及改變當地權力結構也影響歷史上任何一個人的命運。
十九世紀末歷史專業化後,史家傾向在小說與歷史之間劃一條界線即「虛」與「實」,往往將小說列為虛構性而不具參考價值,最多討論小說的「虛中實」。這種二分法只是專斷認為唯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史家寫的歷史才是「史實」,但事實上,史家不也需借用語言中的過去時態、客觀性語言以及「論說形式」捕捉過去的經驗。
《黎明的守望人》一書並未陷入這種「虛」「實」二維對立思維,作者直接認定小說的世界就是康拉德經驗到的歷史,亦即康拉德只是以「小說形式」,傳達出其對歷史的理解:人是在行動中創造歷史,但通常不是在他可以選擇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歷史(本書第四十六頁中一段話的改寫),所以虛構一個小說人物的命運不過是為了描繪那段正在發生的歷史條件(即帝國主導下的全球史)。
康拉德的歷史視野讓他掌握到帝國正在形塑的全球聯結的世界,小說家若要成為歷史家,需要具備的也是這種歷史視野。
(本文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png)
本書作者以歷史學家的獨到見解,帶領讀者見證康拉德的筆下世界,認識全球化如何生成,並形塑我們今日的世界。在作者眼中,康拉德是見證新時代的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