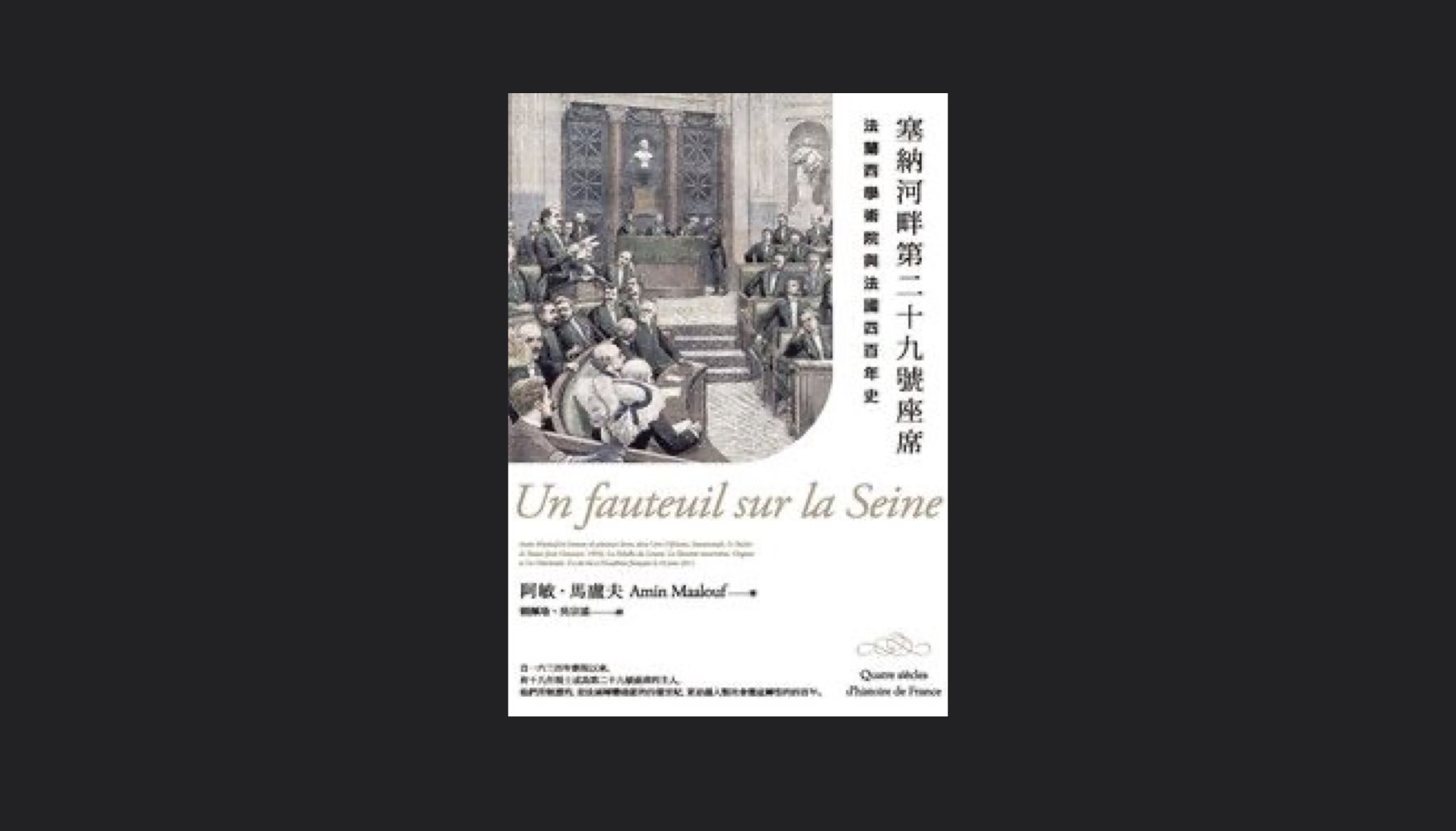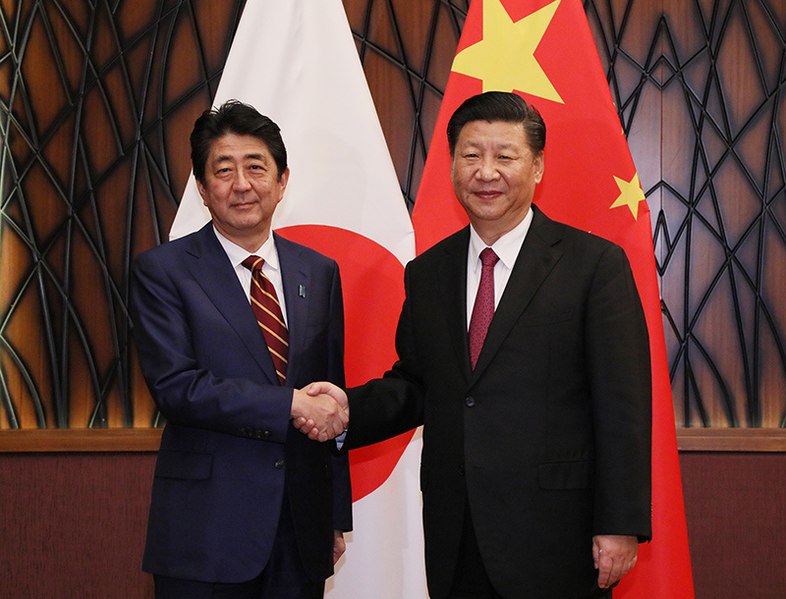2006 年,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這份期刊上展開了一場精采的學術論戰。這場論戰由多倫多大學的 Joseph M. Bryant 教授對於全球史學界中的「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提出質疑。
不少修正主義者主張「歐洲(為何能於近代)興起」是出於「幸運」,並且主張「歐洲主導世界」的時間點不該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反而遠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後才產生。
Bryant 教授因此提出三個問題來質疑修正主義者:其一、我們該如何解釋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到十九世紀間三個世紀以來,歐洲對於世界的佔領以及亞洲諸國越來越明顯的無力抗衡?其二、為何東方帝國無法擁有龐大的軍事力量以抗衡歐洲諸國的入侵?其三、工業革命有可能在瞬然間產生並且徹底改變歐洲社會、組織與工業嗎?Bryant 的質疑中,「軍事」因素成為聚焦重點。
2011 年,《火藥時代》的作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在同一份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回應了 Bryant 的質疑中關於軍事的部分。
歐陽泰特別指出三項論點。其一、中國早在 1300 年就已經發展出「中國軍事革命」。其三、修正主義者正確地指出亞洲諸國早已經歷歐洲後來才發展出的「軍事現代化」;然而,歐陽泰同時指出,Bryant 的論點也指出這樣的「軍事現代化」在歐洲的進展速度遠快於亞洲,而這一個差異很可能就是導致東西方之間產生「大分流」的原因。
眼尖的讀者也許會發現筆者「故意忽略」歐陽泰在 2011 年文章中的第二點。因為,第二點是一則事例,即是 2012 年推出繁體中文版的《決戰熱蘭遮》。
歐陽泰在《決戰熱蘭遮》中提到,透過鄭成功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熱蘭遮城的圍城戰中,他體認到修正主義者並非完全正確,反修正主義者也並非完全錯誤。兩者的差異在於缺乏合適的例子闡述東西方之間的戰爭,而《決戰熱蘭遮》提供了幾近完美的例證,說明鄭成功與荷蘭之間的軍事優勢與差異。
《決戰熱蘭遮》描寫了充滿故事性、類似小說的細節,實際上這便是歐陽泰在 2010 年曾經倡導過的「全球微觀史」(global microhistory)。然而,身為一位全球史學者,歐陽泰更希望回歸初衷,回答西方史學、社會科學等學門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為何是歐洲而不是中國主導世界?」
許多學者曾透過不同角度回答這個問題。歐陽泰的指導教授傑佛瑞・帕克 (Geoffrey Parker)認為西方經歷了「軍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其起因於火砲在歐洲被廣泛使用,因而最早從義大利發展出易守難攻的碉堡(trace italienne),造成圍城戰的革新。
大量裝備火器的步兵出現,同時為了支撐建立碉堡與維持龐大步兵等因素,產生新的徵稅制度,最終促使中央集權國家出現。以上是帕克認為西方興起的原因。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則解釋東西方的分歧發生於 1800 年左右,主因則是英格蘭的二項「幸運」:發現含水煤礦以及擁有新世界的殖民地。這一分岐他稱為「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並幾乎成為「為何西方能興起?」這一命題的代名詞。
然而,為何「大分流」會發生?在帕克以後,許多軍事史學者都提出他們精闢的見解──歐陽泰在本書中提出了兩個概念。其一,歐陽泰將所謂的「火藥時代」重新定義為西元 910 到 1900 年,而非傳統的 1500 到 1800 年。其二,歐陽泰透過二手文獻與統計方法指出歐洲長期陷於戰亂,因此軍事發展有長足的長進;然而,當歐洲軍事蓬勃發展時,中國卻正處於清代的「大和平時期」(Great Qing Peace)(1750-1800)。換言之,歐陽泰認為中國不是「不能」或「不行」發展最先進的軍事科技,而是「不需要」。
一如本文開頭所說,歐陽泰反思並且試圖找到修正主義與反修正主義當中的平衡點,他在本書中承認西方軍事在發展過程中具有優勢,包括深海海域的海戰及碉堡建築的技術;然而,中國同樣擁有軍事上的優勢,例如更有效的補給、強大的領導力與更精良的訓練和整合力。
雖然雙方擁有各自的優勢,但在「軍事大分流」中卻逐漸完全地倒向西方,此一現象即發生在中國清代的「大和平時期」。
相較於一般學界對火器運用多聚焦於中國明清時期,歐陽泰別出心裁地重新定義:早在宋代軍事史的發展已經足夠現代化。宋朝為了抵擋金兵的入侵,軍隊已裝備火器並研發出相當優異的守城戰術。
蒙古帝國時期則是火器發展最快速的時期,直到明初就已經體現於軍隊的裝備上。根據歐陽泰的研究指出,在 1466 年,大明步兵裝備火器的比率已經達到 30%,而歐洲要達到這個數字還要等超過百年之後。
對於軍事史而言,「攻城」是非常重要的議題。一如帕克的論點,歐洲軍事革命的誕生歸功於新式碉堡的出現,歐陽泰也承認碉堡建築是歐洲軍事的優勢之一;那中國呢?
歐陽泰指出原因不僅僅在於元末明初火器的口徑仍小,相較於西方用火器來摧毀船艦或城牆,這時期中國的火器主要用於殺敵。更重要的是中國築城的傳統不同於西方。中國長久以來都用石頭、夯土築城,並且具有一定傾斜的角度,較能防禦砲火;相反地,歐洲城牆較薄,是隨著火砲的產生才逐漸增厚,火砲也隨之發展越來越大。
因此,歐陽泰雖然沒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但他似乎暗示東、西方城牆發展以及火器在戰場上的用途,主導了兩方發展的不同。然而,從上述條件看來,中國看似充滿機會成為軍事火器大國,但具有現代意義的火器──較長、較輕、較有效、更精準──是 1480 年左右從歐洲開始演化出來,而非中國。原因為何?歐陽泰在此開始了他本書中最重要的論點之一:和平。
若說要點出歐陽泰書中唯一可惜之處,也許並不是出自他的能力或是忽略,而是出於歷史學界長久以來對於一個地區的忽視與史料的欠缺:中亞地區。軍事史的研究常常著重於耶穌會士鑄造西式火砲對中國帶來的影響,包括明末袁崇煥用紅夷大砲擊敗努爾哈赤、康熙皇帝委請耶穌會士製造火砲對抗三藩之亂等。
但歐陽泰指出火砲的交流早在耶穌會士之前就已經產生──在王陽明平定寧王之亂前,便透過中亞傳入中國,並被明軍所採用,然而歐陽泰並沒有在這方面有太多著墨。換言之,耶穌會士固然扮演著傳入西式火砲的重要媒介,我們卻需要更多資料以及更關注中亞在火砲傳遞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西方學界對於中國軍事史,尤其是火器使用的研究學者並不算多,較為知名的包括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石康(Kenneth Swope)、孫來臣(Sun Laichen),而歐陽泰這本書可謂是從全球角度論述中國軍事史的全面性著作。
在全球史的發展過程中,有一項令人讚嘆、卻同時也令人詬病的問題在於:作者往往使用二手文獻進行論述,而少用第一手文獻或是創新的研究。歐陽泰這本《火藥時代》,不僅豐富地運用了二手文獻,更是透過自身能掌握多種語言的專長,在第一手文獻上下足了功夫。至於文筆優美等,筆者就不再贅述。
最後,筆者希望用歐陽泰在一堂 Seminar 中的話語,來替這本書總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句話似乎也很適合做為這篇書評的簡單結語。
(本文作者為埃默里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