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過地獄之路》是一部戰爭小說,有別於歐陸作家的取材地景,小說的關鍵場景是一條從暹邏(泰國舊稱)曼谷北邊開始,通往緬甸的鐵路。二戰末期,日軍從各戰場搜刮仍有勞動力的戰俘,運送至暹邏,告訴戰俘完成這條泰緬鐵路,即是完成令日本天皇滿意的任務。如此一來,將功抵罪。戰敗是你們的罪,這條鐵路是你們的自救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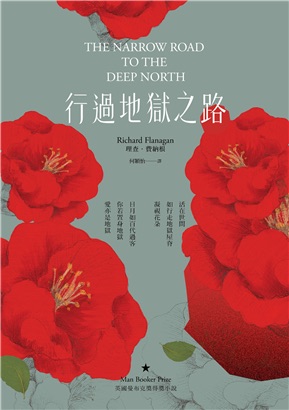
《行過地獄之路》原文書名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 是作者理察.費納根(Richard Flanagan)的心思,他借用日本詩人松尾芭蕉名作《奧之細道》的英譯,中譯則另為華文讀者新譯書名,定調小說文本的屬性。從書名可以約略地推探作者的目的,孕育絕美與至惡的,皆來自同一條產道,無不可能。
泰緬鐵路另稱死亡鐵路,當年日軍以不人道的方式逼迫戰俘,日以繼夜地趕工。苦力使用簡單的工具進行開山挖掘,特別是在 1943 年多數的日子,休息日取消掉了,這段日子被稱 Speedo(速比濤),因戰俘得徒手使勁,如同泳游選手拼命往前衝(可能是澳洲戰俘把自家的泳衣品牌名當作苦中作樂的說法,成為一歷史名詞)過度勞累及營養不良者,仍需繼續勞動。除此之外,霍亂與痢疾如不祥的鐮刀,從沒有離開過戰俘們,那年從笑談速比濤,到苦喊不要再速比濤了。
事實上,這條鐵路沒有成功,從未上路運載軍人及補給,但因之而生的大量的亡魂,早已坐滿另一列陰間列車。

如果說《行過地獄之路》裡只有戰爭英雄杜里戈的人生故事及戰爭本身,是不夠值得推薦,也談不上每頁就能啟發讀者的價值。對讀者來說,幸運的是,這本小說擁有充份的推薦理由,我認為閱讀它,如置入在一群人們的感受裡,體會人如微塵粒子,不停地在時間碎影中翻轉、舞動。精妙又輕盈。人物個別故事有時如同短詩、短篇小說,不需鉅細描繪,也能在我心裡投出清澈且澎湃的形象。
眾多人物交錯並行的筆法,單線式的時間描述不適合,因人們腦海中的思緒感受不走直線式時間軌,抓住人們在這漫長時間洪潮中的感知流動,需要借鏡詩的姿態。
於是這本小說帶領讀者重回古典史詩的豐沛感情,而行文段落則仿擬現代詩的靈動,毫不凝滯,一會兒一道光束,涮下來,是袍澤之情的光輝,它來到我的眼前;另一會兒,一張曾有對比翼鳥繾綣過的床上,他們遺落的一根羽毛飄落到我的心底,更別說一盤炸魚片、一冊被焚燒過的畫冊、一盒萬寶路香煙,它們單零微小,卻飽含每個人的故事,作者理理察.費納根令它們在小說這只雪花盒輕舞飛揚,我愈看愈能著迷。
太初之時為何會有光?這是主角杜里戈一直掛在心裡的提問。
一介讀者的臆測是:有光,人與所愛之人的面目才得以顯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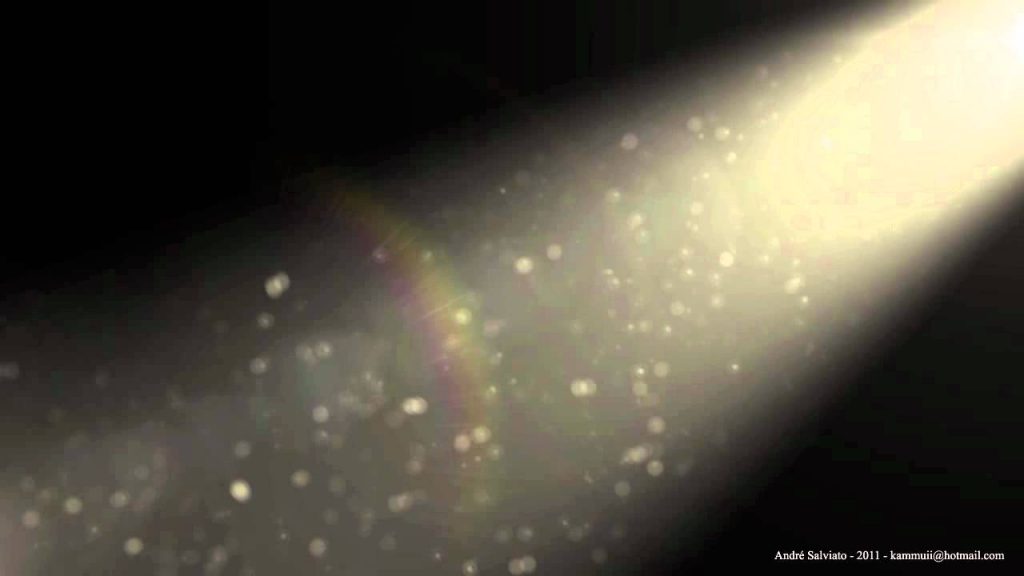
戰時倖存者仰賴死者的光芒,那光芒的燃料是生者對於亡者的記憶,勿忘已逝之人,他們心底才得以有光而生,為他們照亮剩下的細窄小徑,並相信小徑的盡頭與自己的想像相去不遠,他們才得以附著於險峻的戰場上,不致被死亡沖走。
小說裡,同時存在一群光正消散的人,他們的人生餘緒並未被作者給遺棄。
在《行過地獄之路》一書中,別具意義的是,加害一方也有觀視並探索的價值,尤在戰爭之中,加害者是不容易檢視的共犯組成,個別的加害者總是溶於集體的意識之中。小說安排日本軍官中村少佐的生命得以於戰後延長,當他返回戰後敗落的祖國,末世場景下的狼狽掙扎,令我讀起來大為過癮。然後作者運用小說之筆的力道不只如此,在中村的後半生裡,他巧遇另一名戰時醫生,他緩緩道來,自己曾參與日軍對美軍作的活體解剖,最後告訴中村,每個美國大男孩為何會輕易躺上他的手術台,中村第一次有了顫慄與迷芒。
最後中村在生命盡頭之時,猛然的自覺到曾經的天皇信仰,日本精神,可能是至惡的掩飾。惡顯然懂得以美魅惑凡人,他冷汗直流的自我覺察成了《行過地獄之路》最具啟發性的轉折之一,他生命最後一口氣所呼出的絕命詩(臨終之際的俳句),隱然散發出對自己的罪責了然於胸的徹悟:
冬冰
化為清水
我心清明
相較於浸沐在日本古典文學的日本少佐,韓國籍鐵路監工,一名來自殖民國的勞動者,被澳洲戰俘喚作巨蟋的崔相敏,位階是處於戰俘苦力之上,日本軍官的掌管之下。崔相敏來到異國以鞭子教訓紅髮高大的澳洲人,他欣喜持有這股權力,特別白種人和亞洲人是那麼不同,巨大且總是帶著笑臉,亞洲人蠟黃的不只膚色,於是,他愈壓縮這些外國大兵的生存空間,愈能轉換成他渴望的男子氣概。崔相敏沒有受過太多教育,只知道這群外國大兵蓋鐵路真是沒有用,能偷懶就偷懶。他是戰爭食物鍊中的低等雇庸者。
天皇兩字對於日本少佐中村,是偉大的一首詩,實踐天皇要求的任務,就是將神聖之詩置入自己的人生。
同是為天皇的子民,卻面臨戰後清算的鐵路韓國監工,天皇之於崔相敏是佔盡便宜,但責任完全不用承擔,現代黑心老闆的意思。詩性禪意體會與俗世認知重疊在亂世。
在小說裡,作者也透過角色之口道出,人活在時代就是一體性地承擔所有事物。共業二字即可明說此道理,但以故事之姿訴說,我看見的不只是光明面的人性,還有擠滿凡人的惡之闇巷,盡管這窄道上盡是紅色的血、白色的骨頭、黃色的脂肪的濁,卻是《行過地獄之路》給予讀者的秘密甬道。

曾經,杜里戈覺得世間只有一本書,其餘都是甬道。
愛情如崖上之花,再危險也要去一親芳澤。而他生命之書,出現了一雙如瓦斯火焰的藍眼珠。藍眼珠讓所有花朵都失色。他遇見有著一雙如火的藍眼珠的艾咪,曾經如美國大亨蓋茲比志得意滿的人生規畫,自她出現,他突然地失去追逐的胃口。
世界大戰的戰場如惡霧蔓延擴散,戰事截斷了他倆的戀情,戰爭割裂杜里戈與愛咪共享的時間與空間。倆人誤信錯誤的訊息,於是杜里翁在戰場上收到比分手更痛苦的消息。
可以這樣說,杜里戈成為一名戰爭英雄是一件偶然,作為一只會行走陽具卻是他的選擇。戰時,他仰賴信任他的人們,戰後,他不願再去愛,只靠慾念驅動肉體前進,好繼續在眾人面前可以扮演成人、好人,再者是丈夫,又或者是父親。
杜里戈從死亡鐵路歸來,僅抓回肉身,失魂的他,活著的每一口都像嚼著蠟:
活在世間
如行走地獄屋脊
凝視花朵—小林一茶
不只這對比翼鳥,小說裡,一位戰爭遺孀的無語思念,也是另一種愛情的地獄。另一只羽翼不在身邊,我怎能飛得上天,後來我失去抬頭的意願,開始抗拒光,光對我不再有意義,因為再沒有想看得清楚的人,與她的瓦斯火焰藍眼珠。
母親是人生的第一個奇蹟,艾咪妳是母親之後,更好的,獨一無二的,我的新奇蹟。
我在戰爭中所創造的,所拯救的,所拼搏的,都不及妳那天在書店裡,向我走來時,所佩帶的紅色山茶花。曾經撫摸過一個戴著紅色花朵的女子,雙手才能承受乾了又溼、溼了又乾的血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