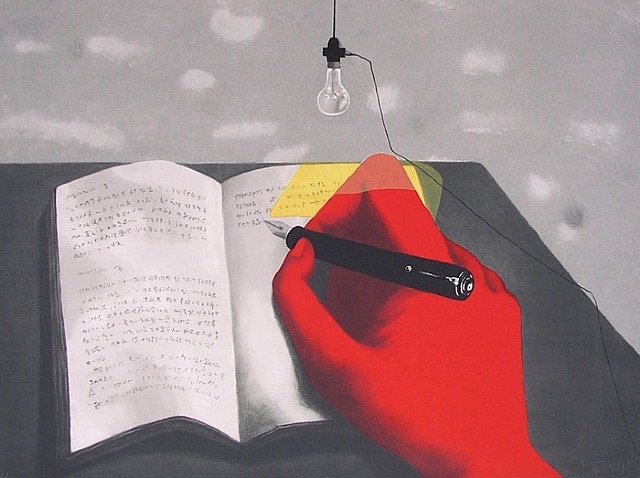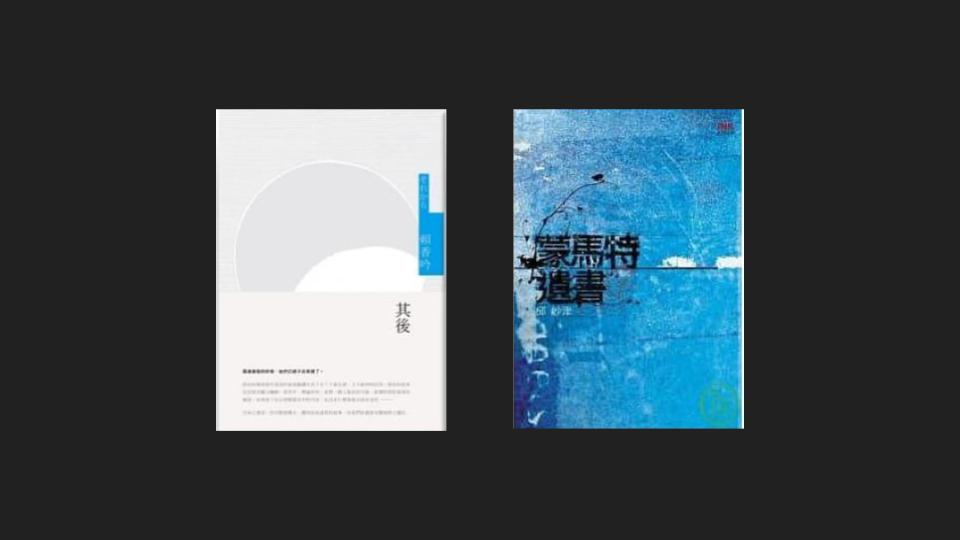握著各式雜誌印出來的紙張,讀著上面言叔夏的文字,常在想:甚麼時候她才要再出書呢?一幀黑白小照片上女作家抿嘴微笑,讓人想到〈塔〉[1]裡面提到三十多歲的她去做牙齒矯正。牙齒對言叔夏而言,是什麼樣的存在?一種有自由意志,需要人去學習與之共處的器官嗎?小時候牙齒掉了會再長,長大以後,蛀缺掉落的牙就是失落了。「如果我們的牙齒都會不斷地長出新的來,我們還會每日早晨起床重複那荒謬的刷牙動作嗎?」這是出自〈尺八癡人〉[2]的句子。
重複的刷牙,為的是抵抗牙齒蛀落;如同重複的書寫為的是抵抗生命的欠缺。
言叔夏亦曾在訪問[3]中提及自己對於同樣經驗的反覆書寫,「有點像復健的過程」,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重複書寫,讓生命中的傷痛慢慢痊癒。我常感覺她的語言像繁複的摺紙技藝,讀者按她的思路步步跟隨,但她往往幾個跳躍性的步驟,很快就將他人拋在原地,讀者只能帶著迷疑看著文字在她手中千變萬化,忽然就變出一朵花來。經驗是白紙,摺紙成花、將相同經驗予以轉化、昇華的行動,即是一種拯救的姿態。〈白菊花之死〉:「你已如此誓言要永保此生乾燥,麗如夏花;你已如此誓言要以之抗拒匱欠與失去。」[4]
然而同一則訪問當中,她也說:「現在書寫對我來說,純粹只是一種說話的練習。最初似乎只是自我的核心,但現在,我想要去告訴另外一個人什麼東西。」原先將書寫作為個人生命經驗的譯寫,以達「拯救」之目的的寫作方式,已經漸漸改變。不過,就其至今未集結成冊的篇章而言,經驗的複寫依然是她一項重要的寫作策略;不一樣的是,過去作品中晦澀的詩意逐漸簡化(但依然優雅迷人),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辯證語氣。那或許接近她在與童偉格的對談[5]當中所說的:將樓梯(經驗)燒燬,以得到閣樓(知識殿堂)的光明──這樣一則援引自阿甘本的隱喻[6]。
這或許聽來抽象。在那場對談中,言叔夏對於自身生命的時間軸,做出了一個精妙的比喻。她說,感覺自己活在一個螺旋狀不斷前進的時間軸上。這樣一個時間軸,若將之拉直則成線性(一般人衡量時間的觀點),然而從上往下俯視,卻成為環狀(一個首尾連貫,起源與結束相接的時間軸)。行走在這座生命軸線上,當一個人途經A點,再往前進(旋轉)一百八十度來到 B 點,能夠看到當初他所身處的 A 點;再往上一百八十度,來到 C 點(A點的上方),又會與 B 點照面;再往上一百八十度的 D 點(B 點的上方)既能看到 C 點,亦能看到 A 點……如此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時間觀。
而這許多、許多點與點連線的凝視目光,即是對於經驗的重複書寫。時間軸中央,那被軸線所圍繞的空無核心,應該就是生命的本體吧。我常覺得言叔夏的文字,往往是從現實被召喚入過往,那夢境一般的歷史,或歷史一般的夢境,最後再被遣返回現實(「在寫作時,我常覺得不是我在寫這些內容,而是這些東西在複寫我」[7])。
這樣的時光旅行,經過的就是那空無的核心;那是唯有透過潛意識夢境才能夠抵達的純粹,黑暗。如同她在〈故鄉的重量〉[8]中所說的:「是寺山的電影教會了年少的我,只有在沒有光的地方,夢境才會發散出那種琥珀色的光澤。」也是在那種琥珀般寧止一切的時空間,才能讓她慢慢將經驗重新翻譯。這大概也能夠解釋為甚麼,言叔夏如此依戀黑暗(「那種黑色一直讓我感到非常地放心。我後來就成為一個在那種黑色裡生活的人。」,〈白馬走過天亮〉[9])。
然而,燒燬?
最初在言叔夏口中聽到「將經驗的樓梯燒燬」這樣的話,令我極為不解:何以如此?又,如何做到?回顧她的諸多篇章,「燒燬」的意象讓我想到的是〈賣夢的人〉:大學教室裡,塔可夫斯基的電影之中火勢燎原,「一整個時代在螢幕上全部燒光,燒得乾乾淨淨」[10];以及〈白馬走過天亮〉[11]中所提到的〈為愛痴狂〉,劉若英在 MV 最末,將「在秋天說要分開」的情人的吉他與大衣,點燃打火機燒掉,作為紀念與告別,對應到九〇年代的逝去。言叔夏的書寫,總彷彿經歷過一個甚麼;不知不覺之間,她就從世紀末來到世紀初,從東部到臺北,巴別之前到巴別之後,天黑到天亮。「白馬走過天亮」的隱喻本身,除了「白駒過隙」的意涵之外,是否也寓有「白馬非馬」此一名家的經典辯題?天亮之後,辯術遂興,再回不到純粹的黑。
因此,燒燬,大概就是像〈壁上的字〉[12]所說的那樣:「不遠處有歷史在火堆裡嗶嗶剝剝地燒著,燃燒殆盡以後,它會在未來的哪一本書上被以史前的文字寫下?」一種末世之後,來世之前的書寫行動──重新定義過去的經驗,賦予它在此時此刻所需要被詮釋的意義。
從這樣的思路出發,我們能發現,其實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對後世之人而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觀看歷史的人,能從所知的歷史當中得到甚麼樣的有用之物。站在歷史兩端的人所關注的面向,是完全不同的。如同一篇作品對於作者的意義,以及一篇作品對於讀者的意義,無法放在同一個標準上去衡量。好比〈鴿樓與瘋女〉中,那些夢境片段一般、關於家鄉的描述,反覆出現的謎樣意象:鴿樓,鴿子,陰天,瘋女人……或許原本就不是外人所能輕易理知進入的一個世界──那是作者本人,對自己身世起源的探究。
言叔夏所在進行的,像是對自我身世的考古工作。那自廢墟中挖掘出土的,已然質變的文物(經驗),連結了身處兩端的考古學家(此時此刻)以及埋藏者(事件發生當下),時差於焉產生。時差的意思是,平行的兩者同時按著自己步子走,沒有誰先於誰;事件的發生並不先於回顧事件的寫作者,寫作也並不先於閱讀。〈鬼魂與觀音〉中問道:「繩結斷裂的時候,有什麼正在敘事的上方凝視著我?」[13]
如此說來,言叔夏的寫作所欲達到的,也就並不僅止是對於自身經驗的考古,而同時,也有占卜的成分:透過回顧過去,思索未來之可能。過去,現在,未來,就是旋轉時間軸上的 A 與 B 與 C。處在當下的人凝望著過去的經驗,而背後有未來正凝望著當下的你。「那保羅・克利的新天使目視著歷史,也從沒料想腦後的一雙眼睛,直直地盯著他的後腦杓。」(〈一〇年代記〉)[14]。
以此角度觀看她的文字,能夠理解許多連結了兩個次元的意象:電話,鍵盤,廣播,歌……。〈天涯歌女〉是她很近期的一篇文章,當中說到她聽石川小百合唱 2010 年版的かくれんぼ(〈捉迷藏〉):「不知年逾花甲的石川在播音室裡重新唱起這首初出道時的歌,會有什麼樣的感受?是否也會覺得這半生唱過的冬雪北地與南方之海是かくれんぼ一種?」[15]貫穿了過去經驗的演繹,與演繹的重新演繹。讓人不禁想及過去待過高雄、花蓮、臺北,而今定居於臺中的作家本人,是否也抵達了一個適宜於追憶的時空?
日常生活中,她依然攀爬在她的時間軸上(以抄寫員巴托比,或者出入地道之姿?),依然表演賣藝;時間中每一轉彎處、每一站駅、圓的切點,都是一個事件,一個人名或地名(那些 C 城,E,O…),一張臉孔。〈塔〉的結尾:「當他用鑷子撬開我的嘴巴,先於我的人見到了我口腔裡拔牙的缺口,也會把我的缺口,當作臉來凝視。」[16]而在這樣的「臉書時代。無夢時代。/用一張臉寫一本書的時代」(〈賣夢的人〉)[17],她用一張張的臉孔,一次次重複譯寫過去的經驗,摺出一朵朵的花。
像是回到〈尺八癡人〉[18]開頭的夢境裡,國小數學課上的小女生被叫上黑板;面對世界複雜的算式,三角形的傾軋,教室外的戰爭,她感到困惑。但她只是圍繞著黑板上的圓心,不斷畫出一片片的花瓣,一瓣,一瓣,又一瓣。那是她給世界的回答,她對抗世界的方式。如此純粹,又如此美麗,讓旁觀的人,深深地為之動容。

[1]言叔夏,〈塔〉,《聯合文學》2017 年 八 月號,頁 118-120。
[2]言叔夏,〈尺八癡人〉,《白馬走過天亮》,臺北:九歌,2013,頁 98。
[3]神小風,〈生命本身的雜亂會自成姿態──專訪言叔夏《白馬走過天亮》〉,Bios Monthly。網址:http://www.biosmonthly.com/interview_topic/3726
[4]言叔夏,〈白菊花之死〉,《白馬走過天亮》,臺北:九歌,2013,頁84。
[5]講題「書寫生命的姿態」。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3zc90ens。
[6]據言叔夏所說,是來自阿甘本《幼年與歷史,經驗的毀滅》一書。
[7]翟翱,〈霧裡的馬都是白色的〉,《聯合文學》2013 年十二月號,頁 45-47。
[8]言叔夏,〈故鄉的重量──用寺山修司的煙草指向北方〉,Bios Monthly。網址:http://www.biosmonthly.com/collection_topic/5822
[9]言叔夏,〈白馬走過天亮〉,《白馬走過天亮》,臺北:九歌,2013,頁 87。
[10]言叔夏,〈賣夢的人〉,《聯合報》,2015 年 5 月 25 日。
[11]言叔夏,〈白馬走過天亮〉,《白馬走過天亮》,臺北:九歌,2013,頁 85、91。
[12]言叔夏,〈壁上的字〉,《聯合文學》2017 年三月號,頁121。
[13]言叔夏,〈鬼魂與觀音〉,《聯合文學》2017 年二月號,頁111。
[14]言叔夏,〈一〇年代記〉,《文訊》2017 年六月號,頁16。
[15]言叔夏,〈天涯歌女〉,《文訊》2018 年三月號,頁21。
[16]言叔夏,〈塔〉,《聯合文學》2017 年八月號,頁120。
[17]言叔夏,〈賣夢的人〉,《聯合報》,2015 年 5 月 25 日。
[18]言叔夏,〈尺八癡人〉,《白馬走過天亮》(臺北:九歌,2013),頁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