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宮崎駿的電影裡,飛行總是一個重要的元素;他對於飛行的執著與熱情素為廣大影迷所熟知。於是在他的收山之作《風起》(2013)裡,宮崎講述了一個關於飛行的夢想的故事。然而這部作品在日本卻得到了毀譽參半的評價:業內人士如動畫片導演細田守肯定本片的成就是「前所未見」,但一些批評家卻極力批判本片的歷史觀。而對於臺灣觀眾來說,本片的題材和宮崎用的許多哏也都不那麼熟悉。好比說,多數人都知道本片是以飛機設計師崛越二郎(1903-1982)的生平為藍本,但對於宮崎的另外一位致敬對象崛辰雄(1904-1953)卻非常陌生。

崛辰雄是何許人也?他是二十世紀前半的日本小說家,與本片主人公崛越二郎是同時代人,和另一位知名作家芥川龍之介(1892-1927)也是至交。宮崎駿的動畫電影《風起》,正確地說,是在崛越二郎的前半生故事中,加入了崛辰雄的小說《風起》(以及其它作品)的情節,揉合而成的改編電影。這部電影有兩條主線:二郎的飛機夢,以及他和菜穗子的戀愛故事。我認為要理解這部電影可能可以由兩股脈絡來看:
首先,本片是宮崎對於崛越二郎、崛辰雄兩人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的致敬、反省之作。《風起》和宮崎先前的作品相較,呈現出了非常濃厚的時代感,對於 1920~30 年代日本社會的躁動不安有著簡潔但精準的描繪:大正時期相對開放的時代風氣已經結束,經濟景氣低迷,貧富差距嚴重,社會氣氛壓抑,軍人日益好戰,日本正走向戰爭。對於宮崎駿這批成長於戰爭末期到戰後初期的日本人而言,「戰爭」始終是一個引人深思的重要課題,包括近來日本的憲法爭議(宮崎自己也做過許多相關發言),都可說是戰爭的遺絮。我認為《風起》這部電影意圖探討的議題是:生存在那個大時代的個人和現實環境的關係是什麼?個人的生命意義又能夠超越時代嗎?
再者,我私心認為本片帶有半自傳的性質。熟悉宮崎駿作品的影迷在觀看本片時,想必都想起了他另一部以飛機(與中年大叔)為主題的電影《紅豬》(1991):從故事主題、橋段乃至於對 1920 年代飛機工藝的刻畫,都能看出這兩個故事的關聯性。眾所週知地,《紅豬》是當時年近五十的宮崎駿的生涯回顧之作。而《風起》對於崛越二郎生平與夢想的探討,在我看來也正隱含了宮崎對於自己創作生涯的回顧與反省吧。
所以我強烈建議:如果你想看《風起》,請務必先去找《紅豬》來看。看懂《紅豬》絕對有助於理解《風起》,而且《紅豬》超有趣的。好豬,不看嗎?
「戰爭責任」
在故事裡,崛越二郎從小就喜歡飛機,夢想著能成為飛機設計師。電影裡的他多次在夢中神遊,與義大利的名飛機設計師卡普羅尼(Giovanni Battista Caproni) 神交。縱觀全劇,他與卡普羅尼每次在夢中相見,都呼應了劇情的轉折。

第一次見面時,二郎還是個 10 歲(?)的小孩。在夢裡卡普羅尼帶二郎參觀了他造的飛機,點燃了二郎造飛機的夢想......聽起來是個很光明的故事吧?但在這裡宮崎卻仍藉由卡普羅尼之口說出,「他們(飛行員)要去和敵人作戰。他們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能回來......」而在二郎一開始的夢境中,他駕駛飛機翱翔天際,最後卻被炸彈擊中而墜落。也就是說,戰爭的陰影始終是存在的,二郎從小就已經意識到,飛機終究是要成為殺人的武器的。正如卡普羅尼所說的,「飛行是人類美麗的夢想與詛咒」。
那麼二郎是怎麼看待這件事的呢?在電影中,雖然他不斷地意識到戰爭即將到來,也不時會表達出他對軍隊的不以為然,但二郎似乎並不特別抗拒為軍方的需求服務。觀眾看到的二郎,是一個為了實現飛機夢而不顧一切的青年工程師,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不惜把染病的菜穗子留在身邊),卻看不太到他對於戰爭的看法。即使一度成為「特高」[1]監控、壓迫的對象,二郎卻仍努力地完成他被交付的任務。
直到電影最後,夢想完成了,但夢想的成就卻毀滅了國家。當他又和卡普羅尼在夢中的草原相見,他感傷地說道「我完成了夢想,卻已心力交瘁......他們(「零戰」的飛行員)沒有一個回來......」在此時崛越二郎才似乎真正面對了戰爭,以及自己夢想的矛盾之處。然而透過(應已死去的)菜穗子「活下去」的呼喚,二郎又拾回了活下去的力量。
在這裡,宮崎駿似乎暗示了個人的夢想、個人意義的追求是可以超越現實環境與外在力量的拉扯的:即使飛機最終成了殺人的武器,但二郎仍造出了美麗的飛機。但這難道是在為崛越二郎的「戰爭責任」開脫嗎?《風起》在日本受到的批判,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這類的地方。批評者多半認為宮崎對於戰爭的態度過於曖昧,對於崛越二郎作為殺人武器製造者的身份欠缺批判。或者可以說,這些批評者認為《風起》欠缺對於歷史的批判精神。
我認為宮崎駿確實是以近似「同情與理解」的角度來看待崛越二郎其人,寬容地看待他的飛機「毀滅了國家」這件事。但我也認為,宮崎並非只是要歌頌崛越造出飛機、實踐夢想的功績。他想討論的是更深沈的東西。
崛辰雄與〈風起〉
要理解宮崎駿的想法,就必須提到崛辰雄的〈風起〉。這篇中篇小說寫的是一位青年陪伴他染上肺結核的未婚妻前往高原上的療養院養病的故事。這個故事是取材於他自身的經驗,崛本人是肺結核的患者,他的未婚妻矢野綾子也同樣染有肺病。[2]兩人訂婚後的第二年,綾子便因病赴山間的肺結核醫院醫治,並在同年冬天死去。崛便以這段經歷寫下了〈風起〉。[3]
小說〈風起〉描述「我」和「節子」相處的點點滴滴。「我」在故事中雖然沈浸於和「節子」共同生活的幸福,和「節子」共同感受著戀愛與生命的喜悅美好,但也不斷意識到死亡的步步進逼。於是「我」決定寫一篇小說,記敘自己和「節子」的故事:
我想把你的事寫成小說,除此之外我什麼都沒法想。我們現在給予彼此的幸福——從世人認為走投無路的絕境,萌發出對生命的喜悅——我想把這沒有人知道、僅屬於我們的感覺,轉換成具體的小說,好嗎?
但當他開始構思小說的劇情時,「我」卻發現自己不得不面對戀人終將死去的可能結果。「我」幻想著小說的女主角將在結局死去,並在臨終前感謝男主角帶給她的幸福,而這則讓男主角振作起來,相信兩人間的小小幸福。「我」想到這裡,便無可抑制地對「節子」產生了羞愧交雜的歉疚感和恐懼。「我」希望能藉由寫下小說,讓自己和「節子」都能肯定兩人經歷過的幸福時光,但他也不斷地懷疑自己是否真的了解「節子」的想法?又是否,自己其實只是強將自己的夢想加諸於「節子」身上呢?
「節子」還是去世了。在「節子」死去三年多後,「我」回到了當初與「節子」相識的山谷過冬。「我」不停地想起與「節子」的過去而感到孤獨悲傷。但「我」在讀了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的《安魂曲》(Requiem)
之後,逐漸接受了「節子」的死亡,重新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並確信了自己與「節子」的愛是真實而有意義的:
......或許我現在的狀態更接近一種幸福。或者,也可以說,最近我的心境是類似幸福卻又比幸福多了少許悲傷而已......不過,節子,我從來沒有將這樣孤獨的生活怪罪於你。我只是為了我自己做著我喜歡的一切,也許,雖然這一切都是為了你,但是我已經完全習慣了自認配不上你對我的愛,以至於認定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自己。
於是就在此刻,「我」終於得到了救贖,重拾了對生命的熱情。崛辰雄想表達的,或許就是在走過死亡與幻滅的幽谷後,生存下來的人仍要在餘燼中找到前進的力量,相信生命的價值吧。風起了,唯有努力生存,而崛辰雄在他的小說中所揭示的生存的意義,也就是愛。那麼,宮崎駿又是怎麼消化、改編崛辰雄的故事呢?
「唯有努力生存」與男人的浪漫
說來「努力生存下去」一直是宮崎駿電影的一大主題。從《風之谷》(1984)到《魔法公主》(1997),宮崎在他一些比較嚴肅的作品裡,常稱頌主人公在艱困的環境中秉持純正堅毅的心靈、對抗外在力量的壓迫與人為的愚行。他也肯定那些樂天知命努力生活的小人物:在《紅豬》裡,他便藉由菲兒和保可洛工廠的大家族肯定了一種小老百姓在逆境中求生存的生命情調。而在《風起》一片中,二郎造飛機的故事以及他與菜穗子的戀愛,也正是這個命題的兩個面向。
菜穗子可能是宮崎駿打造過的角色中最接近於「夢中情人」的一個。她在電影裡和二郎有著「宿命的邂逅」,又在多年後偶然重逢,兩人在水池邊相認的一幕浪漫得一塌糊塗,在黑川家的那場婚禮更是閃瞎了數以萬計的觀眾;她體弱多病,卻仍堅定地支持著二郎的夢想,直至生命的終點將屆......有女如此,夫復何求啊。(笑)
這樣的設定看起來似乎相當老派,有著宮崎駿作品中罕有的「大男人」氣息。二郎與菜穗子結婚之後,二郎的妹妹加代來訪,並質疑哥哥為什麼要把病重的菜穗子留在身邊。二郎的回答是「我也知道......我們非常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天,過得非常幸福」。乍聽之下真是混賬啊!這樣的劇情安排大概可以說是一種(臭)男人的浪漫,但宮崎駿的深意也就藏在這個地方。
片中菜穗子獨自從山上的療養院前往名古屋,在車站與二郎重逢的場景,是改編自崛辰雄另一篇小說〈菜穗子〉的情節:孤獨地在山上養病的女主角衝動地跑回東京,暗自期望丈夫能開口挽留自己;但丈夫卻顧慮著母親(與女主角合不來)的態度,也無法理解女主角為何這樣衝動地回來。失望的女主角只好表示自己翌日將獨自回到山上。電影裡二郎的那句「別回去了,留下來和我一起生活吧」,其實正是小說中女主角期待丈夫能說出口的台詞。宮崎卻將這句話藉二郎之口說出來了。[4]
顯然地,電影裡的菜穗子自己也是希望能留下來的。儘管一開始,菜穗子是自願前去山上療養的,但她最終卻毅然地離開醫院回到二郎身邊。這個抉擇或許反映了菜穗子如何看待自己生命的意義:前去山上是為了求生,但比求生更重要的,卻是讓自己的有限的生命完滿、美好。所以菜穗子選擇追求愛情,與愛人共同生活,甚至不惜因此加重自己的病情。在這裡,菜穗子和二郎的戀情便呼應了崛辰雄在小說〈風起〉中所揭示的、以「愛」為最高價值的生命態度。所以電影裡的二郎才會坦然地將菜穗子留下來,因為只有菜穗子留下來,他們兩人才能透過彼此的愛共同「努力生存下去」。而這「努力生存」的目標,便是要讓二郎造出美麗的飛機。

然而,就在二郎的飛機試飛成功的那一天,菜穗子悄悄地離開了。前來探望的加代正想奪門而出將菜穗子追回來,卻被黑川太太勸阻;她說菜穗子是希望「讓最愛的人只看到她生命中最美的時刻」。我想這番話的另一個意涵是在於,菜穗子自認已經完成了生命中重要的使命了。而當美麗的飛機在天空翱翔,菜穗子與無數人的生命仿佛也隨風隕落了。於是畫面立刻轉到了化為「地獄」的夢中草原。二郎的那句「我完成了夢想,卻也心力交瘁」,便有了格外動人哀傷的意涵。自己的夢想,帶來的除了國家的滅亡,是否也帶走了生命的意義呢?
在夢中,無數的「零戰」在二郎的注目下緩緩上升,匯流進高空上的飛機雲河。同樣的場景也曾出現在《紅豬》當中:波魯克向菲兒講起戰爭時的瀕死經歷,目送著摯友的飛機飄向高空。戰友們都死去了,只有自己苟活下來。波魯克在這裡講出了一段名台詞:
好人都已死去了。而且誰知道他們前去的地方是不是地獄呢?
好人都已死去了,活下來的波魯克就只能是「壞人」,背負著戰友和對手的性命。《紅豬》的波魯克自覺自己是有罪的,為此煎熬不已;《風起》的二郎大概也抱持著類似的心情吧。不過宮崎駿終究為他的角色提供了出路:波魯克因菲兒的愛和生命力得到了救贖;至於二郎,則在菜穗子的呼喚聲中重新確認了自己生命的意義:無論是造飛機的夢想抑或是對菜穗子的愛,終究都是有其意義的。而這樣的信念,也為往後的生命開啓了新的可能。
然而,至此還是必須回到最初的問題:宮崎駿在這個故事裡到底對日本的侵略戰爭展現了怎麼樣的態度?
飛機夢、帝國夢與神秘老外
在電影中,二郎的飛機夢面臨諸多外在的限制:日本的國力遠遠不及歐美先進國家,技術上也大幅落後。在此情況下,唯一有充分資源能支持二郎造飛機的,也就只有軍隊。電影裡用了很大的篇幅講述外在條件的困窘,並且用了數個場景(沿著鐵道走向城市的民工、擠兌的市民、拒絕西伯利亞蛋糕的小姊弟......)暗示二郎的夢想是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方能實現。在二郎對本庄提到那對小姊弟的事情時,本庄以嘲諷的口吻指謫二郎「偽善」,指出他們所參與的計劃的花費「能讓全國的小孩天天吃上天婦羅蓋飯和西伯利亞蛋糕」。這等於是明示了,二郎、本庄等人對這些窮苦人的處境是有一份責任的。
可是本庄卻也隨即承認,即使如此他還是要幹這份工作,實現造飛機的夢想。二郎雖未明說,但從之後的劇情來看顯然也贊同本庄。我認為宮崎駿的想法非常值得玩味:他當然同情這些在大時代下沒沒無名的平頭百姓的處境;而儘管他似乎始終稱頌著二郎對夢想的追求,但他其實也清楚地點出,二郎若要追求夢想,便必須要背負著這些責任生存下去。而若順著這個思路繼續往下推,二郎身上的「戰爭責任」也就很明顯了。
要探討宮崎駿對於這段歷史真正的看法,就必須談談那位出現在山間旅館,吃著水芹唱著民謠的神秘老外卡斯特洛普。設定上,卡斯特洛普是德國人,而從他神出鬼沒的特性、迅速看出二郎的背景以及日後遭「特高」追蹤的情節來看,宮崎應是在暗示此人是一個間諜。這樣的設定很容易讓人想起另一個在日本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理查·佐爾格(Richard Sorge, 1895-1944)。

佐爾格是德俄混血,年輕時受共產主義思想影響,加入共產國際,並且被蘇聯情報機關吸收,為蘇聯當局蒐集情報。他以記者和納粹黨員的身份為掩護,常年活動於東亞地區,並於 1933 年開始於日本建立諜報組織,在二戰期間為蘇聯搜羅到許多重要的情資。他的組織在 1943 年遭日方破獲,他則在次年遭到處決。
在某個晚上,卡斯特洛普跑來找二郎搭訕。卡斯特洛普說道:
這裡是遠離凡間俗事的『魔山』,在這裡人們會把那些俗事通通忘掉:和中國的戰爭,忘掉;滿洲國的事,忘掉;退出國聯,忘掉;與全世界為敵,忘掉。
「魔山」的比喻相當有意思。「卡斯特洛普」(Castorp/カストロプ)這個名字其實就是取自湯馬斯曼(Paul Thomas Mann)的名作《魔山》(Der Zauberberg)的男主角。卡斯特洛普將這座山間旅館比擬為「魔山」,其實也是在批判當時的日本人(或許也包括二郎在內)無視於迫在眉睫的戰爭和日益艱困的局勢。但有趣的是,這位卡斯特洛普同時也是二郎與菜穗子的戀情的推手,加入了他們兩人「你扔我撿」的閃光遊戲裡頭。他與二郎等人顯然在那「魔山」上有著良好的情誼。
歷史上的佐爾格被認為是一名理想主義者,他為他的理想獻身,吸引許多日本人追隨,留下了許多傳奇事蹟。宮崎駿在《風起》中,則明確地對卡斯特洛普抱有正向的評價。而,儘管卡斯特洛普嚴厲地批判了日本人(特別是上層階級)的醉生夢死,但他似乎卻仍對二郎的理想抱有敬意。宮崎駿藉由卡斯特洛普批評戰前日本的歷史,我認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承認了崛越二郎的「罪愆」,但他也同時把崛越看作一位理想家,並對他的這個面向表達肯定之意。
回到《紅豬》出現過的一個場景:保可洛工廠的老爹帶領著他的員工們進行飯前禱告,祈禱上帝原諒他們「以女人的手製造武器的罪」,然後哈哈大笑地要大家「多吃一點,吃飽了努力工作」。造武器是有罪的,但為了生存下去卻是不得不然。這或許也可以和《風起》中二郎隱而未顯的心態交相呼應吧。
理想家的宿命與宮崎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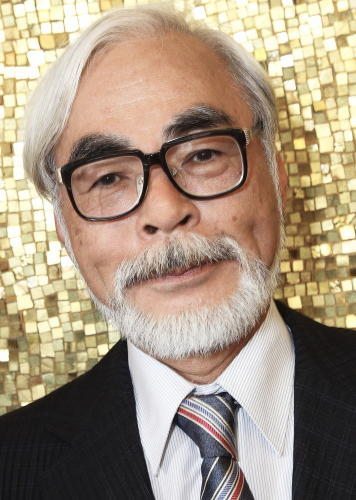
在一篇影評中[5],評論者宇野常寬批評宮崎駿雖然看似推崇「熱鬧的大家族」意象,在表面上稱讚卡普羅尼滿載家人員工的大飛機,骨子裡真正想要的卻是「苗條、禁慾」(而且孤獨)的殺人武器「零戰」。我認為這個說法只對了一半,基本上宮崎駿對於和樂喧鬧的「大家族」(《天空之城》(1986)的朵拉奶奶和他的兒子們、《紅豬》保可洛工廠的女人們、《魔法公主》達達拉城的女人們......)確實是持正面看法。微妙的是,在他的作品中,英雄卻常是獨行的。
《紅豬》的結尾,波魯克打敗了卡地士,但他仍拒絕了菲兒的愛情,把菲兒扔到吉娜的飛機上,要吉娜「把這孩子帶回正常人的世界」。波魯克的意思很明顯:他要走的是「不正常」的、危險的道路,而他不願把菲兒(還有吉娜)捲入其中。換句話說,若真的要背負起夢想,人勢必只能走上孤獨的路途。所以與其說《風起》中二郎的理念是和卡普羅尼對立的,倒不如說二郎的追求理想之路原本就是孤寂的。
當然,宮崎為《風起》的二郎安排了與菜穗子的戀情,將兩人相互扶持追尋理想的過程描繪得極其唯美動人,但終究菜穗子還是死去了。菜穗子的死或許可以看作二郎為實現夢想所付出的代價之一。在片末,二郎面對卡普羅尼「是否認真地活過了這十年」的問題,疲憊地坦承儘管自己確實已全力以赴完成夢想,但「卻已心力交瘁」。這裡的「心力交瘁」,除了見證夢想的幻滅,自然也包括了對菜穗子的歉疚。
我認為宮崎駿在這裡所揭示的是他自身的生命態度。儘管宮崎讚賞人與人之間真摯的情感和「大家族式」的人際關係,但他卻隱然地提示了,自己這一生走的並不是這樣的道路。從《紅豬》到《風起》,波魯克和二郎都選擇去實踐自己的生命意義、理想,孤獨地走上自己的人生旅途。雖死猶生的菜穗子要二郎「活下去」之後便化做幻影消失了,留下來的二郎,在與卡普羅尼喝過紅酒後,仍有大半的人生要度過......「活下去」並不只是單純地活著,而更是要持續為未了的生命旅程奮力找尋新的意義。
我相信這是宮崎駿帶給觀眾最重要的訊息,同時也是宮崎對於自己生涯的總結。《紅豬》還有一個很有名的橋段:被卡地士擊墜的波魯克撥了電話給心急如焚的吉娜,吉娜在電話中要求波魯克放棄充滿兇險的飛行生涯:
「馬可,你總有一天會變成烤乳豬的。我不要,我不要這種結局。」 「不能飛的豬是沒用的豬。」 「笨蛋!」
此時的波魯克渾渾噩噩地度日,除了飛行以外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該做什麼。但即使如此他還是只能飛行下去,而不願走進吉娜的花園。自《紅豬》至《風起》已過了二十年,宮崎駿未曾停歇自己的創作。或者可以說,宮崎也不願成為那隻「沒用的豬」吧。而二十年過去,這隻飛行的豬,也終於飛抵了他的終點。「我的十年已經結束了」,而宮崎駿毫無疑問地,在他的「十年」裡發揮了全部的力量,完成了偉大的業績。就這層意義上,《風起》是宮崎駿當之無愧的收山之作。
《風起》上映以來招致了不少批評和不諒解;這是一部很不「宮崎駿」的作品,有許多幽微難解的片段,也不是那麼有娛樂性。但我私心認為,本片無疑是宮崎駿在他的吉卜力時期中最了不起的作品之一。他將畢生的心血都投注在這部作品上,在生涯的最後講述了一個屬於他的、反映其精神、關懷和生命歷程的故事。《風起》必然無法達到《神隱少女》在票房與獲獎的成就,但本片的價值卻是難以取代、忽視的。

[1]「特高」,全稱「特別高等警察」,是戰前日本的秘密警察。
[2] 輕井澤是崛辰雄許多作品的舞台。他因肺病的緣故自年輕時就常待在輕井澤養病。他也是在輕井澤與矢野綾子相識相戀的。而,《風起》電影中二郎和菜穗子墜入情網的山間旅館便是設定在輕井澤。
[3] 崛辰雄的創作與生平,可見賴明珠為〈風起〉小說中譯本寫的導讀文章。 http://news.msn.com.tw/news3339916.aspx
[4] 我自己還沒讀過《菜穗子》,是從劉黎兒對宮崎駿的專訪中得知這個典故的。劉的專訪文章可見:
- http://news.chinatimes.com/reading/11051301/112013091600043.html
- http://news.chinatimes.com/reading/11051301/112013091700047.html
[5] 宇野常寬,〈鳥並非抵抗重力飛翔──『風起』影評〉 ,http://blog.livedoor.jp/aarinoshitw/archives/3195903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