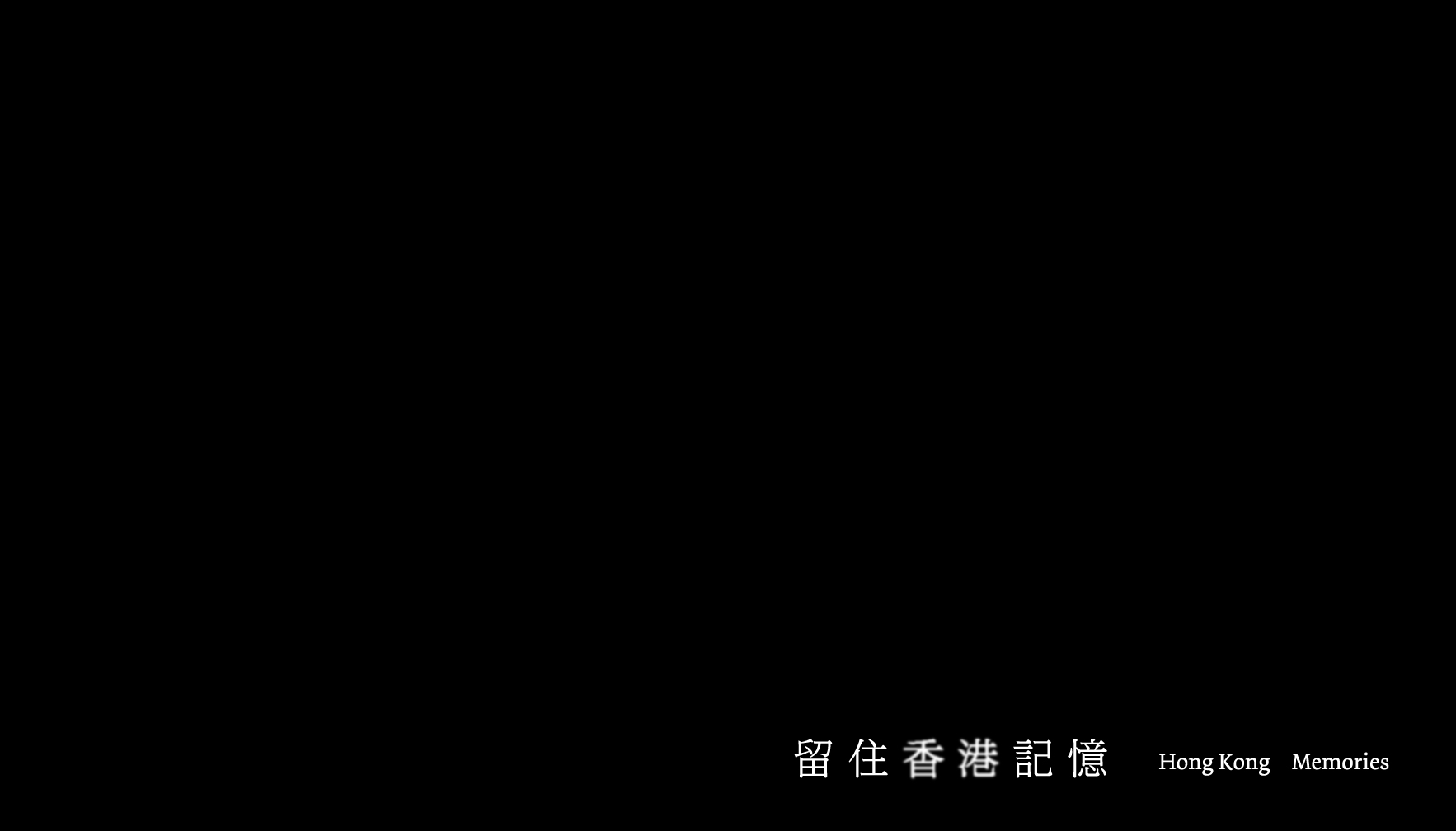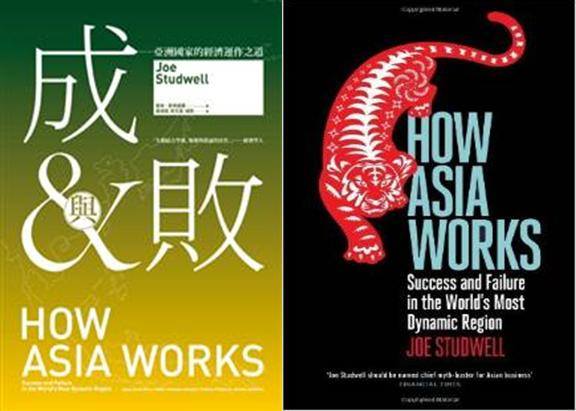在當下的國際討論,「世界主義」並非自明。例如今年七月剛出版、探討現今政治哲學裏各種具爭議性議題的新書 Current Controversie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第一章問的,就是在現今世界脈絡下,我們需否全是世界主義者。
2013 年,劍橋大學出版、從法律與政治角度思考世界主義的專書 Cosmopolitanism in Context:Perspec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其中一個章節就是專門思考移民是否人權一種,而該論文作者的觀點,是外來移民情理上沒有凌駕性權利,原因是本地人的意願亦同樣重要、需要重視。
即使比利時學者 Marco Martiniello 在其著作《多元文化與民主:公民身份、多樣性與社會公正》(中譯本)主張較寬容的人口政策,但其立論重點亦非抱持香港某些論者常說的「本土等於狹隘排外」這種過於簡化的立場。Martiniello這樣寫道:「民主型多元文化主義承認不同文化、族群/種族和宗教群體之間互動、交流對話的重要性,但在此之上,它也為承認和發展族群/種族、文化或宗教群體內部集體生活留了一個空間。」
這些外地哲學討論議程,與香港頗不一樣───香港論者往往論斷前,少有以此較全面的視野看待「本土身份認同」。
要妥善回應香港如今的本土意識崛起、處理「本土身份認同」的存在意義,以及其衍生的道德與政策議題,首先要理解的,是為何此時此刻,「本土身份認同」會成為一個政治議題。關於這點,學者沈旭暉最近在文章〈香港人進聯合國工作的夢〉提了一個很引人思考的問題:「香港人本來就是最適合在國際社會生存的人之一,是什麼時候變得沉溺在『中國夢』與『本土夢』這兩極夢囈中不能自拔?」
一國之中的多元認同
這涉及國家如何構成、構成之間衍生何種內部矛盾的大問題。世界之中,少有國家是真正的單一民族國家,於此中央政府有兩個對策選項:或則是自上而下推行單一同化政策,繼而激起反抗、衍生在地不同族群為保護自身原有文化而有的「反抗性民族主義」(reactive nationalism),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英國的北愛爾蘭、菲律賓的莫洛等都屬可參考案例;又或者,公開承認國內不同族群的「亞國家民族主義」(sub-state nationalism),給予他們平等的地位,推動一國之中的多元認同(multiple national identities)。
政治哲學家 Will Kymlicka 關心的一大議題,就是如何合乎道德地處理一國之內這類「亞國家民族主義」。在這方面,加拿大是具代表性案例。這個國家由幾大族群組成,法語地帶魁北克曾兩次進行獨立公投,但加拿大亦曾通過一個動議,指「Québécois form a nation within a united Canada」。兩位研究如何在加拿大保存魁北克獨特性的學者Alain-G Gagnon與Raffaele Iacovino,他們在著作 Federalism, Citizenship and Quebec: Debating Multinationalism 主張,英裔主導的聯邦政府,必須承認魁北克人是擁有主權與自決能力的族群(sovereign people)、而非單純的少數族群(ethnic minority)與利益團體。
有兩點可以見到,中國並非孤例:其一,中國亦非單一民族國家。官方說法,是中國屬「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國內有 56 個「民族」。回望歷史,中國亦曾有過很具聯邦制味道的「聯省自治」主張,甚至有過比現今香港更鮮明的地方意識;美國學者 Stephen R. Platt 所著的《湖南人與現代中國》是這方面很好的參考讀物。當中提到,20世紀初護國大將軍蔡鍔,曾認為湖南並非中國,因為「中國」的邊界與人口皆可變,而湖南只是純粹的內陸文化圈。後來的毛澤東,用今天的話語說,也曾是「本土派」,甚至寫過:「湖南人沒有把湖南自建為國的決心和勇氣,湖南終究是沒辦法」。
中國第二個可與世界案例可比擬的地方,是她處理國內「亞國家民族主義」的手法。中國所選的方式,是以中央政府強勢與自上而下的「大一統」方式,同化全國各地、不如加拿大般包容多元身份。著有 China’s Forgotten People: Xinjiang, Terror and the Chinese State、研究新疆恐襲的 Nick Holdstock,今年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這樣講述中國政府如何進一步「政治化」新疆人身份:「我在想,是否存在針對新疆的 20 年或 30 年戰略。官方可能希望,如果繼續讓漢人在新疆定居,同時邊緣化維吾爾人身份,那麼異議就會消失……我不確定他們是否有意和心懷不滿的維吾爾群體展開對話。」
九七前後香港的一大變化,是由海洋國家宗主國,過渡到這類大陸國家;後者遠比前者熱衷高舉權力、支配地方,是以在十九世紀英治時期,不論星港都能有政治空間包容如何啟與林文慶這類華人精英的「三重效忠」,即同時保留與英帝國、本土以及中國的情感連繫,現今在香港這卻難以想像。毛主席說,「哪裏有壓迫 哪裏就有反抗」,這正是香港本土意識興起不能迴避的一個政治背景。
「本土身份」可成道德載體
愛談道德的論者,不但不緊扣這類背景作討論,且也多少傾向視「本土身份」為「原罪」,而少有留意到,這身份除可作分配權力與資源的前提外,還可成為道德載體、防止民間禮樂崩壞。哲學家 Charles Taylor 在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Modern Identity 中指「認同……提供給人們一個組織框架,使人們能夠在這個框架中決定,應當在什麼是善的、有價值的或值得稱讚的等問題上持何種主張……如果他們失去了這種承諾或認同,他們就會很迷茫;他們在許多重要的問題上也不再能理解事物對他們的意義了。」
身份凝聚的關鍵,在於社會有足夠的社會資本、存有信任,令社群成員願意合作互助、表現道德關愛;但在現今港人難以影響關乎新成員各種細節的人口政策的脈絡之下,這種珍貴的社會資本、道德載體就不免會受影響。
「法西斯」一詞,在香港語境中多用於批評本土身份之存在;但1939年面世、其時英國首相丘吉爾推薦、分析法西斯興起的 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卻帶給我們另類啟示:法西斯這集體主義所以興起,源於共產與資本主義所承諾的理想世界無法實現、其「有 A 才有 B」線性機械的「理性」無法回應大眾思緒,令民眾心生虛無感與怠倦,這為法西斯興起、坐大國家權力消滅個人自由提供了機會。
這對香港有兩點啟示:其一,不扣連公眾思緒的「理想」,只會令社會更走極端;其二,既然「本土身份」並非原罪、可成道德載體,那麼在香港較可為的保存真我的理想實踐,便是減少依賴政府的「民間自治」,以及勿忘「世界香港」、不以種族膚色但以價值觀定義「香港人」。
最後以《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書介作結、作為身處亂世的提醒:「道德凝聚人心,卻也令人目盲得看不見事實。」
原文刊於《端傳媒》與香港革新論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