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妓與文士
士人與妓女的交往,至少在唐宋時期就已經存在風氣,明朝開國時也沒有忌諱。《國朝典故》提到明初不禁官妓,每日退朝後,官僚們便去妓樓聚會,日益浸淫放恣,以致荒廢公務。宣德初期,有明朝包青天之稱的都御史顧佐(?-1446)倡議禁妓,起初有了顯著的效果,《萬曆野獲編》稱京師(北京)縉紳自此沒有娛樂,竟然流行起男色。
在南方地區,太祖朱元璋(1328-1398)曾經在金陵(南京)設立十六座樓,安置官妓,接待四方賓旅,原本一片昇平歡樂之象也受殃及,謝肇淛形容道:「現在的法律愈來愈嚴厲了,妓女們幾乎沒辦法生存,已經看不到全盛時期那樣的榮景了。」
表面上看起來似乎禁絕有成,盛況不再,但在謝肇淛所處的明代中期,其實禁令早已廢弛,他說:「現在娼妓布滿天下,在大城市裡面有數以千計,就連小鄉鎮裡面也是有的。」對於顧佐禁妓的影響,他又補充道:「雖然公開的場合已經沒有了,可是在隱密的地方仍常常看到。」可見狎妓之風已轉趨私人化、地下化。
江南畢竟遠離京師,又是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地區,成為較早突破禁令的地方,娼妓業在嘉靖時期又重新興盛了起來。明代中期,社會風氣尚俠,並為「俠」賦予更廣泛的含意,「俠游」是一種不將科舉考試視為人生目標,或不被家業局限,轉而追求藝文成就,縱情於游樂、詩酒等活動,表現逸脫的生活觀。
而在城市中的交遊,勢必要雄厚的財力,於是輕財結客,視金錢為糞土,盡情揮霍的價值觀也成為俠的內涵之一,能夠具體展現豪俠之氣的地方便是妓院這類的聲色場所,因為該處提供一個逃避的空間,讓人暫時忘卻現實的困頓,寄身其間的文人也可藉由展現文藝才華,顯現個人的存在感。《板橋雜記》記載佚事的下卷便提到幾位豪俠之士,例如蕭伯梁喜歡在妓院揮灑金錢,身旁總有好多名姬作陪。又如張維有才華,不計較金錢,喜歡交朋友。與他們相伴的名妓,也不免沾染了幾分俠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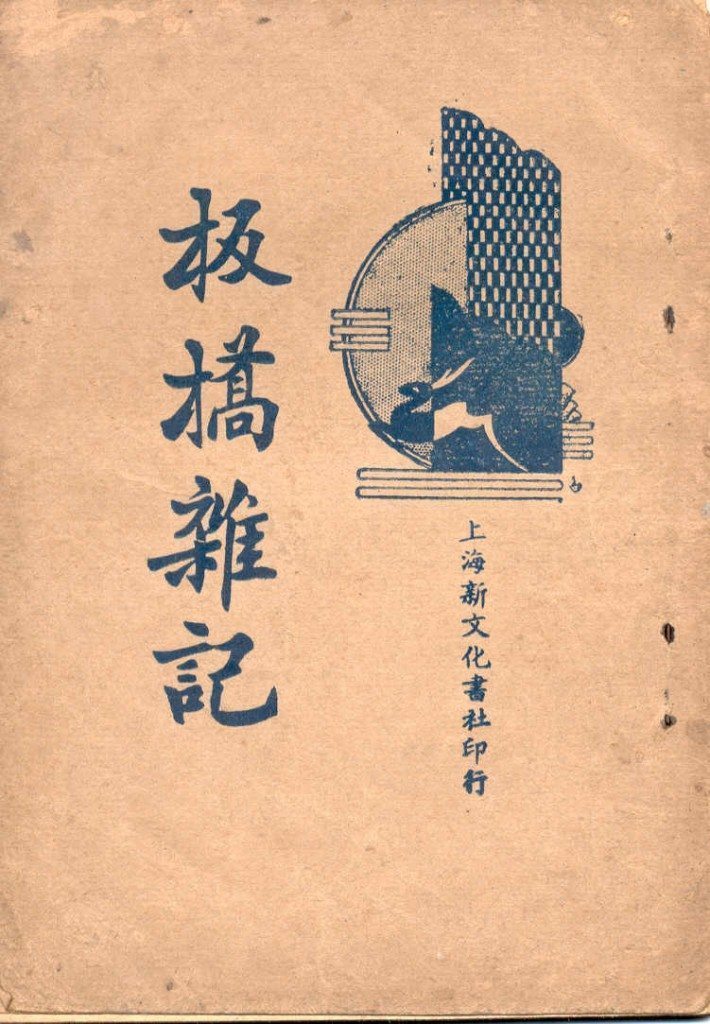
當時的選美比賽稱為「花案」,場面極為盛大,這可不是輕率的品頭論足,而是由幾位知名的文士擔任裁判對妓女進行品賞、排列名次,像是科舉一樣,擬作狀元、榜眼、探花,並配上相應的花卉,如曹大章等名士組成「鷲峰詩社」,是目前已知最早舉辦花案品評者,《蓮臺仙會品》記載其排選結果為:「女學士,王賽玉,小字儒卿,名玉兒,行六,花當紫微。……女狀元,蔣蘭玉,小字雙雙,名淑芳,行四,當杏花。」
至於品選的基準,《金陵妓品》透露道:「第一要看他們的氣質;第二要看他們的儀態;第三要看他們的才華;第四要看他們的容貌。」也有文人會將名妓湊數冠名,諸如「秦淮八艷」、「金陵十二釵」等,後來更依此出版了《金陵百媚》、《吳姬百媚》、《秦淮詩鈔》等歌詠妓女的詩文集,亦有人撰寫《嫖賭機關》、《嫖經》等風月指南,提供比較庸俗的內容給民眾作為尋芳的參考。
崇禎十二年(1639)的七夕,在方以智(字密之,1611-1671)僑居的居水閣聚集了許多妓女,各路的名士豪傑也都來了,車馬、舟船將周圍的街巷與水道擠得水洩不通,三班戲團同時在臺上競演。
原來閣內正在品選花案,共選出二十位,其中王月(字微波)被品為第一名,要登上特製的狀元階臺上,當他一上臺,樂班就開始奏樂,並進酒祝賀,宴會一直持續到天亮才結束,其他沒選上的妓女,只能落寞的離開。隔天,與會的來賓各賦詩記錄過程,余懷寫道:「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姮娥第一香。」王月將這兩句詩繡在手巾上,隨時攜帶在身邊。
《藝苑卮言》載述正德年間的文人們玩一個拋擲骰子的遊戲,一位不知名的妓女,拿到骰子後便以此為題,應答:「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染,拋擲到如今。」小妓有如此文采,實屬難得,因此特別被記錄下來。
而部分名妓的文學造詣比起文士也毫不遜色,《列朝詩集》小傳中多有記載,如揚州名妓王微(號草衣道人,1600-1647)往來在蘇州,與他一起的都是名士。名妓參與文人藝文活動也成為一時風氣,甚至成為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嘉興有名妓周文(字綺生),其舉止言論皆儼然如文士,當地縉紳好文墨者,每次聚會必定邀周文出席共襄盛舉。更誇張者如精通文史、擅長寫詩的朱無暇(字泰玉),有一次在秦淮有一場集結天下名士的聚會,當他的詩一寫成,其他人都自嘆不如了。
然而無論是花案,或是各式文藝社團,當名妓置身其中,與文士交往唱和,其產生的作品往往會以文字的方式傳揚,無形中也有助妓女的聲名,亦是妓女成為名妓的途徑。
從青樓到蘭閨
美人遲暮,千古一轍,名妓的職業生涯是絢爛而短暫的,他們的後半生又要怎麼度過呢?妓女平時供養「白眉神」,也多信佛教,常到佛寺參拜許願,落籍從良後削髮為尼,或成為道姑是一種選擇。轉換身分的另一種途徑是為人妻妾,就男性而言,妻的責任是持家、生育,屬於家內的;名妓則能豐富感官,具有社交性質,因此兩者的角色具有互補性,恰能調劑男性在不同方面的需求。
美國性別史學者高彥頤(Dorothy Ko)曾經分析名妓流動至家庭面臨的衝擊,儘管妓女成為妾後,可能會受到妻的敵視,但兩者有著共同的目的,即服務丈夫,在「從」的倫理標準下,對男性保持忠誠,因此妻對於這位本不屬於家庭的妾也只能選擇接受。冒襄娶董白為妾時,便感謝元配有相成相許的雅量,且與之相處有如水乳般融洽。在明代中後期,當婦女以撒扇、時世妝為風尚時,妻子與藝人的界限也不再分明。
要落籍從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影梅庵憶語》提到冒襄為了替董白贖身,費了一番功夫。事後接到錢謙益的來信,才知道動員了許多人士幫忙,錢謙益請其門生辦理落籍事宜,蘇州有些瑣碎的糾紛則由周鑣(周儀部)打理,曾任禮部官員的李宗憲也從中協助,前後費時十個月才完成。其金錢花費更是驚人,光是處理上至官吏,下及市井的各式借債就花了三天,將借據疊起來竟厚達一尺,還有聲稱是董白生父的人登門要錢。
小說家馮夢龍(1574-1646)在《醒世恆言》中有一則故事提到從良有「真從良」、「假從良」、「苦從良」、「樂從良」等等狀況,像冒襄與董白這樣相愛的便是樂從良,有的時候男有情女無意,勉強娶進門,便是假從良。若嫁入侯門,抬不起頭,變成半妾半婢,那便是苦從良。列舉這麼多情境,卻沒提到一種最淒慘的,沈德符曾有段親身見聞,他認識一個擁有田園、宅第的妓女劉二,卻被一個浙江人范仲子以甜言蜜語誘惑,兩人結婚後,因范仲子喜好賭博,以致劉二的簪珥、姬侍、田產都被變賣,最後投繯自盡。沈德符又聽人說:「這個人習慣誘騙妓女,這種技倆也不是第一次了。」
從良後的妓女有的還會在公眾場合與文人交往,甚至重操舊業,有的則是洗心自新,成化年間的金陵名妓林奴兒,風流姿色,冠於一時。從良後,有舊知欲求一見,林奴兒便以扇畫柳題詩拒之,詩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舊枝條。如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
天地正義見於婦女
唐人杜牧(803-852)有詩〈泊秦淮〉:「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指賣唱的歌妓不能體會王朝滅亡的痛苦,仍然逕自的唱著歌曲。此詩實為借商女諷刺主事者不以國事為念,沉浸於靡靡之音。
但是妓女真的是不關心天下興亡的嗎?與此相反,晚明的名妓不乏以抗節明志者。《板橋雜記》提到張獻忠(1606-1647)搜得名妓王月,留於營中押寨,王月卻忤逆不從,最後被張獻忠煮來以享群賊。鳳陽督師馬士英麾下士兵擄掠淮安,妓女悉被擒,唯獨燕順堅執不從,被士兵所殺。
這些名妓的抵抗可能僅是出於身體上受到侵害,表現出貞節的行為,然而有些名妓更體現出對王朝的責任感,有主動的抗拒行為。例如李香君勸侯方域不要接受南明奸臣阮大鋮的資助,後來南明淮陽巡撫田仰以三百金邀李香君一見,也被斷然拒絕,《桃花扇》便以此為創作原點,說李香君因此自盡未遂,血濺詩扇,被盟友楊龍友繪為桃花,桃花扇即成為李香君與侯方域的訂盟之物。
著名的歷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9)晚年作《柳如是別傳》,雖然自稱「著書唯剩頌紅妝」,但他關注的面向不在男女情愛,而是借此表彰柳如是獨立的精神。陳寅恪說柳如是為曠代難逢之奇女子,並用了很多的史料說明錢謙益在柳如是的鼓勵下,參與了一系列反清復明的運動,相較之下,其氣節更甚錢謙益。
1645 年,南京傾覆,柳如是勸錢謙益應該要有氣節,才不會辜負你的名聲。錢謙益面有難色,柳如是於是奮身跳入湖中,還是被人拉住才沒跳成。有人為這個故事杜撰了嘲諷的內容,說錢謙益原先答應殉國,後來探了湖水,說:「湖水怎麼這麼冰冷啊!」由於水太冷而改變殉國的心意。與錢謙益相反,出仕三朝的龔鼎孳(1615-1673)娶顧媚為妾,也曾投井自殺,但被人救起,遇到人問起,他總說:「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這也使得清人陸以湉(1801-1865)比較顧媚與柳如是時,認為顧不如柳。
清代初期,遺民將精神寄託在江南地區大量婦女殉節的記述,其具體的行為是透過修纂《明史‧列女傳》,將民族觀滲透到文字內,遂有「天地正義僅見於婦女」的論調。學者鄭培凱也注意到這樣的現象,認為婦女能在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乃是因為事蹟符合統治階級主導的道德意識。也因如此,從節烈事蹟中看到的現象,往往只是道德家所想追尋的,並不能真實反映人們的主體生活意識。
高彥頤則有另一種見解,認為對女性貞節要求日益嚴苛,產生了另一種作用是使他們進而忠君愛國,故在鼎革時期成為反清忠明的積極參與者,浙江才女王端淑(1621-1706)詩文中流露對南明小朝廷的同情便可作為證明,部分名妓的殉國行為可能也是如此吧!
結語
有人問余懷,朝代的興衰,可歌可錄的事情那麼多,為什麼偏偏只記狭邪豔治之事?余懷則從初期的十六樓,至晚期的南市、珠市及舊院,細數妓院的變革。也許對明代晚期江南的騷人墨客來說,秦淮的盛衰就是王朝的象徵,多少風流韻事,男歡女愛都在此發生。怎料王朝崩解,繁華轉眼成空,一片歡場,如今只剩遍地野草,秦淮承載著無數士人的記憶,成了抒發懷古幽思的對象。
晚明名妓文化之盛,得利於許多因素,社會風氣的轉變,帶動情欲的解放,而俠游與城市文化結合,更讓妓院成為排解人生挫折、展現文學才華的場所。另一方面,妓女也學習詩文才藝,成為儼如文士的名妓,使文人與妓女的交往,超越了金錢與肉體的層次,而富有情感與內涵。晚明文人忘情追求聲色,恣情縱欲地享受生活,妓女則成為文人在禮教之外,情欲的歸依。
主要徵引書目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明]周暉,《金陵瑣事》,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16編,第3冊(臺北:新興書局,1977)。
- [明]姚旅,《露書》,天啟刻本。
- [明]范濂,《雲間據目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22編,第5冊(臺北:新興書局,1978)。
- [明]張岱著;馬興榮點校,《陶庵夢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明]謝肇淛,《五雜俎》,萬曆四十四年潘膺祉如韋館刻本。
- [明]張應俞著,孟昭連整理;魯德才審訂,《江湖奇聞杜騙新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
- [明]陸容,《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明]馮夢龍;廖吉郎校訂;繆天華校閱,《醒世恆言》,臺北:三民書局,1988。
- [明]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 [明]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順治九年毛氏汲古閣刻本。
- [清]冒襄,《影梅庵憶語》,清昭代叢書本。
- 王鴻泰,〈明清文人的女色品賞與美人意象的塑造〉,收入王璦玲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情、理、欲──文學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頁189-226。
- 王鴻泰,〈青樓:中國文化的後花園〉,《當代》,137 (臺北,1999),頁16-29。
- 王鴻泰,〈青樓名妓與情藝生活──明清間的妓女與文人〉,收入熊秉真、呂妙芬主編,《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頁73-123。
- 王鴻泰,〈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與尚俠風氣〉,收入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頁101-147。
- 王鴻泰,〈美人相伴──明清文人的美色品賞與情藝生活的經營〉,《新史學》,24:2(臺北,2013),頁71-130。
- 汪榮祖,〈文筆與史筆──論秦准風月與南明興亡的書寫與記憶〉,《漢學研究》,29:1(臺北,2011),頁189-224。
- 林麗月,〈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論〉,《新史學》,10:3(臺北,1999),頁111-157。
- 邱仲麟,〈姚旅《露書》中的明代社會經濟史料〉,《明代研究通訊》,4(臺北,2001),頁21-46。
- 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9),頁137-159。
- 游惠遠,〈明代的妓院教育與藝術成就〉,收入勤益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編,《跨領域人文與科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全華圖書,2008),頁210-222。
- 潘敏德點校,〈《嫖經》點校并序〉,《明代研究》,21(臺北,2013),頁99-143。
- 鄭培凱,〈天地正義僅見於婦女──明清的情色意識與貞淫問題〉(下),《當代》,17(臺北,1987)頁58-64。
-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方駿、王秀麗、羅天佑合譯,《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
- 大木康,《冒襄和影梅庵憶語》,臺北:里仁書局,2013。
- 大木康著;辛如意譯,《風月秦淮──中國遊里空間》,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 王書奴,《中國娼妓史》,北京:團結書版社,2004。
- 衣若蘭,《史學與性别:《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
- 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05。
- 李孝悌,《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高彥頤(Dorothy Ko)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 商傳,《走進晚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三聯書店,2009。
- 蔡石山,《明代的女人》,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