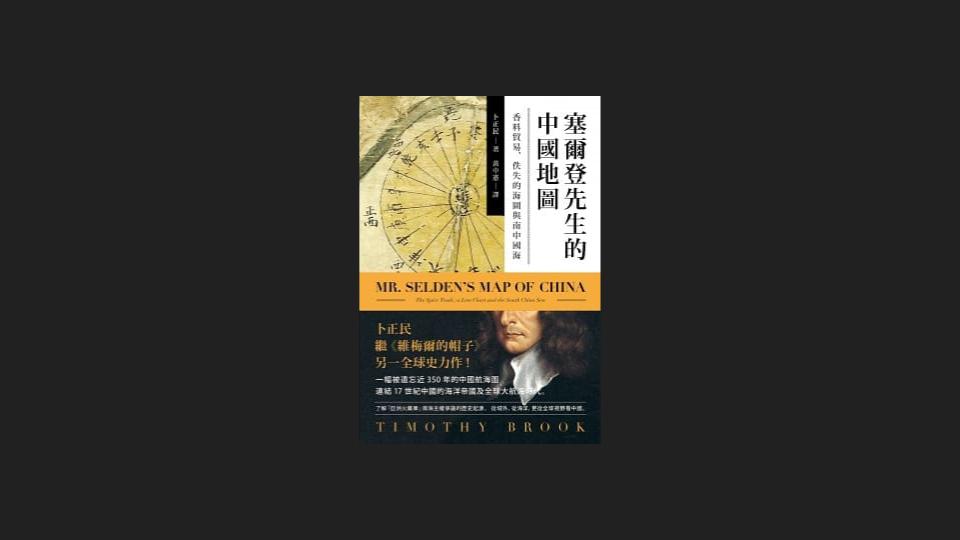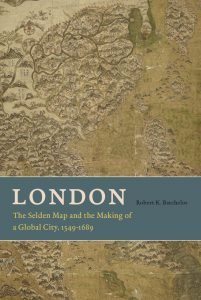地圖秘碼的破解
卜正民繞了前述這麼大的圈子才來到地圖本身的內容,直到第八章「塞爾登地圖的秘密」才開始明確破解這張地圖的密碼,提出以下秘密。
第一是中國。卜正民從明朝余象斗編的類書《萬用正宗》找到塞爾登地圖繪製中國內部時的類似畫法,那是一張呈現二十八星宿相對應之地區的中國地圖《二十八宿分野皇明各省地輿全圖》在這張地圖上,中國並非主軸,地圖繪製者可能拿抄寫自別處的地圖填補中國所在的空間。因此,這張圖的重點是在沿海,而不是內陸。
第二是它非常精確。這張地圖的的比例尺繪圖水平,和當時歐洲最出色的作品如英國地圖繪製家史畢德(John Speed)的《亞洲及其周邊島嶼》相較,兩者不相上下。卜正民推測,塞爾登地圖的繪製者看過歐洲人所畫的地圖,並且抄襲某張歐洲人的地圖,才得以解決繪製中國周邊海域的難題。但不同的是,歐洲地圖對運用經緯度賦予地圖始終一致的比例,在塞爾登地圖上卻看不到。拿塞爾登地圖和近代圓錐投影圖相較,可看出有的地方太大,有些則太小。
卜正民提到,2011 年修復前,這張地圖情況很遭,修復小組將原先的襯底的紙張移除後,背面有一連串用直尺畫出彼此相連的線,與正面的線條相吻合。這說明繪製者根據手邊航路指南的航路資料先畫航線,再填上周邊的海岸,路塊大概是後來才加上的。嚴格來說,這張不是地圖,而是航路圖。另外,卜正民根據圖上比例尺與距離及航速的關係,推測出這地圖與《順風相送》所使用的都是相同的導航資料。
第三是磁場特徵。這位地圖繪製者不僅標出航路的方位,還按照航路的真正走向,將航線如實畫在地圖上。走向依據的是羅針圖,這種羅盤入圖的畫法是中國的首例,直到二十世紀,附上羅針圖才成為中國地圖繪製界的標準作法。卜正民認為這表示塞爾登地圖的繪製者見過歐洲人所畫的地圖。此外,他推斷塞爾登地圖上的航路資訊經過磁性編碼。雖然有些航路有偏離的誤差,但有幾條相當精確的路線,像是連結月港與馬尼拉,澳門與馬尼拉,越南東京灣與爪哇等。這表明它們是中國船隻在南海網絡裡的主要路線。
第四是這是一張商業性的航海圖,裡面沒有帝國的企圖或主張。塞爾登地圖的焦點雖然是在海上,卻不是說明該片海域島礁的主權歸屬,它純粹是張為商人指點航向的海圖。卜正民還特別強調,看待這張地圖或不能用狂熱的民族主義者的角度,主張塞爾登地圖為自己對海域某個岩礁的主權聲明提供了明證。
在這章的結尾,卜正民還是替地圖的身份提供了看法。究竟這幅地圖的作者是誰?在哪裡繪製?繪製的時間是何時?就作者看來,在這張地圖上,繪製者對圖中最了解的地方是在南半部。相較於明朝地圖把東南亞畫得相當精簡,有時甚至完全刪去。塞爾登地圖不同於之前、也不同之後兩百年的中國人所繪製地圖。卜正民推論地圖繪製者的所在地不是在印尼爪哇的萬丹,就是在巴達維亞(雅加達)。
卜正民還透過塞爾登遺囑中的線索:「這張地圖來自一名英格蘭指揮官」(頁 238),進而推敲出這人可能是前文提到的薩里斯。塞爾登大概經由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地圖繪製顧問哈克呂特(Richard Hakluyt)從英格蘭出版商珀柯斯(Samuel Purchas)那裏取得地圖。作者深信,透過同一批收藏者,這張地圖從薩里斯流通到塞爾登手中。他更進一步推論薩里斯極有可能是從一位萬丹的華商處取得地圖,而這位華商以萬丹港為基地進行貿易,想看到自己的貿易版圖呈現在家中的牆壁上,於是出價請人繪製地圖。
卜正民繼續探索薩里斯可能取得這張地圖的時間。他提出了三個說法,並認為其中最有可能的是薩里斯待在萬丹的時候。1604 年他被派到萬丹,1608 年擔任該地商館館長,1609 年返回英國。因此,待在萬丹前後五年間是最有可能的時間。此外,就是透過地圖上非常精確的時間標記——令海德大感興趣的「紅毛住」三個字。這字眼指的是 1607 年荷蘭人在爪哇島插足瓜分建立第一座堡壘一事,因此這標記問世的最早年代是 1607 紅年,最遲不會晚於 1609 年。卜正民取了折衷值,那就是 1608 年。
推論至此,卜正民大致講完塞爾登地圖的身世之旅。在本書結論裡,卜正民相當感慨地說,這張地圖輾轉流傳到歐洲一事,本來很有可能改變這個故事的發展。當年若是有人將這張地圖拿給對的人看,說不定會影響歐洲的地圖繪製者,但卻沒能發生。等到這張地圖到達牛津時,它已經沒有機會引領風騷了,此時地圖界的發展已經大有進展。卜正民把這張地圖失去價值的年代定在 1640 年。那一年荷蘭的地圖繪製家布勞(Joan Blaeu)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繪製出一幅中國海域圖。這代表了歐洲人能依賴自己製作的中國海圖,不需要再回頭拿塞爾登地圖作為地圖繪製依據。等到塞爾登地圖被送到博德利圖書館時,它在技法上已經沒有特別優越之處,它的精確性此時只剩下歷史價值,只是一個外國珍玩而已。
問題討論
塞爾登地圖自2008年被發現以來,受到各地歷史學者、地圖研究者的重視,除了前言提到的兩本書外,至今已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面世,尤其是中國及香港學者最為積極,[1]以下則針對這些作品一併進行討論。
有限資料外的無限推論
《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是筆者近來所讀過的歷史著作中,使用「可能會」、「可能是」或者是各種不確定字眼最多的一本書。其中有些是有了答案而在行文上做句型的修飾,有些則是完全沒有答案,以可能會是怎樣來進行各種推論。卜正民這種不就事物本身去寫,而是繞了一大圈在周圍故事的寫作策略,關鍵還是在於他自己所說的「我們的疑問無法從這件東西本身輕鬆找到解答。」(頁 51)更明白地說,就是有關塞爾登地圖的佐證史料實在是太少了,作者只能憑藉非常有限的資料來寫出一本書,的確需花費一番功夫。
然而,太多的歷史想像與推論會大大降低本書的可信度,像是「我傾向認為地圖上那截尺和那個羅盤表明塞爾登地圖的繪製者看過歐洲人繪製的地圖,知道可拿來好好借鑒」(頁160);「《續珀柯斯的遠行》第三卷含有許多大概會讓塞爾登感興趣的東西」(頁189);「王爾德若看過這張地圖,大概會予以肯定,我們應該也會」(頁 210);「塞爾登大概經由理察‧哈克呂特從撒繆爾‧珀柯斯那兒取得這張地圖」(頁 239);「這張地圖輾轉流落歐洲一事,本有可能改變這個故事的發展」(頁 244)。此外,有些語氣看似很堅定的評論,卻不大具有史料根據,像是「我深信,經由同一批收藏者,這張地圖從薩里斯輾轉流入塞爾登手中」(頁 239-40);或頁 241所說:「如果塞爾登所述沒錯,薩里斯取得這張地圖後,原持有該圖的商人向他『出很高的價錢極力要將它贖回』」,以及頁 242「我們由此可以得出可能的區間,最晚不會晚於 1609 年,最早不會早於 1607 年。我建議折中取值,也就是約 1608 年。」。
此外,書中的很多敘述純粹是作者的想像,以疑問句的方式來表達,像是「那些航路已幾乎磨損見底露出紙質。這一損傷單純是無意間的磨損?還是個足以透露內情的痕跡,表明這是此地圖主人最感興趣的地方,其主人喜歡向友人指出此處?這是塞爾登──例如無意間用他的眼鏡──在其地圖上擺上的記號?」(頁78)上述這些僅靠推論或歷史想像的例子僅是書中的一小部份。
關於地圖的種種爭議
和卜正民的上一本暢銷書《維梅爾的帽子》不同,《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並沒有清楚說明是針對一般大眾而寫,無論從內容、敘事手法、架構還是註腳,都看不出是針對一般讀者。反而我們透過書末的書目出處來源,可以看出他所用的史料大多是當代西方研究,並未引用這地圖公開後針對此地圖所做的中文研究成果。事實上,中文學界雖然晚於英美學界接觸到此地圖,但還是透過各種方式取得此地圖的電子檔,並提出對繪製者身份、繪製時間及內容的見解。
目前所見,香港大學教授錢江 2011 年發表於《海交史研究》第一期的〈一幅新近發現的明朝中葉彩繪航海圖〉一文,應為中文學界最早的成果。錢江發表這篇文章時,並未應用後來學者為這幅地圖的取名,僅描述說是繪製於明朝中葉的彩色航海圖。他在文中大膽推測,繪製海圖的作者或許就是一位常年附隨船舶在海外各貿易港口經商的鄉間秀才,也可能是一位民間畫工,或者是一位轉而經商的早年落第舉子。此外,他還提到英國牛津大學的學者認為,這幅航海圖應該是在福建泉州創作的。由於畫法與中東阿拉伯的地圖繪製法相似,英國學者進而推斷繪圖者可能是一位定居在泉州早已漢化的阿拉伯人。錢江認同這一觀點,但在文中卻沒有說明這位牛津大學學者是誰 [2]。
此外,錢江還提到 2011 年的一次於新加坡舉辦的亞洲歷史會議上,卜正民和他交換意見時,表示不同意他認為此圖創作於泉漳地區的看法,並認為作者一定是居住於印尼巴達維亞的福建商人。關於卜正民這樣明確的見解,反而未見於《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至於創作年代,錢江根據地圖的歷史背景與所繪製的東西洋航路來看,推斷時間應當是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因為當時是海外貿易最為興盛的時期 [3]。
在錢江之後,香港中華萬年網編輯陳佳榮在同年的《海交史研究》第二期也發表了一篇研究文章,正式將這幅地圖取名為《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圖》。文中進行幾項史實的分析:(1)地圖採用了 1602 年後刊布的西式繪圖成就; (2)地圖所載的台灣地名應該在1603年陳第東遊後; (3)地圖所載東北地名應在後金建立後; (4)地圖提到的「紅毛住」等註文,應在 1621 年荷蘭人佔領摩路加群島後;(5)地圖未反映 1624 年荷蘭人佔領台南的情況。綜合這五點推論,他主張地圖繪製的時間大致在 1624 年左右[4]。
關於繪製年代的問題,陳佳榮在 2013 年的《海交史研究》上撰文,又重新做了修正。在這篇文章中,他將這張地圖改稱為《東西洋航海圖》。他根據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的一幅《二十八宿分野皇明各省地輿全圖》,提出地圖繪製時間的上限可推至 1607 年。此外,他在文章提到曾參考貝秋勒在 2013 年發表的文章,很明顯,陳佳榮這看法似乎就是受了他的影響。[5]
有關塞爾登地圖受《二十八宿分野皇明各省地輿全圖》繪圖方式的影響,卜正民在書中也有討論,錢江與陳佳榮所說的繪製時間明顯地和卜正民所提出的 1608 年有所出入。至於貝秋勒的看法則是,他並不同意卜正民的論點,認為地圖可能是在馬尼拉繪製,繪製時間大約在 1610 年代後期,大約是在 1619 年左右[6]。儘管上述關注地圖細節的學者大多是基於考證並加以推論,但卜正民得出繪製時間是 1608 年的理由也沒有比他們高明多少。他在書中一直強調:他關注的是人物,而不是地圖本身,但到了結論部分他還是免不了要用排除法,猜看這張地圖究竟是何時的作品。
2013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林梅村則針對上述文章,做了更進一步的研究,他的結論有四點:(1)這張地圖大約繪製於崇禎六年至十七年(1633 至 1644 年);(2)塞爾登地圖其實就是《鄭芝龍航海圖》;(3)1633年,金門料羅灣大捷,鄭芝龍艦隊從荷蘭人手中收繳了一些海圖。鄭芝龍不僅通曉多國語言,其部下還有許多戰俘及外國傭兵,因此塞爾登地圖顯然借用鄭所獲得的西方海圖的技法;(4)現存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東洋南洋海道圖》,繪者是施琅之子施世骠,時間約在 1712 至 1721 年間。該圖看似源於《鄭芝龍航海圖》,如果屬實,那麼塞爾登地圖原名可能是《大明東洋西洋海道圖》[7]。
透過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看出學界對於這張地圖的繪製時間、繪製者及繪製地點說法不一,由於佐證資料有限,許多觀點都是推測之詞,因此都僅能存疑。儘管這些論著的推論有待商榷,但對於比較晚出版的《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仍應當在文中或註腳中對這些說法有所回應。
說法不一
文中有幾處小錯誤,像是作者在序中提到:「這是幅大地圖,長 160 公分,寬 96.5 公分,大小雖只有瓦爾德澤米勒地圖的一半,但肯定仍稱得上是當時當地最大的壁掛圖。」(頁19)但在第一章卻又有不同說法:「七年後,我在新博德利圖書館地下室仔細研究一樣我怎麼也料想不到其存在的東西。……它尺幅甚大,寬超過1公尺,長將近2公尺。」(頁 35)這兩種說法明顯有出入。在第八章中,作者提到:「其中只有某些秘密會被我們解開。我算過,僅僅六個」(頁 219)。但下文有標示「第幾個」的地方只有四處(頁 219-36),另外兩個並未有數字的標示。這是刻意不說,要讀者自行在下文找答案,還是文字上的疏忽?
此外,有的地方是前後說法不一致。卜正民提到:「當年若有人將它拿給對的人看,說不定會影響歐洲的地圖繪製者,但這事沒發生。」(頁 244)。但這之前卻說:「塞爾登地圖的繪製者能製出如此脈絡一致且精確的地圖,靠的是抄襲某張歐洲人所繪地圖。」(頁225)。既然歐洲都已經有此技術,塞爾登地圖若早一些被發現,究竟能有多大影響?這裡的看法似乎不太一致。
從塞爾登地圖看倫敦
相較於卜正民旨在破解《塞爾登中國地圖》的秘密,同樣研究這幅地圖且是最早的發現者,貝秋勒的研究方法就截然不同,他的專著《倫敦》則是透過這張地圖探討英國如何經由英國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聯繫所帶回來的各種資源,將倫敦打造成一座全球性的現代都市。兩者相比,筆者更喜歡這種較為非推理式的寫作風格。貝秋勒認為亞洲的貿易體系對於倫敦的文化、知識與政治形塑扮演了基礎性的角色。透過在南中國海、印度洋與東亞海域的相遇,英國商人不僅發現新的財富來源,而且還有新的王權模式與主體性。舉凡這些現代性的象徵,像是合股公司、民族、法規、國家、政治革命,都被視為與亞洲的轉變有關。
貝秋勒不像卜正民一樣逐一去破解地圖裡的密碼,反而是更廣泛地去看來自亞洲的這些地圖、知識或觀念與倫敦的關係。書中提到塞爾登收藏來自世界各地的書與手稿,還有中國航海地圖與測繪羅盤。在這個時期,塞爾登常提議如何廣泛地調查及翻譯語言、法律、歷史與科技;而所謂的「翻譯」是多面向的、去中心的,有時是跨歷史的脈絡。從這方面來看,翻譯為啟蒙、政治、經濟與科學革命的過程,提供了充分養分。《倫敦》一書讓我們見到和卜正民完全不同風格的書寫,看似在寫塞爾登中國地圖,但重點不是在這張地圖上,而是延伸出許多課題,所強調的是十七世紀的倫敦[8]。
結語
同一張地圖竟可以讓學者寫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著述,正透露出這張隱藏了數百年的地圖的魅力。不同研究背景的學者無論在有關地圖的內容、繪圖者、流通過程、收藏家、時代特色、貿易、全球都市等方面,都有相當不錯的研究成果。這不僅要感謝卜正民以抽絲剝繭的方式帶領我們認識塞爾登地圖的生命史,更要對地圖的發現者貝秋勒以全球史的視角探討倫敦都市的近世發展表示敬意。
如同卜正民在書末所說的:
儘管目前仍有許多疑問未能有滿意的答案,但有關這張地圖的解密工作不會到此告一段落,在卜正民及貝秋勒的努力下,我們看到了許多研究成果,日後勢必會吸引更多學者加入討論。
[1] 參見錢江:〈一幅新近發現的明朝中葉彩繪航海圖〉,《海交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頁 1-7;陳佳榮:〈《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圖》繪編時間、特色及海外交通地名略析〉,《海交史研究》,2011 年第 2 期,頁 52-66;陳佳榮:〈《東西洋航海圖》繪畫年代上限新證──《二十八宿分野皇明各省地輿全圖》可定 “The Selden Map of China” (《東西洋航海圖》)繪畫年代的上限〉,《海交史研究》,2013 年第 2 期,頁 102-109;林梅村:〈《鄭芝龍航海圖》考──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藏《雪爾登中國地圖》名實辯〉,《文物》,2013 年第 9 期,頁 64-82。西方學者則有Robert Batchelor,“The Selden Map Rediscovered: A Chinese Map of East Asian Shipping Routes, c.1619”, Imago Mundi 65, no. 1(2013):37-63; Stephen Davi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den Map: Some Conjectures”, Imago Mundi 65, no.1 (2013):97-105。另有針對沈福宗與海德的信件往來進行的探討,參見William Poole, “The Letters of Shen Fuzong to Thomas Hyde,1687-88”, Electronic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article 9 (2015), http://www.bl.uk/eblj/2015articles/pdf/ebljarticle92015.pdf ,1-28. 龔纓晏、許俊琳:〈《雪爾登中國地圖》的發現與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15 年第 3 期,頁 100-105。另可參見龔纓晏:〈國外新近發現的一幅明代航海圖〉,《歷史研究》,2012 第 3 期,頁 156-60。
[2] 錢江:〈一幅新近發現的明朝中葉彩繪航海圖〉,頁5-6。
[3] 錢江:〈一幅新近發現的明朝中葉彩繪航海圖〉,頁6。
[4] 陳佳榮:〈《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圖》繪編時間、特色及海外交通地名略析〉,頁55-58。
[5] 陳佳榮:〈《東西洋航海圖》繪畫年代上限新證:《二十八宿分野皇明各省地輿全圖》可定 “The Selden Map of China”(《東西洋航海圖》)繪畫年代的上限〉,《海交史研究》,2013年第2期,頁102-109。
[6] Robert Batchelor, London: The Selden Map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City, 1549-1689, pp. Loc 2225 of 9151(Kindle)。
[7] 林海村:〈《鄭芝龍航海圖》考〉,頁79。
[8] Robert Batchelor, London: The Selden Map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City, 1549-1689。
上篇由此去:「閱讀地圖裡的全球史秘密──評卜正民《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