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年,國際足總祕書亨利.德勞內(Henri Delaunay)道出組織遭遇到的最大困境:「今日國際足球不再甘願被框限於奧運的範圍內,很多國家的職業足球已受到認可且組織成形,可參加奧運的一流選手不再能完全代表各國實力。」

1928 年阿姆斯特丹奧運證明,足球無疑是當前最受歡迎的盛事,國際足總在激勵之下付諸行動,成立第一屆世界盃籌備委員會,召開會議排解內部針對比賽基本形制吵嚷個沒完的爭執。
世界盃將對全世界開放,不只歐洲球隊可以參加。所有球員不分職業或業餘都能代表國家出賽。賽事每 4 年舉辦一次,金錢收入由國際足總與主辦國拆分。截至此時,有幾個歐洲國家對主辦賽事表露興趣,但顧慮到可行性、風險、花費,紛紛都打了退堂鼓。
機會於是留給了唯一有意掏錢的國家:烏拉圭。
烏拉圭也的確有錢。當地的羊毛、毛皮、牛肉產業 1920 年代蓬勃發展。在總統奧多涅茲治下建立起福利國家,依靠農產外銷的豐厚利潤取得充裕資金,維持社會和平,奠立了一個政治進步、高度投資教育、城市發展繁榮的年代。
烏拉圭急欲確立國家地位、打響國家名號,證明烏拉圭確確實實就是世界足球冠軍,政府於是表示願意支付來訪球隊的開銷、為世界盃興建一座全新適用的球場,並且提議賽事在 1930 年 7 月揭幕—正好是烏拉圭獨立制憲 100 週年。
1929 年,國際足總在巴塞隆納的會議上,儒勒斯.雷米(Jules Rimet)把主辦權授予烏拉圭,並委請法國雕刻家亞伯.拉夫樂(Abel Lafleur)製作一座金盃,時稱勝利女神盃,日後方改稱雷米金盃(Coupe Jules Rimet)。

不像日後世界盃對於電子媒體、現代通訊、國際觀光的建設需求龐大,烏拉圭不必顧慮這些,只須把心力集中在興建新球場。籌備委員會委請建築師胡安.斯卡索(Juan Scasso)設計,將之命名為世紀球場(Estadio Centenario),以紀念即將到來的制憲 100 週年,地點選在城市新擴建後位於中心地段的巴特列公園(Parque Batlle)。
1930 年 2 月工程動工,公園像蟻丘一樣人頭鑽動,兩家不同建設公司卯足了勁興建自己那一半球場。混凝土進口自德國,因為拉丁美洲尚無能力自行生產。實際究竟會有多少球隊到新球場參賽,在年初還是個問題,各地國家足總接二連三回絕了邀請。不來的包括不列顛四國、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德國、瑞士和中歐國家。
羅馬尼亞國王卡羅爾二世曾在 1928 年個人承諾會支持世界盃,他說到做到,協助組建羅馬尼亞代表隊,並把他們送上了特派郵輪「綠爵號」(Conte Verde)。不過,這些球員大多是受雇於普洛耶什提當地不列顛工廠的油井工人,是國王的情婦居中斡旋,雇主才答應放行。
船行到熱那亞,法國隊也上了船,他們在雷米的脅迫下答應參加,但像國內的頂尖前鋒馬努埃.亞納托(Manuel Anatol)或國家隊教練加斯東.巴洛(Gaston Barreau),雷米說服不了他們陪同前往。在國際足總的比利時副主席魯道夫.席德瑞爾(Rudolf Seedrayers)威逼之下,比利時人也一起上了船。只有南斯拉夫隊打扮得漂漂亮亮,搭著一艘叫「佛羅里達號」的遊輪出航,似乎不需要其他動力,光是想到能兩個月不用工作,還能登上拉丁美洲這片足球的新大陸去冒險,這就夠他們樂了。
這四個國家與地主國,加上另外八支美洲球隊—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墨西哥、巴拉圭、祕魯和美國,構成十三個參賽國,1930 年 7 月將集結在蒙特維多。

原定開賽之日,世紀球場尚未完工,第一屆世界盃的開幕戰因此是在國民隊主場中央公園球場(Parque Central)和佩納羅爾隊的波奇多球場(Pocitos)這兩座小小的球場舉行。
阿根廷隊演出首輪好戲,與法國的比賽由於兩隊中場表現出色而打得難分難解。阿根廷在第 80 分鐘進球打破僵局。法國隊猛烈反擊,派出馬塞.朗吉勒(Marcel Langiller),沒想到裁判竟然提前 4 分鐘吹響終場哨。
阿根廷球迷衝進場內,法國球員包圍裁判理論,騎警追著所有人跑。巴西籍裁判阿瑪迪亞.雷哥(Almedia Rego)尷尬又沒輒,只能雙手一攤承認失誤。草皮清空以後,阿根廷前鋒羅貝多.奇洛(Roberto Cherro)昏倒,重啟的比賽又草草劃下句點。
現場佔多數的烏拉圭球迷狂噓阿根廷球員,把法國球員高舉在肩膀上歡送下場。阿根廷一氣之下揚言退賽,但還是現身以 6:3 擊敗墨西哥。小組賽最後一戰,阿根廷 3:1 擊敗智利晉級準決賽。
烏拉圭的世界盃有待世紀球場完工才開始。7 月 17 日球場落成,毫無疑問是當時世上蓋得最好的球場。容納量雖不比漢普頓公園球場或溫布利球場,但在不列顛諸島之外,9 萬人已是歷來最大。論建築之美,世紀球場則完全是不同層級。有充沛的海外投資、政府挹注,又有具建築素養的金主贊助,1920 年代末,蒙特維多興起一股建築熱潮。除了城市的中央大道與綿延的濱海大街,一種獨特而壯觀的現代主義拉丁風格也漸漸成形,建築特色包括飛騰的純白平頂、精密的幾何結構、弧形的水泥陽臺,以及玻璃磚裝飾。戰間期歐洲誕生極簡主義和現代主義,烏拉圭的建築菁英是最早一批最好學的學生。法國知名建築師柯比意(Le Corbusier)本人亦曾在 1927 年造訪蒙特維多,既是為了學習也是為了傳道。斯卡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設計出世紀球場。
世紀球場計劃成為拉丁美洲第一座鋼筋混凝土球場,雙階橢圓形結構,分成四面看臺,像一朵裝飾藝術的花,多層花瓣成扇形綻放。走道、牆面和座位設計忠於美學核心,表面光滑、圖案簡單。其中兩面看臺決定命名為哥倫布和阿姆斯特丹,彰顯奧運奪冠的榮耀。各界萬分期待第三座看臺將依相同原因取名為蒙特維多。單論這些結構,世紀球場已經非同一般,但斯卡索還在球場北面加上他的「朝聖地標」──一座 9 層樓的高塔,從百米高空俯瞰低陷的球場草坪。

從當時到現在,這座高塔始終不同凡響地昭告著現代樂觀主義。高塔底部的方牆向旁抽長,有如一架飛機優雅流線的機翼。高塔正面是一艘光滑的鐵殼船,船首指向天空。緊接著船首的是觀景臺,順著長方形混凝土凹紋立刻翻轉向上,凹紋一路延伸至塔頂高高的旗杆。沿著塔身可以看到九扇窗戶和九條幾何橫槓,呼應烏拉圭國旗的九道橫條。
就在高塔的遮陰下,在上達 10 萬名觀眾面前(該國男性成年人口的 2 成),烏拉圭先後踢掉祕魯和羅馬尼亞,晉級準決賽。準決賽第一場,阿根廷以 6:1 橫掃美國,隔天烏拉圭在一球落後南斯 拉夫的情況下也追進了 6 球──追平比分那一球,據說原本該由南斯拉夫開界外球,但一名警察沒讓球出界,接著才讓烏拉圭踢進球門。三天後,烏拉圭與阿根廷進行史上第一場世界盃決賽。
那三天消失在一陣旋風般狂亂的活動與臆測之中。歷史文獻比往常更加被傳說與謎團的漩渦吞沒。戰爭迷霧瀰漫,一如河霧吞沒了部分從布宜諾斯艾利斯航向蒙特維多的輪船。船上倒楣的阿根廷首都居民發現自己在拉布拉他河上迷航,而決賽早已落幕。
沒人真的知道實際上多少阿根廷人去了烏拉圭(估計約有 10000~15000 人),更不知道多少人真正抵達了世紀球場,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港口從未見過這等景象。有錢人搭乘私人帆船或租用專機出發。郵政部長替自己和親友雇了一艘貨輪,六名眾議院議員徵用了政府一艘靠拖船拉動的平底駁船。航線經過蒙特維多的各家大西洋郵輪營業處,或經營定期短程渡輪的公司,全都被數以萬計的群眾團團包圍。
蒙特維多當地場面一樣瘋狂。躲在聖路西亞的阿根廷隊尤其備感壓力。奇洛從對法國一戰以來就一直處於神經崩潰的狀態,無法再上場。路易斯.蒙提(Luis Monti)據說收到雙重威脅,阿根廷人威脅他不准輸球,否則就要殺他母親,烏拉圭人則威脅他不准贏球,不然也會下手。然而蒙提會來,只是因為所屬的聖勞倫佐隊的董事懇求他參賽罷了。烏拉圭民眾聚集在球隊下榻的旅館外頭等著嗆聲堵人,那更是想當然爾的事。

比賽當日,兩隊在大隊軍警陪同下前往世紀球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日常生活暫停運轉。通用汽車的阿根廷工廠停下生產線,眾議院延後議程,市內的辦公室職員擠在收音機旁,大批民眾聚集在報社門外。在蒙特維多,世紀球場座無虛席,還有上萬人徘徊在外聽場內觀眾吶喊。比利時主裁判尚恩.蘭格納斯(Jean Langenus)舉哨至唇邊,他知道自己安全無虞,因為烏拉圭政府已接受請求,會特別派人保護他自己、他的助手和家人,回程的船隻也已停妥在港口,終場哨音一響,船一小時內就能啟航。
1930年7月30日
烏拉圭4—2阿根廷
蒙特維多,世紀球場
紀念塔(Torre de los Homenajes)頂端的旗杆升著烏拉圭國旗,天空萬里無雲,國旗起初幾乎沒有展開,直到一架單薄脆弱、鋼絲加固的雙翼機嗡嗡飛過,吹得國旗冉冉飄揚。世紀球場歡聲雷動,向國旗、飛機、高塔和國家致敬。
3/4 個世紀過去,站在塔頂已看不到國旗,倒是過了 75 年,他們終於裝設了電梯。高塔後方開闊的天空,如今為灰色的混凝土巨塊佔據,那是球場落成幾年之後蓋的大學附設醫院,資金來自是同一股捐助熱潮。醫院高 15 層樓,因為年久失修,多棟病房大樓現在看起來陳舊斑駁,水管破裂、石灰剝落。
向下俯瞰球場草坪,你睜大眼睛看到了烏拉圭人和阿根廷人。半場比分 2:1,地主國在下半場踢進第 3 分。但已經沒用了,草坪四處散落著某場搖滾演唱會所留下拆解到一半的舞臺支架。足球現在幾乎填不滿世紀球場。
很快一切都會悉數消失,當年實驗採用的鋼筋混凝土,禁不起大西洋海風鹽分的侵蝕。說不定不用到 100 年。說不定氣候變遷會加速作用。拉布拉他河會淹沒這座城市,徒留球場孤立於汪洋之上,如一道彎弧的灰色浮標,提醒著過往水手,水底下有沉沒的寶藏。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沮喪的沉默籠罩住一群群失望的球迷,阿根廷國旗還收捲在他們的旗杆上沒有攤開。入夜之後,沉默讓位給了酒精和怒氣。烏拉圭領事館和菁英出入的東方俱樂部遭到街頭民眾攻擊,一名持烏拉圭國旗的女性被人丟石頭,某幾個街區出現暴民一邊演奏《脫下你的蓋頭來》(Sacarse el Sombrero),一邊揮舞著國旗遊街,堅持所有人等都要向隊伍國旗行禮致敬,誰敢不從最好小心一點。半夜街上還傳出槍響火光,警方到了大清早才終於把人群驅散。
隔天,某些阿根廷報紙對國家隊表露憎惡,指責隊員缺乏膽識,另一些則披露烏拉圭使詐,國家足球被害妄想和自我厭惡的根源雙雙由此誕生。但真正令阿根廷人失望的是球員欠缺團隊合作。義大利記者貝雷拉至現場觀賽後認為:「阿根廷人踢球優雅而富有想像力,但優越技巧彌補不了戰術缺失。拉布拉他河岸兩支國家隊,烏拉圭如同辛勤的螞蟻,阿根廷是只顧玩耍的蚱蜢。」
從格拉斯哥第一次舉辦國際賽事至今僅僅過了 60 年,最高國際賽事已經橫越汪洋來到大西洋彼岸。個人對上集體、技藝對上戰績、技巧對上力量、美感對上效率,存在於足球核心互不相容的各個極端,不單只是轉移陣地上演,對極限的探索也提升至前所未有的精細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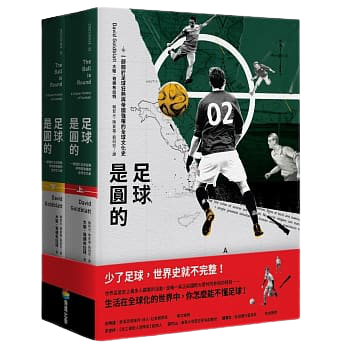
世界盃是史上最多人觀看的活動,是唯一真正由國際大眾共同參與的時刻……
生活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你怎麼能不懂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