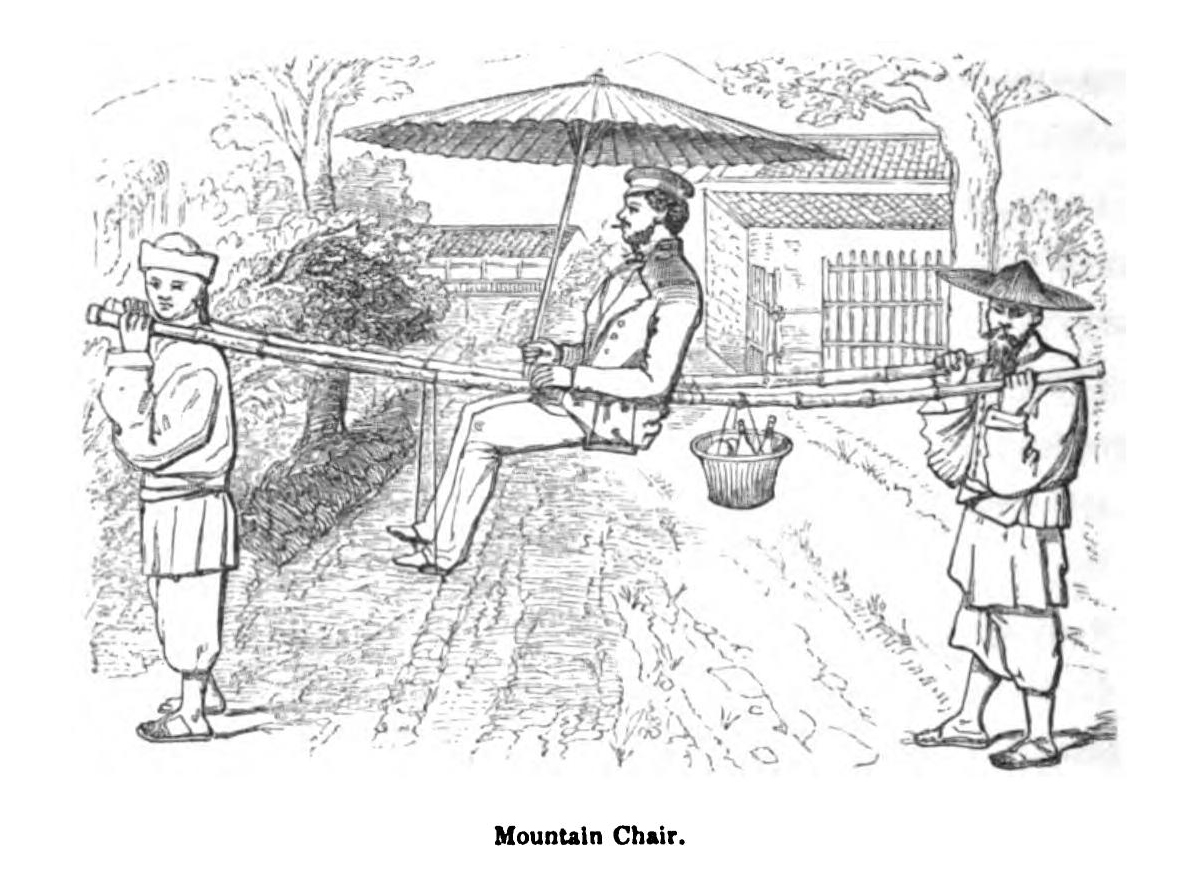2019 年 10 月 2 日是印度聖雄甘地誕生 150 周年。基於甘地的崇高形象與巨大影響,印度各界舉行了不少紀念活動,現任總理莫迪也在紐約時報上發文大談甘地的思想。但莫迪的投書引來一些讀者批評,因為莫迪長期被視為印度右翼國族主義的代表,他的任期間也出現不少爭議或迫害事件,比如警察攻入校園鎮壓學運,取消喀什米爾自治地位,拒絕穆斯林移民取得公民權等等,顯得與甘地的形象格格不入。
不過,近年卻有越來越多研究重新檢視甘地的思想,尤其是甘地在南非的言行,發現甘地其實有明顯的種族主義 [1]。從這些研究看來,甘地的思想遺產與今日印度的右翼政治風潮之間的關係可能比表面上更加複雜。本文要介紹的《博士與聖人》(The Doctor and the Saint: Caste, Race, and Annihilation of Caste, the Debate Between B.R. Ambedkar and M.K. Gandhi)一書,即是建立在這些新的甘地研究上,並以種姓制度為主題,為此一複雜關係提供了一個犀利的切片。
《博士與聖人》的作者是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而本書的原型來自她為印度政治思想家安貝卡(B. R. Ambedkar)的《消滅種姓制度 (Annihilation of Caste)》一書在 2016 年重新出版時所撰寫的長篇序言。書名中的博士即是安貝卡,因為安貝卡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以及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兩個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參與起草印度獨立憲法並擔任第一任司法部長。聖人則是指甘地。洛伊生動地分析了兩人的思想背景,尤其是甘地在南非的言行,以及兩人在種姓制度問題上的分岐與衝突。
習於通行的甘地故事的讀者,可能會覺得洛伊引述的甘地言行難以置信,大大悖離了傳統的聖人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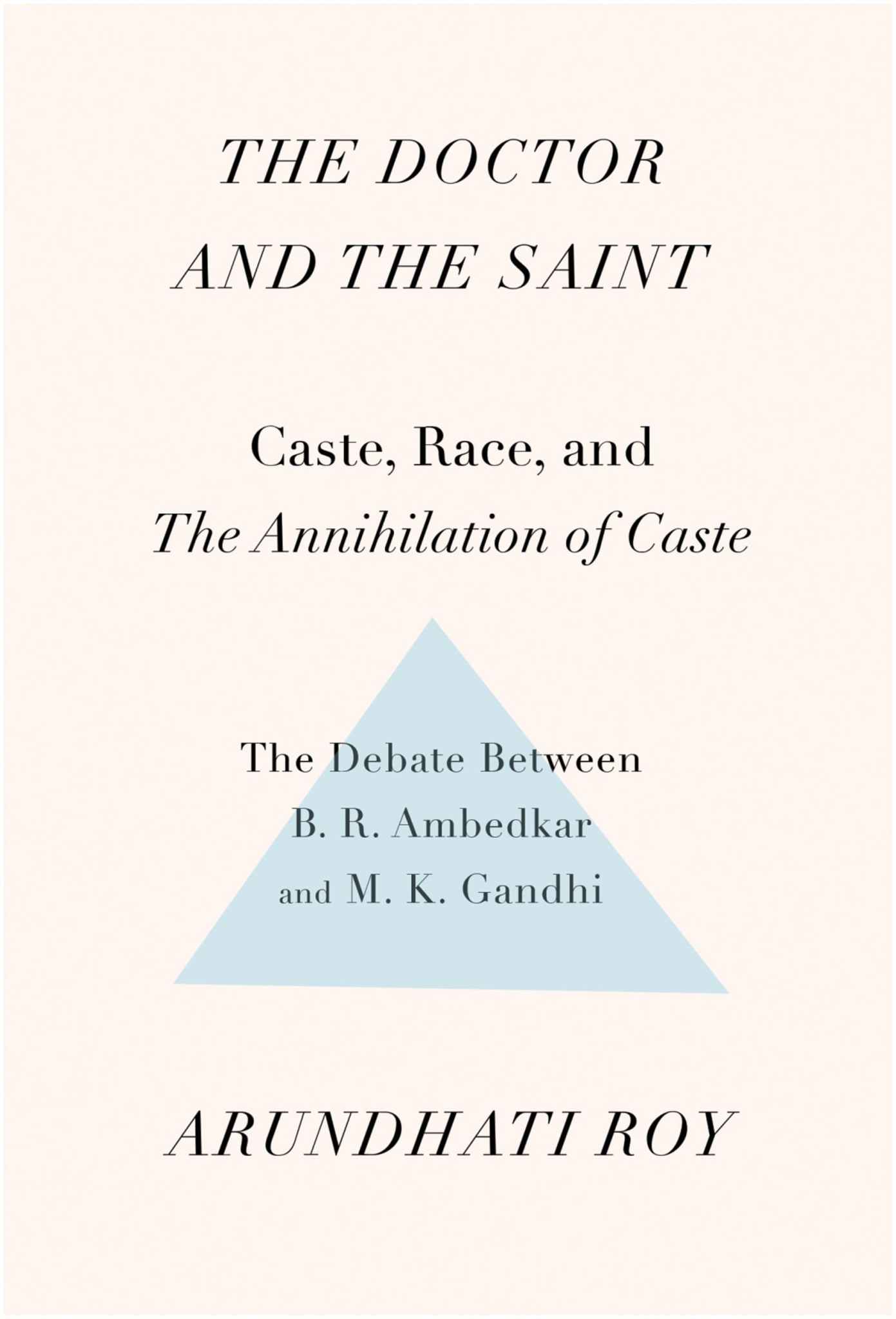
#聖人在南非
甘地的聖人形象起源於南非。
據說他在南非被白人丟下火車後,開始為印度人爭取權益,一起與黑人反抗殖民政府的種族隔離,種下了他日後領導印度窮人來反抗大英帝國的種子。然而,甘地在南非爭取的並不是全體「印度人」的權益,因為他在南非受雇於印度富商組織(多數為穆斯林,也包括高種姓印度教徒),爭取的是這些印度富商的權益。
根據甘地當時的書信與文章顯示,他其實非常鄙視當地黑人與印度苦力。他的第一個重要政治行動是於 1895 年時,爭取在德本郵局開闢第三出入口,這樣這些印度商人才不必和 (甘地認為的)低賤的黑人與印度苦力混在一起。
甘地在南非入獄時被迫與黑人關在同一個牢房,但他其實連與黑人共用同一個郵局出入口都不願意,對此甘地在信中抱怨連連,認為不被當成白人對待就算了,但被當作跟土著黑人一樣對待,就實在太過分了。甘地認為這些黑人(還有同牢房的華人)就跟動物一樣野蠻,因此還在獄中發起請願,要求牢房要分開,被單、食物、廁所都要分開。
甘地是如此深信自己與黑人、賤民不同,在 1946 年的一次賤民階級社區訪問時,甘地甚至把人們招待他的食物丟給羊吃,說自己稍後會透過喝羊奶而吃到他們給予的食物。甘地一生強調「心靈純淨」,對賤民階級或黑人的厭惡,也常歸結到他認為這些人不純淨。這不是甘地個人的特殊執著,而是印度教高種性者對賤民階級的一般看法。

此外,與日後的非暴力形象不同,當英國在南非打布爾戰爭時,甘地自願組隊參戰幫助英國人,被分配到醫護單位。稍後殖民政府鎮壓祖魯人起義時,甘地也公開發表文章,表示印度人支持殖民政府。
甘地在南非時即已頗負盛名,後來回到印度時更開始被稱為聖雄(Mahatma)。甘地作為一個精明的政治家,也積極利用此一形象,穿粗布衣服、茹素、禁慾、批評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表現得安貧樂道,強調要回歸印度鄉村傳統的純樸秩序。但與此同時,甘地依舊繼續受印度大企業家資助其政治活動,也持續維護印度傳統社會的種姓制度。
甘地得到印度富商資助,在南非購地建了自己的農場,用來維持他的特殊生活方式,進行他的純淨心靈實驗。他把農場取名為托爾斯泰農場(他有過不只一個農場,這是第二個),但他並不關心南非的土地分配問題或貧富差距。
甘地還以一種很奇特的方式實踐其禁慾思想。他讓一群少男少女住在他的農場裡,吃與睡都在一起,還要求他們一起洗澡,但嚴格禁止他們有任何具性意味的互動,用意是以此 「試煉」來培養他們的純潔心性。他在日記裡曾提到一個事件:有個少年對兩個少女開了不恰當的玩笑,這兩個少女向甘地告狀。甘地為此罵了那個少年一頓,同時認為應該也給兩個少女留下一點印記,好讓其他有邪念的人不會再將眼光放在她們身上。最後他決定這兩個少女應該剪掉她們的長髮,兩人不從,他便運用團體壓力,最終逼她們剪髮 。
甘地終其一生奉行此種試煉。在甘地七十多歲時,還曾與兩位年輕女孩睡在一起(Manu,他的孫侄女,以及 Abha),以檢測自己是否成功克服了性慾。
宗教與政治
仔細檢視甘地諸多政治上的言行,似乎都帶有強烈的宗教色彩。作為一個律師與政治人物,甘地並沒有真正鑽研過甚麼典籍,他的宗教思想獨樹一幟,是從小接受的具耆那教色彩的印度教,與西方當時的神智學和靈修思潮的奇特混合。[2] 知名理論家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甚至認為,甘地並非讓其宗教從屬於政治,也比將宗教與政治合而為一的伊朗什葉派領袖霍梅尼更極端,把宗教抬得高於政治,政治活動從屬於宗教思想。

甘地之所以吃素禁慾,一方面反映了印度教高種姓追求純潔的文化,另一方面則反映了基督教思想中對罪孽的恐懼。甘地不是嚴謹的思想家,發表過許多前後不一致的言論,但他自認真正追求的目標是修行成聖,此種人格的修行是遵循活的真理,因此不受理性邏輯或宗教典籍的僵固限制。在他的理想中,一旦他達到了聖人境界,聖人開口,全民都會聽從。
甘地也反對許多代表西方的現代性元素,例如認為機器與鐵路會帶來罪孽與瘟疫,醫院是罪惡的溫床,農民識字沒有好處,只會變得不滿足,等等。對西方現代性的拒絕,正是他與大英帝國對抗的原因之一,也貫穿於他衣食住行方面的種種表現。在這種思想下,他一再堅持印度要的不是獨立,而是 Swaraj ── 一種靈性自足、超越肉體物慾的狀態,因此他並不想將英帝國逐出印度,他的鬥爭是要印度人自我改造。一旦達成 Swaraj,便能引領英國人走向理智,甚至引導世界大同。
儘管甘地極少說明 Swaraj 的具體樣貌,但從他對一系列爭議的反應來看,他的理想似乎是以印度傳統社會為模型。他特別不希望為了驅逐英國勢力而造成社會革命,在甘地看來,無論是工人罷工或佃農反抗地主,都會破壞印度社會秩序,比英國統治更糟。
安貝卡 vs 甘地
回過頭來看,安貝卡博士(Bhimrao Ramji Ambedkar)又是何等人物呢?
印度的種姓區分方式相當繁複,若按照最粗略的分法,可分四大階級: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安貝卡博士則出身於比四大階級還低下的賤民階級。安貝卡由於當時殖民政府推行新法規之故而被允許上學,但他依然不能與高種姓者坐在同一個教室,也不能喝同樣的水。即便後來他幸運得到獎學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與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取得兩個經濟學博士學位,他回到印度時依舊被當賤民對待,一度因為沒房東願意接納而找不到住處,從公共水井取水也被百般刁難。

與甘地不同,安貝卡篤信啟蒙理性,希望透過政治經濟制度的改革實現自由平等博愛,也提倡現代工商業的發展。在安貝卡看來,賤民之所以是賤民,只能從事社會地位低下的工作,是因為其他高種姓者掌握了土地、水源、道路、金融、教育等各方面的資源,一旦賤民反抗或稍有逾越的言行,高種姓者可以對賤民恣意燒殺擄掠,或者實行社會抵制,讓賤民沒地可耕、沒水可喝,連去村裡的雜貨店買東西也不行。政治上,賤民在每個村莊裡都是相對少數與弱勢,所以如果按照傳統的地方政治模式,賤民永遠逃不出高種姓者的手掌心。
也就是說,在安貝卡認為賤民問題是政治經濟上的權力問題。
但甘地並不這麼想。
甘地 1936 年(與安貝卡發表《消滅種姓制度》同年)寫了篇文章,叫做〈理想的賤民 〉(The Ideal Bhangi),裡面描述了他認可的賤民形象:
- 婆羅門的責任是維護心靈衛生,賤民的責任是維護人們身體的清潔衛生。
- 理想的賤民應該熟知怎麼把糞便與尿液轉化為肥料。不僅如此,他們還應該仔細檢查人們的糞便與尿液的品相,並適時提醒人們注意健康。
- 理想的賤民應視祖傳的職業為神聖的責任,以此維生,不求發財。
在甘地一生的許多著作中,經常主張印度應該拒絕西方的工業化資本主義,發揚印度傳統文化。甘地認為賤民問題屬於文化問題,他改變賤民的稱呼,開放賤民進寺廟,主張賤民遭遇的問題可以透過溫柔勸說,慢慢移風易俗。
也就是說,甘地反對的只是認為賤民穢不可觸的文化(untouchability),而不是決定政治經濟資源分配的種姓制度本身,在他眼中,後者可避免西方強調自由與人權所帶來的貪婪僭越,以及由此導致的無良競爭與社會撕裂。他認為不同種姓各司其職,互不通婚,並不代表種姓制度意味著等級制。婆羅門與賤民階級之間並沒有地位高低的問題,因為只要他們恪守其天生的職責,領取相應的生活報酬,不貪圖更多,他們在神眼中都是平等的。
基於如此分歧的看法,在政治上如何處理種姓制度,成了甘地與安貝卡最大的衝突點。
在 1931 年由英國殖民政府主持,討論印度立憲議題的圓桌會議(Round Table Conference)上,安貝卡主張應該賦予賤民獨立的政治代表權,以十年為限,讓賤民階級自己獨立選出自己的代表進入議會(而不是讓主流政黨設賤民保障名額),但同時也可以參加一般的選舉。這種雙重選舉權類似於日後的積極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其他少數族群的代表也提出爭取。

甘地同意給予穆斯林與錫克教徒雙重選舉權,但對賤民階級則堅決不讓步。甘地批評,那些主張予賤民階級獨立政治權力的人完全不了解印度社會的構成,一旦給予賤民階級獨立政治權力,印度社會將會被撕裂,因此他誓死反對。會議過後一年,1932 年,殖民政府決定賦予賤民階級獨立的選舉權,為期 20 年。當時甘地正在獄中,為了表明反對此一政策的決心,他在獄中開始絕食抗議。此書作者洛伊對此寫道:
這實在非常諷刺,高種姓的印度教徒向來想盡辦法要把賤民階級隔離開來,他們要隔離食物、水、學校、道路、寺廟、水井,現在居然說如果賤民階級取得獨立的選舉權,印度就會被撕裂(巴爾幹化)...
但此時的甘地早已是國內外一致推崇的聖人,他絕食的消息一傳開,輿論就沸騰了。殖民政府推卸責任,回應說只要賤民階級同意,它願意撤回政策。於是巨大的壓力排山倒海湧向安貝卡,要他讓步妥協。高種姓團體也趁機軟硬兼施,一邊舉辦活動與賤民分享食物,暫時開放寺廟,一邊鼓動恐怖情緒,讓賤民恐懼一旦甘地絕食而死,將出現殘酷報復。
在如此聖人面前,博士哪裡是對手。甘地絕食四天之後,安貝卡迫於形勢不得不妥協,前往獄中與高種姓代表簽下波納協定(Poona Pact)。最終,賤民階級雖以保障名額的形式進入議會,但因為候選人要得到高種姓者的同意才可能出線,形同被拔了牙齒的老虎,實際作用有限。
結語
許多人或許會將甘地與安貝卡衝突的原因,詮釋為兩者都想去除種姓制度,只是甘地是溫和保守派而安貝卡是基進派,因為對情勢的判斷不同才選擇了不同的策略。但由前述介紹可知,此種看法可能低估了他們兩人政治思想之間的鴻溝。
莫迪在其紀念甘地誕辰的紐約時報投書中指出,當全世界都在談權利時,甘地則強調「責任」。他引述甘地的話:「權利的真正來源是責任...只要盡了責,權利自會隨之而來」。我們若把甘地思想放回前述歷史脈絡中,便能了解甘地本人所談的權利與責任仍深埋於種姓制度框架裡,與西方哲學中關於政治責任(political obligation)的討論其實貌合神離。

當然,上述這些關於甘地的歷史紀錄與分析,並不是要否定甘地在印度獨立建國過程中的關鍵作用。恰好相反,這些分析是要幫助我們弄清楚,究竟甘地是「為何」與「如何」起作用的。例如,許多人都指出,甘地超越當時國大黨其他領導人,從而改造了國大黨的地方之一,是他能夠鼓動農村居民,發起真正的大眾動員。但當時的農村居民為何響應甘地的號召?前述的分析提醒我們,甘地的動員能力恐怕與其擁抱種姓制度的宗教思想,從而能夠喚起保守民眾的認同脫不了關係。
歸根到底,政治領袖的思想固然能在關鍵時刻發揮決定方向的作用,政治領袖及其思想本身也是歷史條件、群眾情感與意識的產物。歷史確實有打破預期的、躍進的時刻,但其躍進的方式與姿態,往往已被過去的傳統預先決定。
[1]例如 Ashwin Desai and Goolam Vahed 於 2015 年出版的《南非的甘地 (The South African Gandhi)》一書。
[2] 請參考 Kathryn Tidrick 所著的《Gandhi: A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Life》一書,從甘地的宗教思想解讀其政治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