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也奇怪,羅馬葡萄酒的征服範圍竟然比羅馬軍隊還大。羅馬軍隊進入日耳曼尼亞,來到條頓堡森林(Teutoburg Forest),全軍覆沒,再也沒回來過。但羅馬葡萄酒進入了日耳曼地區,來到條頓森林,本地人飢渴暢飲,想喝更多。
當地人非常飢渴。想像一下有一群原始的日耳曼人,一整年都在舉行很陽春的啤酒節,大概就對這情況略知一二。
一天一夜的狂飲並不丟臉。他們和每個飲酒的人一樣會發生口角,拳腳相向,鮮少只是辱罵,通常會受傷掛彩。
這是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 [1] 的紀錄。他還說,日耳曼人在做政治決策時,完全是爛醉如泥,並認為這樣才誠實:

現代政治實在應該採用這種政策,這樣電視訪談會更有趣。這當然是「酒後吐真言」的極致。如果政治充滿謊言與騙子,而酒能讓人說真話,那麼灌大家一堆酒(真理的母親),豈不是很合理?這是有道理的,就像中國人與印度人認為統治者絕不該喝醉也是有道理的。採用這種方式無疑可能會引發更多戰爭,但至少知道原因何在。
塔西佗也提到,日耳曼人雖然自己釀啤酒,也會進口羅馬葡萄酒,還用羅馬的金酒杯喝羅馬酒。我們會知道這一點,是因為野蠻人的國王喜歡以最昂貴的酒器陪葬。他們相信身邊會需要這種酒杯,才能在永恆中和他們崇拜的奇奇怪怪神祇狂飲。當然,他們的如意算盤打錯了,因為現代考古學家很沒品,把他們挖出來,拆散了他們與酒器及神祇。
羅馬帝國衰微、失敗、瓦解了,但葡萄酒貿易並未中斷,繼續供應著愛喝葡萄酒的汪達爾人(Vandal)與愛喝啤酒的哥德人(Goth)。問題是,這些人一直處於野蠻狀態,未對飲酒習俗寫下隻字片語。我們只能略瞥見一二,但光芒很快熄滅。這就是黑暗時代。
我們確實瞥見的一眼,是五世紀出身希臘的羅馬外交官普利斯庫斯(Priscus)所寫下的。普利斯庫斯在西元四四八年曾與匈人(Hun)皇帝阿提拉(Attila)一起晚餐。這是一場外交任務,因為有人偷了阿提拉珍貴的羅馬飲酒杯,阿提拉相當惱火,除了要回酒杯,還與酒杯的新主人見了面,一位叫做西凡納斯(Silvanus)的羅馬人,然後殺了他。

普利斯庫斯被派去安撫這位史上最暴力、最令人聞風喪膽的統治者;在等候一會兒之後,他在三點鐘時受邀到阿提拉最大、最喜歡的房子參加宴飲。
他被帶進一間大廳堂,桌子沿著牆壁排列。阿提拉的桌子在中間,床就在後面的平臺上。這位好戰者的周圍是與他最親近的家人,看起來並不開心。阿提拉的長子很害怕父親,只敢盯著地上。其他賓客依照年長順序,沿著房間周圍坐,右邊的階級比左邊高(和羅馬饗宴一樣)。普利斯庫斯的桌子在左邊的最後方。
每個人都得到一杯酒,依照習俗,喝一小口之後,在位子上坐下。接著開始敬酒。
這一定花了很長的時間:冗長的形式兼有恐怖、無趣與討厭的座位規畫,和現代婚禮一樣。最後食物端上來,大家開始吃吃喝喝,享受一番。只有阿提拉例外。他從來不笑,只和他嚇壞的家人坐著,看著所有的賓客吃銀盤子上的東西,自己則吃裝在木盤上的東西。
之後,有個發瘋的斯基太人與摩爾侏儒被帶上場,開始搞笑,人人都捧腹大笑,只有難搞、野蠻又矮小的阿提拉依然繃著一張臉。夕陽西下,火把點上,普利斯庫斯明白這天晚上完成不了任何事,「整個晚上幾乎都耗在宴會,之後我們離開,不願再喝酒。」
普利斯庫斯回到君士坦丁堡寫歷史書,而阿提拉死於流鼻血。
修士也為酒瘋狂
野蠻人在歐洲到處出沒,令人不堪其擾。他們愛酒,卻不清楚酒是怎麼製造的。以前在遙遠的大草原時,他們會製作一種有趣的飲品,叫「馬奶酒」(kumis),是用馬奶發酵製成,可以邊遷徙邊製酒。當他們短暫停留時,則可用穀類製作麥酒。但釀製葡萄酒需耗時多年,悉心栽培葡萄園,野蠻人不懂。因此他們會出現,喝光葡萄酒,把葡萄園燒掉,卻搞不清楚怎麼沒有葡萄酒可喝了。他們心情很差,騎上馬到另一座城鎮,重蹈覆轍。

整體而言,無辜的旁觀者時運不濟,許多人決定不再忍受。這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修道院的發展。
修道院是寧靜的地方,由於遠離城鎮,比較安全。一旦說服野蠻人成為(名義上)的基督徒,那麼基督教修道院(表面上)就是個安全的地方,可以坐下來放鬆,喝個爛醉。
這股趨勢是在六世紀時,由聖本篤(St. Benedict)開啟。他建立幾間修道院,並著手寫下規則。本篤是個明智的人,因此這些規則並不嚴苛。第四十條規則使得飲酒完全無法禁止
一赫明納的酒大約就是現代的一瓶酒,或許少一丁點兒。[2]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怎麼可能足夠?要是天氣很熱怎麼辦?要是口渴怎麼辦?要是你做了些蠢事(例如運動),需要喝酒怎麼辦?難道聖本篤是怪物嗎?
不是。聖本篤是善良體貼的人,早就把這些事列入考量。因此這規則還沒完:
你的選擇只有加入本篤修道院, 或是留在家裡, 任由每個路過的西哥德人(Visigoth)人掠奪。無怪乎修道院蓬勃發展。這並不是因為本篤認為修士必須喝葡萄酒,或喝酒值得讚揚。

其他修道院對於酒的分配量沒說得那麼清楚,但從規定來看,酒顯然是喝得到的,只要不喝醉即可。如果喝到站不起來,無法歌頌詩篇,就會受到嚴懲。最極端的懲罰是六十天的禁食,但這只有在你爛醉到把聖餐吐出來才會發生。本篤顯然知道,沒有酒,就會有麻煩。因此四十條規則的最後如此寫道:
當然會有人抱怨。黑暗時代的修士與民眾都需要酒,否則只能喝水。水需要良好維持的水井,最好有引水道,但這需要有效率的組織、政府及黑暗時期所缺乏的一切。少了這些條件,最好的水源就是最近的溪流,而對於並非住在高山區的居民來說,溪流多半汙濁。
從最近的溪流所汲取的水很少透明清澈,幾乎可確定含有恐怖的東西,例如蟲子、水蛭。有一本盎格魯薩克遜的書,提出吞下可怕東西時的療法:立刻喝一點熱的羊血。這告訴我們兩件事:(一)水很噁心;(二)但人們有時還是得喝水,因為你可能口渴,買不起更好的東西。一般盎格魯薩克遜人對這件事的態度,可從修道院院長艾弗里克(Abbot Aelfric)的名言看出:「有麥酒就喝麥酒,沒有的話就喝水。」
[1] Tacitus,西元五六到一二〇年,羅馬帝國執政官、元老、知名歷史學家。
[2] hemina,約二七三毫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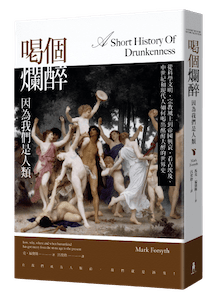
世界上幾乎每個文化都會飲酒,而人類永遠有想要酩酊大醉的衝動,於是所有的文明都會為酒醉尋找一個位置,或設法加以控制。
如何看待喝酒這件事,由古至今都充滿悖論與荒誕,也與現代化中的性別、階級與殖民息息相關。
且讓我們跟隨這本書,從羅馬的飲酒杯、修道院的酒桶,再到殖民地罪犯的酒瓶,一杯接著一杯,以全新的視野觀看這場酩酊大醉的世界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