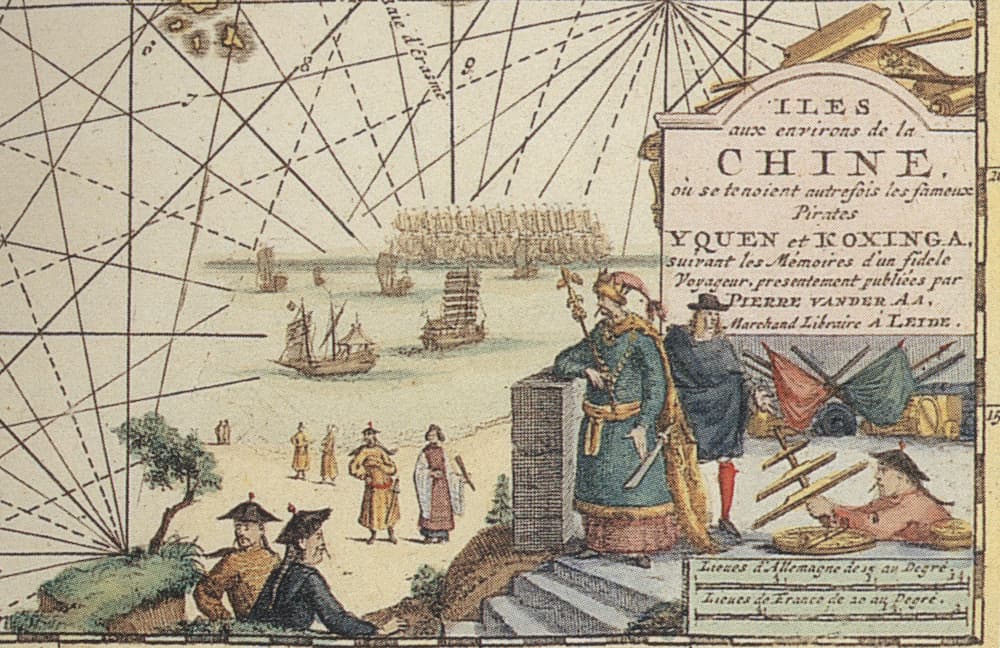朝鮮各種《燕行錄》文獻中,不僅只是旅行見聞而已,另外還記載有明清時期許多書商、書販與出版目錄的相關資料,若是細加摘錄整理,或許可以對我們理解清代的出版文化以及政治氛圍,提供來自域外的特殊觀察視角。
《燕行錄》記載中,即有當時朝鮮使臣與清人討論學術的對話,談話的主題,其實也涉及清朝與朝鮮在出版文化上的若干交流現象。例如:朝鮮使臣時常向清朝文人問及浙江李霈霖(生卒年不詳,乾隆嘉慶年間人士),他們多半認為李氏是當世大學者,聲名卓著,在朝鮮士林學子之間為人共所周知。但朝鮮使臣與不同讀書士人求證的結果,則與此大不相同。
對清朝文士而言,李霈霖只是一名富有商人,雖然他廣延各方學者刊書,但徒為謀利而刊行圖書,並非是研究學問的儒者文士。朝鮮使臣們在多方查證後,方才相信李霈霖此人雖然在朝鮮文壇頗有盛名,但是在清朝卻不過是一位以印刷為業的富人而已。相較之下,各種類似的傳聞掌故,甚至是明清宮廷軼聞,可以說散見於燕行文獻之中,讓人讀起來別有特殊的文化趣味。
筆談世界裡的交流互動與清朝政治文化的觀察
東亞使節的外交活動中,普遍出現彼此以紙筆對談溝通的特殊情況,可以說當時存在著筆談文化。而東亞筆談文化,其實就是一種「無聲的歷史」,也是私人日常生活領域中的一個特殊場域。這一類朝鮮使臣與清朝文士之間的筆談紀錄,可以說散見於明清以來的燕行文獻中,提供人們有關明清宮廷文化、政局變化,甚至是庶民社會各方面的詳細紀錄。
事實上,朝鮮使節的筆談對象並不僅僅局限於明清兩朝有功名的士人們,燕行文獻實際上可以說是廣泛觸及朝鮮使臣在使行旅途中所遇到的各個能進行文字筆談的識字階層人士。近年來已有研究者注意到相關問題,並且進行討論,也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發表。

綜合各方面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看到朝鮮使節們的任務雖是為了國家而進行的外交,以及重要情報訊息的搜集工作;這些燕行文獻並依照朝鮮官方的典章制度,而被保管收藏於「承文院」之中。但若換個視角來觀察,則朝鮮使臣留下的許多與當時清朝官員與士人們的筆談紀錄,提供了一種呈現清代日常生活面向的獨特史料。
朝鮮燕行使節們可以說是透過「筆談」的交流形式,以極其私人的媒介載體,逐日詳細記錄下了各種清朝見聞經歷的重要域外史料文獻。經由這些域外史料,我們得以一窺其時私人領域中的各項政治議論,以及私人空間中所呈現的歷史敘事,甚至還能觀察到清代國家權力在其中所發揮的巨大影響力。
另外,這一些保存在朝鮮燕行文獻中的私人筆談紀錄,往往含括許多清朝宮廷祕聞與街談巷議,例如乾隆六年前後,洪昌漢(乾隆年間人士,生卒年不詳)曾在《燕行日記》中記載了朝鮮使節與通事官之間的議論,隱隱約約中,記錄下了一些有關乾隆皇帝的私生活軼聞。
像是當時通事官金普柱(乾隆年間人士)等人就曾在言談中提及乾隆帝的宮廷軼聞,他說「胡帝昨歲得十九歲美女,色可傾國,極寵溺」,皇太后並因此責備乾隆皇帝沉迷於女色之中。乾隆皇帝後來更因此緣故,不再入見皇太后,並時常帶著這一位年輕的女子同到圓明園內遊樂,以此來逃避皇太后的責備。類似的宮廷傳說其實並不少見,乾隆年間朝鮮使節們可以說為清代的宮廷祕聞留下了一個來自域外的側面紀錄。
這些紀錄甚至包括了有關乾隆朝後宮后妃的各種傳言,並且提及乾隆皇帝的廢后,也就是皇后那拉氏(1718-1766)被幽廢一事,甚至記錄下了當時在北京城中傳講的各種街談巷議的具體細節。例如朝鮮使臣洪大容就曾經在《湛軒書》中寫道:「近日以皇后幽廢,宗親皆憂怖不寧⋯⋯」這一類有關乾隆朝後宮的傳聞,繪聲繪影,甚至還描述當時清朝皇室眾多宗親都相當憂慮恐懼。
洪大容在另一段紀錄中進一步描寫他曾與某位清朝文士談及此事,他向清人詢問皇后幽廢之事,清朝文士則回答說,皇后仍然在冷宮之中。洪氏接著又詢問,皇后被囚廢,朝廷眾臣們為何無人諫言?清朝文士回答說乾隆帝的皇命威嚴,「人皆畏死」,所以又有誰能為了皇后之事,敢於諫言呢?洪大容聽聞之後,內心深覺為人臣慮立身事君,怎能只顧念身家性命的保全,於是頗為感慨的說:「朝廷可謂無人矣。」

實際上,我們透過相關文獻記載,可以看到洪大容為了探問宮中祕聞,用盡了各種手段,多次嘗試向清朝士人詢問乾隆皇帝廢后的傳聞。他甚至用許多小紙片與清朝士人筆談,試圖以此來取信於清朝士人。而且在筆談過程中,清朝文士往往將小紙片「隨書隨裂」,絕不留下任何證據。
洪大容在《乾淨衕筆談》中便描寫到筆談中每當提及清朝宮廷祕聞時,清朝文士便頗為驚動,舉措慌張忙亂,急忙將小紙片隨書隨裂的緊張情況。最後,清朝文士似乎不願多言宮廷禁聞,便在筆談中向洪氏直言國法森嚴,擔心恐有性命之憂,所以才會有這些無法自覺的慌張舉動。清人在筆談的最後還提及滿洲侍郎阿永阿力諫不可廢后,幾近於死。
相較之下,朝中漢臣們卻無一人敢於諫言。類似洪大容的筆談內容在朝鮮燕行文獻中相當常見,這些筆談可以說是一種極為特殊的紀錄,為後世保存下其時私人議論中的政治文化氛圍,也提供了我們有關清代士人們對於時局世事的第一手觀察。

朝鮮使臣對於清朝政局的評論與使行旅途見聞
除了上述的東亞筆談文化之外,朝鮮王朝的燕行文獻紀錄中,還包括朝鮮君臣朝議奏對的對話,並且記錄下了朝鮮使臣與朝鮮國王對於清朝政治局勢,以及清朝宮廷重要成員身體狀況的評論與實地觀察。例如:朝鮮使臣任應準(1816-1883)在光緒六年出使清朝,在其返回朝鮮後,曾在「熙政堂」的奏對中向朝鮮高宗(1852-1919)報告,提及清朝正在進行軍事備戰,而且已經陳兵部署在各處海口關要的重要位置,試圖以此預防俄羅斯出兵要脅。
但是相關軍費支出開支龐大,致使國家出現「銀貨窘絀」的困境。此外,任氏還在報告中提及光緒皇帝年幼繼位後的概要,並說明這次出使日程較長,比以往更費時日,主要是因為清朝「事務浩繁,虞憂多端」、「凋弊莫甚」,朝廷上下正值多事之際。
朝鮮高宗更在此次奏對中,特別詢問清朝兩宮太后的健康情況,並提及慈禧皇太后(1835-1908)平日即有患病,加上剛又獲聞慈安皇太后(1837-1881)因病逝世的訃報,朝鮮高宗因此更加關切慈禧皇太后近日的身體情況。任應準便回答說在出使北京的時候只有聽聞到慈禧皇太后患病之事,等返國途中進入朝鮮境內,方才聽到清朝皇太后病逝的傳聞,但未能確認,一直要到回到朝廷述職後,方才知道慈安皇太后已經病逝之事。
朝鮮高宗認為清朝正當「意外之喪」,財政上必定多有窘迫,另外又進一步詢問任氏有關清朝乾旱災情的具體情況。任氏在回答中提及去年冬天出使前後,正逢大雪,但是山海關內則是「土乾塵漲」,而且北京附近「一直亢旱」,清廷雖然曾舉行過五次祈求雪雨的儀式,但是「終無靈應矣」。朝鮮高宗提及近日傳聞離北京不遠之地發生火災,想必也是因為旱災所致。

此次奏對的內容可說相當豐富,特別是朝鮮君臣顯然非常關注清朝與俄羅斯之間的紛爭衝突,以及議和與賠償費用數目的細節。清廷如何應對俄羅斯的軍事行動與防禦方案的相關情資,顯然成為朝鮮君臣關切重點之一。朝鮮高宗相當重視此事,詢問俄國收兵之後,清朝在各處的陳兵部署是否也已經罷還撤去。任應準回答中提及俄方鋪張聲勢,聲稱將要發兵攻擊,以此恐嚇清朝。
清廷不得不籌備防禦方案,部署大量兵力,但是軍需方面卻無法持續供給。因此備戰只持續了半年,朝廷便開始有議和的主張,最後尋求與俄國議和,簽訂和約,避免兩國再有衝突。除了上述任應準的燕行報告外,《承政院日記》的記載中也留下了不少類似的君臣朝議奏對,以及對於清朝政局的分析,甚至包括對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等多位帝王的評價,可以說為清朝宮廷文化留下了相當珍貴的第一手觀察。
相較於政治中樞的情況,燕行文獻還提供了有關清代日常生活與政治文化特殊氛圍的觀察紀錄。事實上,朝鮮燕行文獻中記錄了許多使臣們與清朝人時常提到一些有關滿漢矛盾的日常生活細節。例如乾隆十四年以書狀官身分出使清朝的俞彥述在《燕京雜識》中,便曾詳細描述了清朝漢人心中的滿漢心結。清朝漢人百姓在面對朝鮮使節的當下,常常會隱諱滿漢之間,彼此已然通婚的事實。
俞氏描寫到清朝官署衙門之中,「滿漢便同主客,氣勢懸殊」,漢官職掌文書,滿官則主掌印信,呈現出一種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圍。清朝立國之初,原本滿漢並不彼此婚嫁,但年歲漸久,滿漢之間也開始通婚。但是漢人們並不願意朝鮮使臣知曉此事,猶然以此為羞。
俞氏還寫道自己曾在北京遇見一位南京人士,因為家貧而想與滿人通婚,所以育養女兒,卻不為其裹足。後來,這位南京人士的兄長來到北京,聽聞弟弟想與滿人結親,十分氣憤,不僅嚴厲責備,甚至還因此失去兄弟情義,最後憤而離去。俞彥述觀察到隨著清朝習俗逐漸變化,滿漢通婚之後,由於貧富不同,「滿人之家,漢女甚多」。俞氏深有感嘆,認為「誠可憐也」。
另外,燕行文獻還記載了一些清朝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文化衝擊現象,清朝百姓與朝鮮使者之間,常有一些政治文化方面的誤解。例如朝鮮使節團官員的衣飾時常被北京鄉人誤認為戲服,因為在當時由於清朝官方對於冠服的禁令,只有在戲曲演出時,才能穿著明代衣冠服飾。雙方在衣冠制度上,產生了一種文化上的衝擊,朝鮮使臣與譯官就此事進行了筆談對話,並記錄了彼此的意見想法。

朝鮮使節團成員之一的李岬(1737-1795)曾經在《聞見雜記》記載了類似情況,也可以作為例證。李岬寫道清朝百姓們對於衣冠服制的改變,頗有想法,因而每次在與清人交談的過程中,問到衣服制度之事,漢人都會「赧然有慙色」。而且清朝百姓有時還會自我解嘲一番,解釋說這是依循當下法令,何況剃髮之後,比較方便,不再有「梳櫛之勞」。
而且無論貴賤,衣冠均是如此,所以也就沒有什麼名分之別,制度很是簡易,甚至在平日執事服役的工作中,也沒有什麼妨礙。不過,有的清朝老百姓則會向朝鮮使者大發感嘆之言,提及朝鮮使臣所穿服裝正是自家祖先的衣服,並且家裡還藏有明朝的舊時衣裳冠服,甚至還會表達對於中華衣冠文物的欽慕之情。李岬在交談的最後,特別提及在使行途中看到明代衣冠只能見於戲曲表演之中,感覺到四海之內皆是「胡服」,愴然感嘆「中華文物,蕩然無餘」。
衣冠制度的討論之外,筆談紀錄還包括對於清朝禁燬圖書之事的相關議論。例如朝鮮使臣徐浩修(1736-1799)在1790年出使清朝時,就曾與禮部侍郎鐵保(1752-1824)交遊往來。
徐氏曾詢問鐵保:
《牧齋集》方為禁書,閣下何從得見?
鐵保則回答:
凡禁書之法,至公府所藏而已,天下私藏安能盡去⋯⋯
錢謙益(1582-1664)的《牧齋集》雖然是清朝官方禁書,但是禮部侍郎鐵保依然可以閱讀到此書。鐵保可以說是一語道破箇中虛實,清朝官方所謂的禁燬圖書,不過只能禁官家公府所藏;天下之大,各種民間私藏圖書安能盡去?
類似記載並不少見,像是朝鮮使臣朴思浩在 1828 年出使北京,他也曾對清代禁書政策提出嚴厲批評。特別是針對康熙一朝召集文士纂修圖書,提出了他對於清朝政治文化的一種域外觀察與評論。朴思浩認為此事實為「賺得英雄之術」,並非為了倡導文化。康熙皇帝的政治企圖所在只是為了讓清朝豪傑之士,「埋頭蠹魚之間,不知老之將至」。
朴氏認為康熙皇帝巧妙利用考校書籍,徵集天下文士的做法,一方面既可讓海內豪傑之士安心於書本學問之中,另一方面又可消除讀書人內心各種不滿,進而使其「憤嘆之心,如雪遇陽」。事實上,這些滿漢之間的政治忌諱,以及清朝政治文化中的隱約幽微之處,很難在一般史料文獻中得到如此細緻的印證。這類紀錄雖然較為早期,但可以作為來自域外之人的一扇有助於我們觀察清朝政治文化的特殊窗口。
.png)
從皇家御宴上的雅緻菜色到京城百姓的日常點心;從來自歐洲的自動人偶到西域進獻的獅子;從高僧法骨串成的御用念珠到皇后親手縫製的刺繡荷包,王一樵以生動淺顯的筆觸,描寫古代旅人的所見所聞,以及他們對明清兩朝的深刻觀察。域外之人,往往提供了一扇窗口,讓我們可以透過他們的雙眼,找尋到這些發生在紫禁城中,令人神往不已的有趣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