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是美國電視史上最精彩而有趣的政治辯論,並完全反映了六十年代的衝突與焦慮。
1968 年是美國最動盪狂亂的一年。越戰越來越血腥,金恩博士和參議員包比肯尼迪(Robert Kennedy)先後被暗殺,學生佔領哥倫比亞大學……
憤怒、哀傷與迷惘,從美國歷史的黑暗之處猛烈襲來。
那一年也是美國總統大選年,共和黨在邁阿密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民主黨在芝加哥召開全國大會,人們都在關注誰會是兩黨的總統候選人。美國三大電視網中收視率最差的 ABC 電視台想到一個奇招,請兩位著名作家在電視上辯論: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 和維達爾(Gore Vidal)。
巴克利和維達爾這兩人分別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且,他們極度厭惡彼此。
ABC 的媒體新聞稿如此說:「巴克利和維達爾將用他們特有的風格『討論』全國代表大會的人物和議題。做為當前政治最尖銳的觀察者,保守派的巴克利和敢言的自由派維達爾想必會有很多不同意見。」
巴克利曾出書批評耶魯等菁英學校太左傾,捍衛四處獵巫左翼份子的參議員麥卡錫。1955 年他創立保守派刊物《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其內涵綜合了保守主義的三大支流:經濟自由放任主義、傳統主義和反共產主義,開啟了當代新保守主義運動。
維達爾在 1946 年出版第一本書,1948 年的小說《城市和支柱》(The City and the Pillar)則讓他大紅也很爭議──因為主角是一名男同性戀且書中有同性性關係的描寫。此後他寫小說、寫歷史、寫政論,是暢銷書作者,作品也被改編成電影。他毫不掩飾對同性戀的支持,雖然並未正式出櫃。維達爾的箴言是:「永遠不要拒絕有發生性關係或上電視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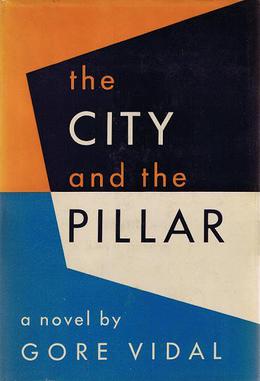
這兩個人都具有知識分子稀有的明星光環:他們都上過《時代》雜誌封面,都經常上電視節目(克利從 1966 年開始主持自己的節目 Firing Lines[1],經常邀請不同立場的人如喬姆斯基、諾曼梅勒與他辯論),甚至都參選過公職(巴克利選過紐約市長,維達爾選過紐約議員,但都沒當選)。他們瀟灑自戀,能寫能辯又風趣,極有個人魅力,且都有強大的身世背景和社會關係:巴克利出身富有家庭,和尼克森與雷根都是好友,維達爾的祖父是參議員,他個人與甘迺迪總統、艾蓮諾羅斯福都是好友。
有人說,巴克利是「他那時代最好的辯論者」,維達爾是「他那時代最好的演說者」。
在六零年代,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反文化、嬉皮、性解放,正在定義一個新美國,一切舊的秩序與規範都在崩解。維達爾積極擁抱並且支持這些改變, 巴克利則是反對甚至痛恨這些改變。就在 1968 年初,維達爾出版了一本性幻想的小說Myra Breckinridge(兩年後改編成電影) ,巴克利嚴厲批評形容這本小說是變態色情。
兩人第一次針鋒相對是 1961 年各自在美聯社的專欄上。1962 年,維達爾在電視節目上批評巴克利和《國家評論》,巴克利本來傳訊息給節目主持人:「請告訴維達爾不論是我或我家人都不想接受一個粉紅酷兒的道德教訓。」但他進而要求上電視反駁。在節目上,他將保守派觀點講得清晰有理,改變之前許多人對保守派組織如約翰伯奇學會(John Birch Society)的負面印象。 這是巴克利第一次上電視節目,他馬上就知道如何掌握這個大眾媒體。
兩年後,他們在電視上同台評論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當然氣氛很不好。
當 1968 年 ABC 電視台問巴克利有沒有哪個人是他不願同台辯論的,他只說了一人:維達爾。但維達爾在後來也說是他先被邀請,並表示不願意和巴克利同台,只是因為不願意讓巴克利掌握機會傳播理念,才不得不去辯駁他。
最終他們願意一起舉行十場電視辯論會,各自的費用是一萬美元(約莫今日的七萬美元)。
2
紀錄片《最好的敵人》(Best of Enemies) (2015)回顧了這系列辯論,影片不僅重現當年辯論片段,也討論當時的歷史脈絡及對後來電視文化的影響。
在這十場電視辯論中,兩人在越戰、種族主義、美國在世界政治的角色、貧窮問題、法律與秩序、對異議的容忍,以及如何看待性解放的問題,全都針鋒相對,呈現了六十年代巨大對立的兩種世界觀,他們的言語犀利、博學、機智、具有思想性,又毫不留情的嘲諷彼此,精彩而迷人。
不過,一開始他們雖然保持著幽默與節制,但越來越從對政治的討論轉為對個人的攻擊:他們都把對方視為會把這個國家帶向沈淪之路的體現。觀眾作為圍觀者也越來越嗜血,渴望更刺激、更衝突性的內容。
最後一場辯論出現了最激烈的攻訐。那一天正是美國六十年代與政治歷史上最讓人難忘的時刻之一:在芝加哥的民主黨代表大會場外,群眾和警察爆發激烈的暴力衝突,抗議者被警察打到血流滿地、哀號遍野。

維達爾和好萊塢明星好友保羅紐曼與知名劇作家亞瑟米勒也走進街頭的催淚瓦斯煙霧中。
在當天稍晚的辯論中,電視不斷播出警察毆打學生的畫面。
巴克利當然對這些搗亂的傢伙深惡痛絕,批評那些抗議傢伙拿著胡志明的標語。「昨晚我住在十四樓,整晚我聽到幾千人的聲音用骯髒的話罵美國總統,但十七個小時下來,警察沒傷害任何一個人。」這是明顯的謊言。
維達爾說這些抗議者來這裡只是想進行和平的示威,但這個國家的警察暴力卻讓我們彷彿活在蘇俄政權下。
這時主持人問:「維達爾先生,抗議者在公園中舉起越共的旗子是不是一種挑釁的行為?就好像在二戰期間舉起納粹旗子?」
維達爾:「你要了解背後的政治議題。有些美國人認為美國在越南的政策是錯的,而越共想要建立起自己的國家是對的。這也是在西歐和其他許多國家的立場。如果這在芝加哥是一個新奇的主意,那就太悲傷了,但我想這就是美國民主的意義。」
巴克利突然打斷說,這裡有些人是支持納粹的。
維達爾說,就我所知,唯一支持納粹的只有你。
聽到這話,巴克利失去一貫的冷靜──他在自己的節目經常與立場不同的人如喬姆斯基、諾曼梅勒辯論,但都維持風趣機智──激動地回擊:「聽著,你這酷兒(queer),不要再叫我秘密納粹,我會把你他媽的臉打扁。」
這段話讓整個電視前觀眾都驚了,「酷兒」這字眼當時還是很歧視性的惡毒詞彙,巴克利回到自己的化妝室後,十分沮喪。那一刻,他輸掉了辯論,因為他超過了底線。
3
這個電視辯論的概念在當時仍屬新鮮,尤其是這兩人並非新聞工作者或政治學者,一開始其他媒體都取笑這個奇怪的主意。但這十場辯論吸引了全國注目,尤其最後這場粗暴的爭吵撼動了整個美國──雖然那一年最不缺的就是震撼,但從來沒人在現場電視節目看過如此血淋淋的爭執。十年後的《紐約》雜誌稱這個事件和披頭四上蘇利文秀、人類登陸月球,並列為電視史上最重要的時刻之一。
他們的爭執當然沒有在 1968 年結束。《君子》(Esquire)雜誌在次年刊出他們繼續批評彼此的文章,其言論之激烈導致兩人互相控告對方誹謗。
在那篇批評對手的文章上,維達爾還寫道:「我們都是雙性戀……同性戀是人類境況的不變事實,而不是疾病、不是罪惡、不是罪犯,雖然總是有人要把它和這三者聯結起來。同性戀和異性戀一樣自然。」
也就是在那個 1969 年,紐約發生石牆暴動,成為同志平權運動的起點。

此後,維達爾持續創作小說、劇本、政治與文化評論,尤其是一系列歷史小說更具有廣大影響,是美國最重要的作家與公共知識份子之一。巴克利持續擔任《國家評論》總編輯一直到 1990 年,在尼克森任內曾擔任駐聯合國代表,幫助雷根當選總統,一直都是保守主義的巨人。
在 2000 年 11 月的保守派《國家評論》雜誌,最後一頁竟然出現了維達爾的照片,那是 Absolut vodka 的廣告,攝影師是著名的 Annie Leibovitz。再過幾年,當巴克利在 2008 年過世時,維達爾寫下一篇惡毒的訃聞,並且說,「安息吧──在地獄」。
《君子》雜誌的傳奇主編 Harold Hayes 曾說,巴克利和維達爾的辯論可以說總結了六十年代的焦慮:「這兩個最聰明卻又最對立的人所呈現出的酸苦、極端、野心和沮喪,充分代表了美國的集體混亂。」
確實,唯有那樣一個瘋狂而激情的時代,才能產生這兩個如此迷人的人物。
他們的辯論開啟了美國大眾媒體的全新時代:因為這十場辯論為 ABC 電視台帶來很高的收視率,其他電視台開始模仿這形式,邀請不同立場的「名嘴」來辯論。然而,那些人的聲音越來越激昂,內容越來越空洞,知識與思想的論辯淪為不同黨派的立場鬥爭、言論的摔角大賽,或者名嘴們的譁眾取寵。
2004 年,美國著名的政治新聞諷刺節目主持人強史都華(Jon Stewart)在 CNN 的談話性節目「交火」(Crossfire)上,公開指責兩個主持人只是以黨派立場煽動觀眾情緒,純屬作秀。他對他們大聲說:「請停止再傷害美國」。第二年,CNN 停掉這個節目。
這當然不只是電視節目的悲哀。如今我們更來到一個社交媒體的新時代,所有的討論都更為碎片化,人們也更在「過濾泡泡」中打轉,更不要說後真相和假新聞扭曲了這世界主要的資訊來源。
於是,公共領域充斥著過度喧嘩而虛無的雜音,而越來越難聽見思想的回聲。
[1]1968 年他還訪問了傑克凱魯亞克談嬉皮,不過凱魯亞克雖然啟發了反文化,卻是一個保守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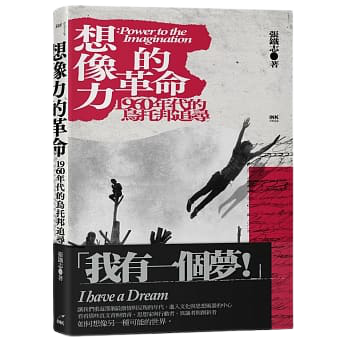
本書寫下六○時代一則則迷人的故事,或者悲傷或者亢奮或者莞爾,宛如小說的非虛構寫作,既是大時代的歷史震盪,也是個人青春追尋的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