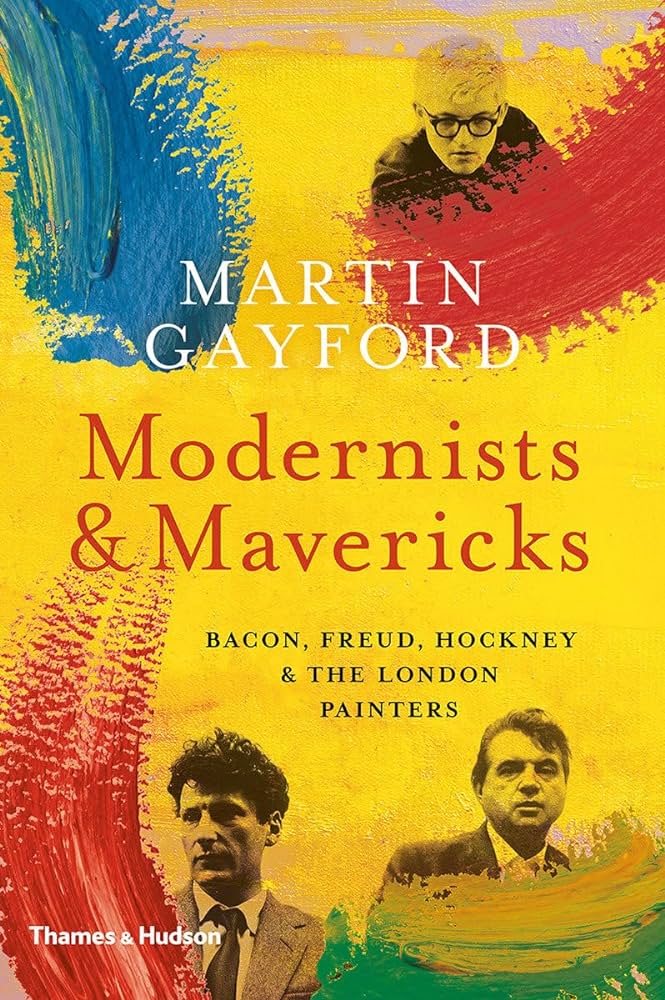第二次世界大戰落幕後,在倫敦殘破的瓦礫堆中,誕生了一批新的藝術家。經歷過戰爭的洗禮,他們胸懷一份好奇而自由的探索之心,讓戰後英國藝壇遍地開花,而其中又數法蘭西斯・培根、盧西安・弗洛伊德,以及大衛・霍克尼這三位巨匠最為人所知。三人如今雖名滿天下,但在五、六十年前抽象表現主義大行其道的歐美藝壇,他們卻是叛逆的獨行者,毫不理會所謂抽象、極簡和概念主義的「時代精神」,自顧自地創作當時為人所鄙視的具象藝術。
跳出抽象藝術的框架,用「具象」重尋自由
對培根而言,抽象藝術僅僅具有「裝飾品」的價值,與人類生命的悲劇性質完全脫節,唯有具象藝術,方能體現他最為著迷的暴力、情感與衝動等繪畫維度,並衝擊觀者的神經系統。
自 1950 年代中期起,培根一度陷入低潮,遂前往英國抽象藝術重鎮聖艾夫斯尋找靈感,他曾對抽象藝術滿懷希望,以為這種概念非常接近他「放掉控制,憑本能與機運自由作畫」的理想,但他終究還是無法欣賞不含情感訊息,只是簡單視覺存在的抽象藝術。
弗洛伊德與霍克尼雖不像培根如此直白地表達對抽象藝術的不喜,但兩人作畫的核心精神,皆以呈現個人經驗與人類心理層面為主;而當時的抽象主義已走向教條化,太過刻意地想要瓦解形體的桎梏,反而形成了另一種框架,限制了藝術家傳達生命體驗的能力。對弗洛伊德與霍克尼,以及其他渴望自由揮灑的戰後英國藝術家來說,抽象藝術顯然不是理想的載體——除了都致力於創作具象藝術之外,三位藝術家與攝影技術的關係也值得一提。
和假想敵握手言和:容納攝影的繪畫時代
攝影技術自 1839 年發明以來,便成了每一位手作藝術家不得不面對的重要課題;而培根對照片的運用,在三位藝術家之中最為積極。早期,他以親自從報章雜誌搜集而來的照片為藍本創作了不少畫作,其中包括高美館三十週年特展「瞬間-穿越繪畫與攝影之旅」(下稱「高美館特展」)所展出的《教宗習作 VI》(1961)。
這是培根自 1950 年開始,以委拉斯貴茲的畫作《英諾森十世》的攝影為靈感,歷經十數年創作的「教宗系列」中的一幅。有別於原畫的雍容華貴、氣度安閒,培根筆下的教宗面目猙獰,構圖歪斜,用色也趨於衝突陰鬱,透過對原影像的反轉與扭曲,呈現出荒謬而令人不安的詭異氛圍。有人將培根對教宗影像的複製,闡釋為對宗教與父權的反抗心理;此外,握有權柄,表情憤怒的老男人,似乎也與權威父親對幼年培根造成的創傷,以及他與具暴力傾向的飛行員彼得・拉席(Peter Lacy)的虐戀有關。但培根本人卻只提到,他之所以如此著迷於這張畫的影像,僅是因為這是一幅偉大的作品。培根著迷於暴烈的情緒與各種形式的扭曲,並著重感官性的細節——他認為,繪畫的成功關鍵,在於能挑動人們的神經並引發情緒,而非其中的內涵,因此特別不喜歡解釋自己的畫作,並稱如同他的畫,「無意義」便是人生本質。一幅畫的故事在被講述的那一刻,便淪於無趣。
泰德現代美術館《瞬間-穿越繪畫與攝影之旅》展出培根作品《教宗習作 VI》(Source: 國巨基金會)
肖像該不該相像:人像攝影帶來的啟示
1960 年代起,培根轉而請友人約翰・迪肯(John Deakin)為他拍攝各種奇異的照片,主題為他在倫敦蘇活區(Soho)所認識的人們,弗洛伊德也名列其中。高美館特展展出的《盧西安・弗洛伊德肖像習作三幅》(1965)正是培根在這個時期的作品。
早在 1950 年代,這兩位藝術家便已相知甚深。根據弗洛伊德的第二任妻子所言,有段時期,她們夫婦每日都與培根共進晚餐。從 1951 年到 1971 年,培根為弗洛伊德畫了 16 張畫像。特展展出的《盧西安・弗洛伊德肖像習作三幅》中,培根除了慣用的扭曲手法外,也將弗洛伊德的眼睛模糊處理,既似沒有聚焦,又似半睜半閉;在其中一幅裡,更讓弗洛伊德以手覆面,彷彿在遮擋畫家的視線。
培根在繪製肖像畫時,偏好於參考照片,並在人物本身不在場的情況下創作——這是因為,雖然他的每一筆都包含感情,但他認為故意去扭曲人的五官輪廓,簡直像是在「傷害他人」,是一種冒犯,而他也不喜歡畫中人物看著他在畫中扭曲他們的樣貌。而且,人物不在場時,培根創作的自由度也較大,不會被他們實際的長相所限制,畢竟他想畫出的是人物所散發的感覺,而不是其真實樣貌。以照片代替真實人物,透過將事物扭曲使其超越表象,在扭曲過程中又回歸至對表象的記錄,這樣的創作方式看似超現實,卻真切地體現了現實中人們飽受折磨的內心世界,從而達成了比照片更能反映真實的畫作。
作家 Martin Gayford 曾著有《現代主義者與獨行俠:培根、佛洛伊德、霍克尼與倫敦畫家們》(Modernists & Mavericks: Bacon, Freud, Hockney & the London Painters,中文書名為編輯暫譯)。
與培根相似,以觀察入微、下筆慎重且作畫仔細聞名的弗洛伊德,認為照片雖然寫實,但只能傳達「光線落下的方向」,而他的畫要呈現的則是更深刻的真實——包括畫中人物的情感波動、與周遭場景的關係,以及對自身和繪畫者的感覺等,照片僅是記錄「觀察結果」,弗洛伊德的畫作更進一步將觀察到的元素篩選,並以各種不同方式展現。相對於培根認為,畫中主角在身邊會使創作受到長相束縛,因而往往以照片作為參考,弗洛伊德則偏好寫生,認為人物在身邊才能自由創作,不受回憶所限,甚至選擇忽視攝影這項技術。
弗洛伊德的早期作品帶有強烈的超現實感性特質,但他本人並不喜歡這種風格,反而渴望自己的畫作具有「在現實中有可能見到」這種性質。高美館特展展出弗洛伊德的《女孩與白狗》(1951-1952),是他在轉型期間的一幅傑作,畫中人物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凱蒂・格爾曼(Kitty Garman)。第一眼看到這幅畫,必然會注意到凱蒂大得異乎尋常,比例奇特的雙眼。雖說凱蒂的眼睛的確較常人為大,但畫中尺寸顯然完全與現實不符;由此可見,弗洛伊德的目的並非畫出如照片般栩栩如生,幾可亂真的作品,而是選出一項元素(眼睛)凸顯,從而呈現出他在凱蒂身上所觀察到的焦慮與自我沈溺。
《女孩與白狗》(Source: 英國泰德美式館) © Tate
打破媒介藩籬:停駐在攝影和繪畫裡的時間
1950 年代起,弗洛伊德與培根往來,畫風明顯受到後者的影響——他逐漸受不了以往與作畫對象同行同止,近距離觀察,長時間坐著不動的繪畫模式,並希望揚棄過於精細平順的描繪方式,轉而使用更寫意、包含更多情感資訊的筆觸。若比較高美館特展展出的《抽菸的男孩》(1950-51)和《畫家的母親 IV》(1973)兩幅畫,便可發現後者明顯帶有更多凌亂大膽的漩渦狀線條,筆觸也更厚重粗礪,彷彿堆疊的血肉,不再像以往那樣平滑順暢。
作為後輩的霍克尼師從培根,在其影響之下,也喜歡以照片為作畫參考;不過在他心中,繪畫的目的並不是像照片那樣,透過固定鏡頭捕捉單一瞬間或單一角度,而是以持續運動的雙眼接收無數轉瞬即逝的畫面,並將之拼湊連結,創造更接近真實的圖片。
在「創造比照片更貼近真實的作品」這一方面,霍克尼的精神與兩位藝壇前輩非常相似。離開倫敦,抵達他眼中自由而性感的洛杉磯後,霍克尼徹底揚棄以往的概念性畫作,只畫與自己切身相關的人事物,這點與弗洛伊德一模一樣;但不同於風格灰暗,喜愛呈現不安、焦慮、憤怒與恐懼的兩位前輩,較晚出生的霍克尼不受戰爭記憶影響,用色較為明亮鮮豔,透著俏皮的玩心。此外,仍然在世的他更勇於打破素描、攝影,甚至數位繪畫等媒材藩籬,不斷拓展繪畫的可能性。
在高美館特展展出的作品《藝術家肖像(泳池與兩個人像)》(1972)中,霍克尼將兩張看似無關的相片連結起來:其中一張是個在水中游泳,因光線折射顯得有些扭曲的人;另一張則是一名男孩看向地下的照片。霍克尼透過將兩張毫無關係的照片並置,為畫作營造出奇異的氛圍;從這種手法中,似乎可以瞥見培根「教宗系列」的影子。
.JPG) 泰德現代美術館《瞬間-穿越繪畫與攝影之旅》展出霍克尼作品《藝術家肖像(泳池與兩個人像)》(Source: 國巨基金會)
泰德現代美術館《瞬間-穿越繪畫與攝影之旅》展出霍克尼作品《藝術家肖像(泳池與兩個人像)》(Source: 國巨基金會)
1960 至 70 年代,雙人物肖像是霍克尼畫作的一大主題,他常以對比強烈的方式呈現兩個人物,而這幅畫更進一步將兩人置於完全不同的背景之下——一人在水中,一人則在陸上。純以用色來看,《藝術家肖像》明亮活潑,就像霍克尼其他以「愛與歡樂」為主題的畫作,但畫中的水陸分界,卻點出此作的核心其實是「分離」,透過此種對比並置的手法,霍克尼深刻地描繪了他與戀人彼得・施萊辛格(Peter Schlesinger)分手後,揮之不去的悵惘之情。
攝影以畫面凍結了時間、表情與場景,繪畫則藉筆觸記錄時間的流動、情緒的轉化,以及人際的互動。透過欣賞培根、弗洛伊德與霍克尼三位藝壇大師的作品,並了解他們彼此人生軌跡的交錯,我們將能一窺藝術家如何透過畫筆,建構出超越表象,直抵核心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