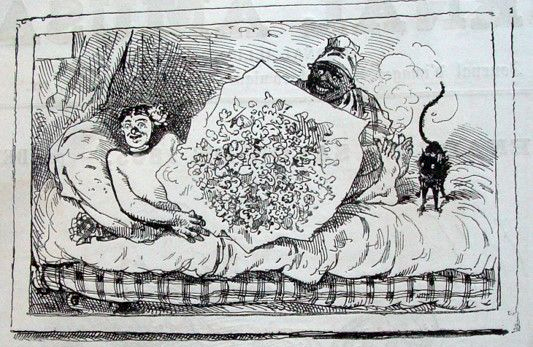在臺灣許多舞蹈教室,常用法國藝術家竇加(Edgar Degas, 1834-1917)的芭蕾舞海報或複製畫來佈置牆面。有次臺北青少年芭蕾舞團的老師和家長問我:「為什麼竇加這麼愛畫芭蕾舞?他有女友在舞團嗎?」當下我很快回答:「他沒有和芭蕾舞者交往過,也終生未婚喔,大概是因為他覺得芭蕾舞很美吧!」

藝術家熱愛某一主題,甚至其歷史定位已和所畫主題融合為一,箇中原因非三言兩語能解釋,而值得從作品和文獻好好探詢一番。竇加在幾回印象派聯展中,便以生動刻畫芭蕾舞而聞名,也成為藝術史上首位專精芭蕾舞描繪的創作者。二十世紀初,曾經有收藏家和評論者問年邁的竇加,為何努力不懈地投入芭蕾舞繪畫?
他給予兩個簡短的答案,一是:「因為芭蕾舞是現存唯一的希臘人體動作總合。」二是:「我只不過想藉由舞者,畫出美麗衣料和人體動作罷了。」[1]
古典文化的傳承
竇加提供的兩個線索,未直接談舞蹈本身,卻都指向人體動作對於他選擇題材的至關重要。
而他如此念茲在茲人體動作,是因為他深受古典美學薰陶和摯愛希臘文化之故。竇加在路易大帝中學接受古典人文教育,進入巴黎美術學校學習人體寫生,爾後赴義大利留學和探親三年,勤奮臨摹了數百幅古代和文藝復興作品。
他早年的歷史畫作《斯巴達青年運動》即呈現古希臘人崇尚健美的身體,細膩描繪斯巴達少女的體能、勇氣和魅力。竇加具備人體寫生的絕佳功底,卻身處歷史畫走下坡的時代,需要在現代生活中找到恰當的題材來發揮,而芭蕾舞讓他發現了古希臘人和現代人之間的連結。

十九世紀歐洲舞蹈家認為芭蕾起源於古希臘,因此竇加從希臘雕像和龐貝城壁畫中,追溯古典芭蕾的蹤跡,描摹優雅的律動和衣裙。[2] 在他速繪的手稿上,常圖解古典芭蕾基本舞步,註記各種術語(battement à la seconde, plié, pirouette, rond de jambe à terre),準確程度近乎舞蹈教學手冊。他亦寫了四首格律嚴謹的十四行詩,形容芭蕾舞的絕美神秘(le beau mystère)、千變萬化和繽紛色彩。[3]竇加的詩人好友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也作詩讚舞,將舞蹈譬喻為「身體的書寫」(écriture corporelle)。舞者的身體彷彿符號和媒介,在空間中創造形體和意義。
台上台下的記錄
竇加執著畫芭蕾舞,反映他所浸染的菁英教育和古典美學,也顯示他的中上階級出身與社會觀察。竇加父親為愛好藝文的銀行家,舅舅和弟弟從事跨國棉花產業,但在他初登藝壇時,家庭經濟陷入嚴重危機,使得他必須扛起謀生擔子,以致他自嘲地稱呼畫作是產品(article),供應資本市場的交易。從天之驕子轉變到自食其力的竇加,特別敏銳於現代社會的階級差異和職業百態。他犀利的畫筆,曾掃描過洗衣婦、製帽女工、妓女等勞動者。

竇加筆下的舞者並非單純回復古典風華,也不像浪漫派芭蕾畫中脫俗空靈的仙子。
在十九世紀上半葉歐洲風行芭蕾舞熱潮,著名舞星如 Clara Webster、Marie Taglioni、Fanny Cerrito 受觀眾追隨愛戴,流行畫報常見其帶著撫媚微笑、蹬著曼妙的腳尖功。
相較之下,竇加著重於舞者養成的漫長過程和辛勞訓練,而不是台上最耀眼的主角。習舞的少女多來自貧窮家庭,期待經過日日磨練和重重考驗,能靠表演領薪,貼補家計和自立維生。竇加畫出少女真實的身體動作,緊繃的肌肉,伸展的筋骨,彎曲的關節,釋放的能量,以及她們重複練習中的挫折、疲憊和恍惚。
竇加是如何了解舞蹈的幕後世界呢?
其實他沒有舞者女友,而是透過朋友和鄰居介紹,聘用幾位舞者當他的畫室模特兒。值得注意的是,他從1870 年代初畫了芭蕾舞十多年以後,才於 1883 年經收藏家幫忙而取得巴黎歌劇院會員資格,方可進入後台更衣間和排練室,就近觀察舞團的上課、評鑑、整裝、預演情景。[4]
從竇加的素描、粉彩和油畫,可見他深諳舞團建築的裡外,舊址教室的落地窗和旋轉梯,Charles Garnier 新建的華麗結構,還有舞團的靈魂人物,如 Jules Perrot 老師和伴奏的音樂家。他亦從歌劇院包廂的觀眾視角,俯瞰謝幕的璀璨剎那,在壓縮的畫面中,展現和對比休閒的富裕階級和奮力工作的舞者。

斯巴達式工作觀
芭蕾舞作為古典藝術形式,又是十九世紀巴黎中上階級喜愛觀賞的表演,堪稱視聽感官和社交儀式的盛宴。對竇加而言,芭蕾舞不只是古典的延續,或社會階級的紀錄,更啟動了現代繪畫無窮的挑戰和實驗。他長達 40 年的鑽研,從未自滿於「芭蕾舞的專業畫家」名聲,而是不斷跳脫構圖章法和技法窠臼,變換畫面的視角、配色、明暗和質地,捕捉舞者的瞬間姿態和神情。他探勘每個身體的動能、停滯、柔韌、震顫,甚至超越攝影術的洞察力,更傳神地表現人體各樣的情感、造型和韻律。

竇加的自我紀律和勤儉克己,可稱之為斯巴達式(Spartan)的價值體現。他晚年離群索居,過著斯巴達式的簡樸日子,訪客和模特兒驚嘆於他淡泊名利仍兢兢業業地工作不休。芭蕾舞閃現的詩意和流暢感,其實蘊含艱難的技巧規範和藝術表達。
這正如竇加的創作觀,看待繪畫如一連串待克服的難關,不抄捷徑,不容懈怠。[5]「為何竇加鍾愛芭蕾舞主題?」此一大哉問,可從藝術家的自述和生平習性看出端倪。竇加的古典素養和斯巴達式信念,讓他在芭蕾舞中找到相映的追求和實踐;而舞蹈的絕美神秘,引發他去貼近掌握的無盡渴望。

[1] 收藏家 Louisine Havemeyer、評論家 George Moore、畫商 Ambroise Vollard 詢問過竇加為何鍾愛畫芭蕾舞,得到這般回答。請見 Richard Kendall and Jill Devonyar, Degas and the Ballet: Picturing Movement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2011), 12, 15.
[2] 為紀念竇加逝世百年,2017 年劍橋大學 Fitzwilliam 博物館舉行 Degas: Passion for Perfection特展,將古希臘 Tanagra 舞俑和竇加臨摹的畫作一併陳列,顯示兩者的關聯性。
[3] “Danseuse”, Huit Sonnets d’Edgar Degas (Paris: La Jeune Parque, 1946).
[4] Richard Thomson, Edgar Degas: Waiting (Los Angeles: Getty Museum, 1995), 33.
[5] Paul Valéry, Degas Danse Dessin (Paris: Gallimard, 1938), 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