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英國有個來自牛津的前衛畫派,名叫前拉斐爾兄弟會。該畫派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成員米萊所作的一幅肖像畫《約翰.羅斯金》。

畫中臨風立於瀑布邊的男子,就是維多利亞時期最重要的藝術評論家,也是英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
細長的麥稈在藍色背景中律動,小小的花瓣在畫框中舞蹈,描金的蕨類植物和花朵在黑暗中閃閃發光——這種對自然風光的細緻描繪,便是羅斯金希望將萬物依照自然形態的生命能量重新歸類的理念。
米萊的這幅畫淋漓盡致地體現了羅斯金的想法,可見羅斯金對米萊的影響深遠。由此可見,雖然羅斯金本人並不是兄弟會的成員,但被認為是前拉斐爾兄弟會的靈魂導師。
同時,這幅畫代表了藝術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變──風景畫的興起。尤其是風景畫中對大自然的忠實描繪,從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靜水流深的細節中發現並且崇敬自然之美。
這種對自然的崇敬之情將繪畫變成了一項道德實踐,用羅斯金本人的話來說,風景畫是十九世紀的藝術創造,讓更正統的藝術形式:宗教、詩歌、預言,在其中殊途同歸。
羅斯金相當讚賞米萊在其成名作《奧菲利亞之死》(Ophelia ,1851-1852)中對自然的細膩描繪和宗教符號的運用,曾主動邀請他來蘇格蘭和自己一起度假。羅斯金的父親甚至聘用米萊,讓他為兒子羅斯金作畫。
米萊以蘇格蘭的山野瀑布為背景,打算為羅斯金畫一幅肖像畫,但就是在這場旅行中,米萊竟和羅斯金的妻子艾菲.格蕾(Effie Gray)墜入愛河,旅行和繪畫都不得不狼狽收場。第二年,艾菲向羅斯金提出離婚起訴,理由是「未曾圓房」。
最終,米萊是在倫敦的畫室完成了這幅《約翰.羅斯金》,日後米萊回憶說這是他「最痛苦的一次作畫經歷」。羅斯金也相當痛恨這幅肖像,後來他將畫作送給了自己的好友亨利.阿克蘭爵士(Sir Henry Acland)。阿克蘭爵士家族一直收藏此畫近百年,到 1965 年才轉賣給佳士得拍賣行。
直到 2012 年,這幅畫才進入公眾視野,由以收藏前拉斐爾派作品著名的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借展。牛津大學是充滿羅斯金和兄弟會成員們一同學習、生活的回憶,亦是他興致昂揚幻想創新藝術理念的地方。藉由這次的展出,畫中的羅斯金彷彿回到了最初的起點。

羅斯金是何許人也?
現代藝術社會學的創始人阿諾德.豪澤爾(Arnold Hauser,1892-1978)說過,羅斯金是第一位強調藝術與生活之間有所關聯的人。在羅斯金之前,藝術和生活從來沒有那麼清晰的聯繫,他認為若人們的生活條件得到改變,也會喚醒對美的感知和對藝術的認識。
羅斯金發揮他超越時空的魅力影響著後來的我們,連印度國父、聖雄甘地都曾表示羅斯金是影響他最深的三位思想家之一。[1]在從約翰內斯堡到德班的火車上,當時還在南非工作的甘地讀完了羅斯金的《致後來人》(Onto This Last),深深被其中的田園式浪漫主義打動,隨後在南非西海岸買下一片農田,希望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可以過一種更自然淳樸的生活。這也是甘地回到印度後,提倡農耕和簡樸生活的開始。
除此之外,羅斯金的個人生活也充滿傳奇。他的離婚官司在道德風氣嚴謹的維多利亞時代引起軒然大波,儘管艾菲後來嫁給了和他有師徒情誼的米萊,羅斯金依然公開支持前拉斐爾畫派。然而,羅斯金晚年曾多次精神崩潰,他因自己的社會理念得不到同代人的理解和支持,也無法改變社會現狀而痛苦不已。
推崇羅斯金的人認為他是魅力非凡的鑒賞家,亦是走在時代先列的思想者;反對他的人則認為他缺乏基本的經濟學常識,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浮於表面且不切實際,甚至充滿家長式的自以為是。但他的堅持真誠而恆久──無論他的理念是否不切實際,羅斯金費盡終生希望改變現實,他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他所屬的時代。
紳士平民
1819 年,羅斯金在倫敦出生,父母都是虔誠的福音派聖公會基督徒。父親從事雪莉酒買賣,不但能提供給家人舒適的生活,也有餘力購買和收藏藝術品,尤其是當代藝術家的水彩畫。
羅斯金在讀大學之前,都是在家自學。父親教他文學和藝術,母親則教他讀《聖經》。父母的虔誠和對當代藝術的欣賞深深影響了羅斯金日後的道德信仰和價值觀。當時浪漫主義是正在興起的新思潮,而為羅斯金的審美打下浪漫主義底色的,正是父親的生意夥伴送他的一幅印象派之父威廉.透納的風景畫。
1836 年,十七歲的羅斯金進入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學習,註冊時寫的身份是「紳士平民」(gentleman commoner)──在講究階層身份的維多利亞時代,羅斯金很明顯地並不屬於舊貴族階層。他父親是成功的生意人,能提供他良好的教育,包括文化和藝術上的品味;但畢竟是白手起家,沒有世襲的頭銜和社會地位。
然而,此時「紳士」的定義開始改變,只要原有的貴族階層稍有鬆散,城市新貴便有晉升的可能。「紳士」逐漸成為一種道德品質和社會規則,不再是僅由出身而定的頭銜,在社會中的泛化使其標準更為可及。
譬如,同時期出版的小說《簡愛》,書中的男性角色──牧師、商人、醫生、教師──都並非紳士階層出身,但他們都企圖達到紳士的教養,也以紳士自居。可以推想羅斯金很可能也有類似的生活經驗,他從父親那一輩開始,憑藉社會環境的改變和自身的努力而改變人生。

日後,羅斯金開始呼籲政府重視大眾教育和生活福利,以藝術和美啟發人們的道德和心智,這是他作為一介平民的體悟。他特別強調必須由政府出資負擔大眾的審美教育,相應地,被啟發心智的人民也會為社會帶來道德和精神上的改變,這種想法也反映了維多利亞時代紳士階層的社會責任感。
藝術的公共性
羅斯金可以說是英國第一位藝術評論家,也是他最早在英國提出藝術是一個公共問題,國家和社會層面都得重視。他認為藝術不僅局限於藝術家、鑒賞家和貴族,而是社會平等賦予每個人的文化財產。
他也認為藝術和思想的地位同等重要,譬如建築這種藝術形式就具有言語功能(talking),因為建築記錄事實、抒發情感,尤其是廟堂和公共大型建築物,如同史書般清晰地刻畫著歷史。因此在羅斯金看來,藝術家也肩負著傳教士那樣點燃大眾心智的責任。
這些想法與他在少年時代就曾多次和家人遊覽歐洲不無關係。那裡的建築風光和藝術收藏,都給羅斯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旅行也讓他深入考察歐洲的建築和藝術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差異,結合歐洲本身的興衰,逐漸思考藝術的社會意義──他認為藝術承載著一個時代、一座城市、一個國家的精神。
羅斯金對藝術的看法是他對時代進行觀察和反思的結果。就好像他反感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認為現代機械的生產使人失去了和產品之間的親密聯繫。細緻的匠人精神也被粗糙的形式、廉價材質和大量生產所取代,商人謀取暴利,工匠卻生活潦倒,他覺得這種生產和財富的分配方式會讓英國社會陷入危機。
因此他反對維多利亞時代的工業生產和商業精神,更認為維多利亞時期欣欣向榮的經濟發展是一種道德敗壞的表現,因為大家貪婪地積累財富,不惜壓榨他人,也造成了一批無法在巨大的金融鏈中獲利的人群。儘管大眾深知這種資本邏輯的陰暗面,卻不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來改變現實。
然而,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其實是以道德感強盛聞名的時代:社會宣揚禁慾、強調勤奮努力、有嚴格的行為準則、司法重罰犯罪行為、權高位重的教會對個人道德嚴格把關。尼采甚至宣稱,維多利亞時期是英國道德的起源。
羅斯金卻逆時代而行,批判為英國帶來強盛國力的工業資本主義,和被社會讚揚的嚴謹道德。不過他不是只有批評而已,他也走在時代尖端,提出類似空想社會主義的經濟理想;同時認為教會應該對這種道德的墮落負責,因為人們沒有按照《聖經》中耶穌教導的友善和淳樸方式來生活。
在維多利亞時期,中產階級也開始收藏藝術品,英國社會慢慢形成國族文化意識。羅斯金身上深深刻著那個時代的烙印,甚至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代言人。他對道德、財富、國家的看法根植於當時新起的民族自豪感,希望成就一種屬於英國的藝術形式和社會價值。羅斯金特別提倡繪畫,認為這種藝術形式能展現畫家的個性和情感,因此每一件都獨一無二,這種獨特也是大量生產的維多利亞工業時代下的救贖。
從 24 歲開始,他花了十多年時間陸續寫成五卷《現代繪畫》(Modern Painters),為不受正統派支持的浪漫主義畫家辯護──例如威廉.透納,也在《泰晤士報》中公開維護前拉斐爾兄弟會,縱使他們當時根本尚未見過面。
一般人都認為文藝復興時期是威尼斯藝術的高峰,但羅斯金不這麼覺得,他認為威尼斯是從文藝復興開始衰落的。對他而言,威尼斯強盛時是基督教建築的中心,它曾經是所有歐洲國家中最虔誠的宗教國家,但在文藝復興時期因為強烈的人文精神,雖然成了文藝復興的源泉,卻也開始褻瀆曾經虔誠的建築藝術。譬如,羅斯金覺得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總督安德烈亞.文德拉敏(Andrea Vendramin ,1476-1478)的墓碑失去了中世紀的宗教敬畏感,反而更著重於表現世俗的奇技淫巧。

(Source:Wikicommons)
對羅斯金來說,當任何紀念物表達生命的榮耀時,對死亡的恐懼也應該有一樣強烈的呈現。文藝復興時期的墓碑華美繁複,逐漸淡化了石棺本身的肅穆和沉重。現在我們通常認為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展現了人文色彩,是基於對中世紀反思的文化重生,但羅斯金認為恰恰是這種對人世的強調和癡迷,讓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偏離了對上帝的信仰。文藝復興時期是一個害怕死亡的時代,因此人們樹立許多紀念碑,紀念塵世的英明,卻遺忘上帝的雋永。
另外,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師特別講究秩序和比例,有嚴謹的構圖、體系、和比例,塑造一種理想化的協調秩序;而在羅斯金眼中,這種特定的框架將工匠變成了奴隸、機器和工具。在他的書中 [2] 特別關注 「哥德藝術的本質」,將哥德式建築和文藝復興建築對比,目的是批評後者的世俗技術性。更重要的是,羅斯金強調這種藝術是拜某一種特定的社會環境所賜,因為社會特別讚揚這種理想和精神狀態。
羅斯金在批判文藝復興和威尼斯的機械性時,很明顯地在影射他所身處的維多利亞時代英格蘭。他甚至認為這種建築和藝術形式象徵著現代工廠、現代暴政、現代災難,使得人們的靈魂萎縮,不假思索地沉入一個無法識別的深淵,被埋入一堆由編號組成的機制中,脫離了自然與上帝。如果英格蘭忘記了威尼斯的例子,那就必須透過更高尚的方式引導它。
羅斯金從兩個層面來討論藝術如何能做到這一點,或者說是藝術的兩種意義:藝術的第一種意義是自我提升個人修為。譬如歐洲繪畫之父喬托(Giotto di Bondone,約 1267-1337)的繪畫和希臘羅馬的古典神話都為現代人提供了真實的信仰和良性生活的例子,我們可以用它們檢驗自己的優缺點。
藝術的第二個意義是為了歷史的自我,也就是集體的、更大更抽象的自我。羅斯金認為高尚的藝術為偉大的歷史時代作了歸納,集中了無數高尚的情感。偉大的繪畫和偉大的詩歌等藝術,讓我們擺脫自己時代的局限,向我們揭示自己忽視的或無知的真理。它為我們帶來更廣闊的視角,我們從中可以看出自己的偏見和自滿。
繪畫、詩歌和建築對羅斯金自己的成長非常重要,他也用這些藝術形式為例來喚起讀者的同理心和想像力。
有點諷刺的是,羅斯金反感的工業技術讓維多利亞時期的交通工具變得更發達,人們更容易到達遠方,他自己亦是其中的受益者。早在 1825 年,蒸汽火車就已經可以通往歐洲和美洲,這意味著遠行不再是王公貴族的專利,家境殷實的中產階級也能負擔得起長途旅行,於是出現了一批不再滿足於將視野局限於英國本土的人。
羅斯金的父親就是其中之一,他靠做買賣發家,讓兒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而且經常帶他出國遊覽,以至於羅斯金最著名的論著《建築的七盞明燈》和後來的擴充的《威尼斯的石頭》都來自於他在歐洲旅行時的見聞和思考,探討威尼斯建築中的道德啟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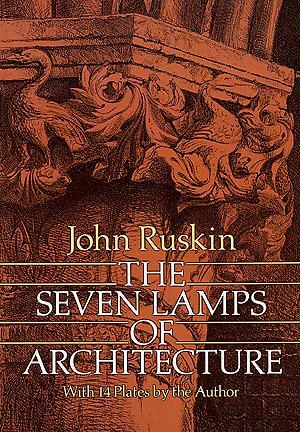
Dover Publications。
他將對歐洲的觀察擴展到全世界,相信任何國家的藝術都是該國社會和政治美德的指數。這也蘊含當時英國身為世界霸主的自信,對道德倫理和知識文化的思考都帶著四海之內皆準的普世性。不僅是義大利,他也借鑒過往的藝術創作中,希望從印度中古藝術中尋找帝國衰落的蛛絲馬跡。
「除了生命之外別無財富」
羅斯金認為藝術和道德是統一的,一個國家的道德和價值觀體現在藝術上。在寫完《現代畫家》的最後一卷後,他把這種文化批評的模式運用到社會經濟上,開始著手寫作關於政治經濟的論文,發表在著名的《玉米丘雜誌》[3](Cornhill Magazine)。但這些評論遭到太多人的反對,主編不得不中斷連載,只讓他發表了四篇。
其中最著名的句子:「除了生命之外別無財富。」他所說的生命包括愛的力量、快樂的力量、敬慕的力量。一個國家裡快樂的人越多,這個國家就越富有;一個人在充分發揮自身作用的同時,對別人的生存越能產生有益的影響,也就越富有。總而言之,國家的經濟是要讓人盡可能快樂高尚地生活。
他對財富、對社會的理解成為《致後來人》的基礎之一,並以這種有機的「生命財富論」駁斥當時享有盛名的經濟學家,包括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藉以強調他反對機械性的、純粹功用和效益主義式的認識。
「生命之外別無財富」,因為資本(capital)這個詞本意為「事物的頭部、源頭、根部」,只有產生與自身不盡相同的事物,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有生命的資本,而不是僵化的東西。
儘管此時的他因為對教會失望,已經放棄了基督教信仰,他的話語還是帶有宗教色彩,書名也源自詹姆士王欽定的《聖經.新約》中的〈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十四節。此章節以葡萄園為喻,討論天國裡的公平待遇和賞賜,多時作工的沒有餘,少時作工的也沒有缺,因為上帝從不虧待人:
「拿你的走吧!我給那後來的和給你一樣,這是我願意的」(I willgive unto this last, even as unto thee)。
從討論藝術的社會道德意義開始,羅斯金一直強調要依照《聖經》的教導生活,這裡也以經文中的譬喻,告訴大家造物主本來就沒想讓人的行為受到權宜之計的支配,反而要接受正義制衡(balances of expediency)。
他所說的「正義制衡」,意指包括情感在內的正義,而那種情感即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愛。僱主與工人之間的一切合法關係以及各自的最大利益,最終都取決於「正義制衡」。同時,他也以此提醒他的同輩人,無論是維多利亞中產還是教會,真正的道德不在既有秩序下的經濟、慈善、司法,而在於真正按照《聖經》中的平等、質樸的方式去生活。
對他而言,上帝給了世人足夠的眷顧,沒有必要過度追求奢華和財富。羅斯金在工業革命如火如荼的1860 年代,以此譬喻作為他的經濟理念基礎,和他嚮往哥德藝術的古典藝術觀異曲同工。
羅斯金對改變既有政治經濟模式的具體構想,是自上而下,從國家層面建立機制性的保障,同時也是家長式和父權式的。他認為國家有責任對國民進行義務教育,不僅在於讀寫,還包括教導孩子如何過一種有意義的生活,告訴成人如何選擇和實踐對社會有價值的工作,如何欣賞、熱愛和保護自然,如何做出有倫理道德的決定。
身為僱工管理者的商人或工廠主也被賦予了為人父母般的權威和責任。羅斯金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進入商業機構的青年已完全脫離家庭的影響,於是他的僱主就必須承擔父親的角色。
僱主的權威,以及其經營活動的總體氛圍,再加上與年輕人一起工作的同事,這些都比家庭的影響更直接、更有壓力,並常常決定了他是善是惡。如此一來,僱主若想要公正對待自己的僱工,唯一的途徑就是嚴格審視自己是否在必要的情況下將他們視如己出。
這種家長式的視角在羅斯金的政治經濟和藝術社會觀中,都是非常重要且具爭議性的論點,很多人認為它剝奪了工匠和藝術家的職業自主權。在他的日記中有不少關於社會改革的虛擬對話,其中他本人是田園牧歌的締造者和管理者,和他對話是被教導的勞動階層孩子。換言之,在羅斯金的理想藍圖中,窮人並不能得到真正的權利和自決,而是需要被「家長」管理、教育和看顧的人,這也是他常受人詬病的地方。
雖然羅斯金地許多理念看似守舊,但他也有開明進步的地方,譬如他贊成男女同等教育,並且捐款給在倫敦和愛爾蘭的女子學院。
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可以說,羅斯金當時的想法已經初現社會主義的影子,儘管他並沒有公開加入社會主義黨,但他曾在由基督教社會主義建的倫敦工人學院(Working Men’s College)教書,每個月寫一封《給英國工人的信》(Fors Clavigera)。
然而諷刺的是,羅斯金在繼承父親的遺產後,依舊靠著雪莉酒生意過日子;也就是說,他一邊享受著資本主義的既得利益,一邊呼籲僱員參與激烈的社會改革。
晚年的羅斯金飽受憂鬱症的折磨,他在自傳中寫道:「醫生認為我是過勞成疾,但我發瘋的原因是因為我的工作沒有任何成果。如果大家知道我的作品得到何種待遇,就會明白我的痛苦了。我花七年的時間寫一本書,燃盡生命之火,出版後卻沒人相信裡面的話。」
他最雋永流傳的作品《建築的七盞明燈》,被他自己認為一無是處,這本書的第一版裡被基督教會規範的道德感,雖然他有虔誠的信仰,但對教會卻是充滿著矛盾的心情。放棄基督教信仰後的他很難得到周圍人的理解,包括他苦苦求愛十多年的夢中情人──1858 年,40 歲的羅斯金愛上了少女羅薩(Rose La Touche, 1848-1875),但羅薩無法認同他的宗教信仰。

1875 年,27 歲的羅薩發瘋而死,56 歲的羅斯金失去了追求十六年的愛人;而歐洲依然在摧毀古建築和古藝術,他也無法從工業革命手中拯救他熱愛的大自然。總總原因,使他痛苦不堪。
除了他的自傳《過去》(Praeterita)之外,羅斯金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作品是《英格蘭的愉悅之處》(Pleasures of England),這是他作為藝術史學者在牛津講課的演講錄,似乎概況了他畢生的心血。這位赤誠的維多利亞愛國者,帶著家長式的責任感,一心希望帶領社會改變,卻無法在有生之年收穫成果和知己。
也許羅斯金本人並不以為意,但事實上他的著作《現代畫家》直接地影響了前拉斐爾兄弟會的成員們,使他們將對自然的細緻描繪和象徵主義結合起來。前拉斐爾派的創始人亨特說,羅斯金的《現代畫家》解決了一個困擾英國藝術的大問題──仰賴過時的繪畫習俗,缺乏有效的繪畫符號,風格和技巧上都較薄弱。
維多利亞繪畫需要新的圖像學(iconology),替代不再對時代有意義的過時符號和象徵。羅斯金鼓勵年輕人挑戰繪畫習慣,嘗試融合宗教和文化符號的現實主義,賦予繪畫另一層深意,就好像十九世紀的象徵主義或中世紀藝術。而通過前拉斐爾派的藝術實踐,羅斯金也實現了他的理想──為英格蘭同胞指出了屬於英國的藝術價值和藝術話語。
如同二十世紀最著名的法漢翻譯家傅雷曾在家信中寫道:「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獨的。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創造許多心靈的朋友,你永遠不要害怕孤獨,你孤獨了才會去創造,去體會,這才是最有價值的。」
羅斯金在世時,這樣的話也許並沒有給他帶來安慰。但他孜孜不倦地結合社會現實的創作,為藝術史留下了更寬廣的世界,和以他命名的藝術學院同樣雋永。哪怕不斷有質疑和反對,也展示著這個精神世界的生命力,而這與社會同呼吸的生命力,正是他對藝術史的貢獻。

[1]另外兩名是古埃及學者亨利.梭特和俄羅斯作家列奧.托爾斯泰。
[2] 《建築的七盞明燈》(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和《威尼斯的石頭》(The Stones of Venice)。
[3] 《玉米丘》是維多利亞時期極有影響力的媒體,托馬斯.哈代的代表作《遠離塵囂》(Far from the Maddening Crowd)和柯南.道爾的不少小說都初印於這份雜誌,甚至維多利亞女皇本人都在《玉米丘》上發表過隨筆文章,可見羅斯金作為藝術評論家的地位。



:作家、插畫家、旅行家,三位女性與波斯詩集的故事29.jpg)
:漫遊奇境,跨越-150-年的經典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