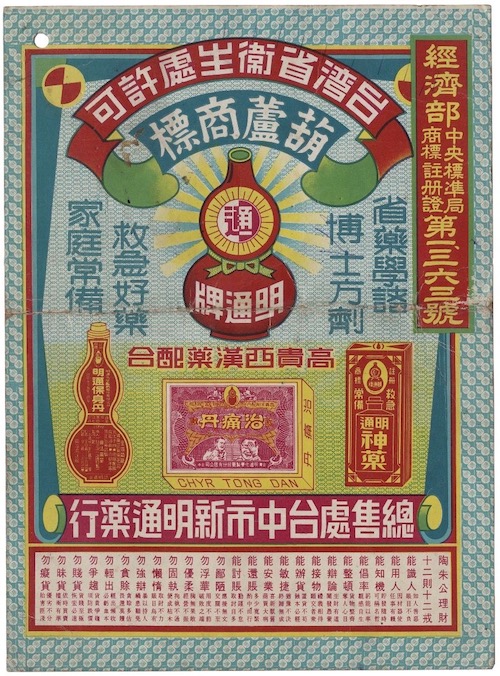「卡巴迪」是一項觸碰性的競賽運動,源於南亞地區,跟許多運動一樣,於十九世紀以來,經歷「現代化」的過程,使一項原本在不同地區、且規則各異的運動,變成一項規範性的運動。
在 80 年代,卡巴迪從印度輸出到世界各地,於 1990 年成為亞運會正式比賽項目,於 2006 年的卡達杜哈亞運,有印度商人看準這項運動的發展潛力,把它商業化,於 2014 年成立職業聯賽,名為 Pro Kabaddi League (PKL),廣受歡迎,至今成為板球後,印度收視率第二高的職業聯賽。
2006 年的杜哈亞運,除了吸引了印度商人外,也吸引了一位熱愛運動的臺灣商人黃忠仁先生。在他回到臺灣以後,成立中華民國卡巴迪運動協會(2008 年 1 月) ,在他推動之下,卡巴迪運動協會在兩年之內得到國際認同,2009 年 10 月正式加入成為國際暨亞洲卡巴迪總會的會員之一,參與國際賽事。
在臺灣,卡巴迪也發展迅速,至今,已有 6 個縣市成立卡巴迪委員會,並有 12 個大學團體、17 間高中、和 12 間國中曾參與卡巴迪賽事,遍佈全國。縱然如此,卡巴迪在臺灣仍屬小眾運動,認識的人不多,而卡巴迪運動員的故事更鮮為人知。
「本土」訓練
「2008 年我第一次參加卡巴迪亞青盃,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卡巴迪,教練只給了我們一隻 DVD,內容是杜哈亞運的卡巴迪比賽片段,然後,便叫我們從中學習……我們的同組對手是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和伊朗,結果,我們分別大敗 60:3、40:20 及 80:20……賽事結束後,一些隊友決定放棄這個運動,但我對自己說,從那裡倒下,便從那裡站起來,之後,我就自己不斷看片,研究卡巴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威暘是臺灣第一代的卡巴迪選手,2017 年 6 月,我跟隨他到花蓮,參與當地一間中學所舉辦的卡巴迪訓練營,在回程到臺北的路上,他跟我分享他的卡巴迪歷程。

他說,不同地方發展卡巴迪有不同模式,如日本,他們每一至兩年便會到印度卡爾各答進行集訓,增進技術,相比之下,臺灣的發展則較為「本土」,既沒有出外集訓,也沒有從南亞請教練過來指導,一切只從影片和書本中學習。
威暘說,起初訓練方面相當困難,但後來隨著網路的普及,網路上能找到更多的資料和影片,這大大改進他們的技術,同時,這樣的發展模式之下,避免了「教練一言堂」的文化。佳銘和威暘同屬臺北市立大學卡巴迪隊的隊員,佳銘是隊伍的前隊長,他跟我解釋他們的訓練模式:
「臺灣沒有專業的卡巴迪教練,當我們練習的時候,我們每人會輪流擔當教練的角色,首先觀察自己隊伍的強弱之處,然後自己上網找資料,作出針對性的訓練。」
過去有很多文獻討論臺灣國民政府如何透過體育運動貫輸「儒家文化」,桎梏臺灣的體育發展(例:Chiang et al. 2015; Yu and Bairner 2011),但從臺灣卡巴迪的例子來看,訓練模式以運動員為中心 (player-centered approach),每個成員都需要徹頭徹尾的參與,這使大部份的運動員除了善於作賽外,也善於觀察、帶領、教導和分析賽事,給運動員一個較全面的發展。
時不予臺灣
2014 年,威暘有機會到印度參與 PKL 的賽事,共參與了第一季和第三季的賽事,另一位卡巴迪運動員佳偉,於 2016 年也參與了 PKL,並參與了第三季和第四季的賽事。隨著這些國際賽的經驗增加,臺灣卡巴迪隊的實力也得到提昇,但男子隊苦無機會走上國際舞台,威暘告訴我:
「2008 年,我們全沒準備之下參與國際性比賽,結果慘敗收場……現今,我們準備就緒,卻沒有機會一展身手……」


當威暘跟我分享這番話時,正值臺灣剛剛跟巴拿馬斷交,媒體上也討論著臺灣被孤立的狀況,在國際體壇上,同樣地,臺灣常處於一個被動的位置。以代表隊稱號來說,他們不能以「中華民國」或「臺灣」參與國際賽事,只能以「中華臺北」,2008 年北京奧運,甚至被主辦國建議稱為「中國臺北」(Bairner and Hwang 2010),在種種原因之下,很多運動員都會覺得臺灣在國際體壇上常站在一個較邊緣的位置。
事實上,2016年10月,印度舉辦卡巴迪世界盃,亞洲受邀參與的隊伍只有日本、南韓、泰國和孟加拉,臺灣不在名單之上,而整個賽事共有 12 隊參與,當我跟很多臺灣卡巴迪運動員交流的時候,他們也同意如果臺灣能參賽,以他們的實力,很大機會能打入準決賽,問鼎前四。

「卡巴迪是……」
佳偉是另一名資深的卡巴迪成員,當我問到他對臺灣的卡巴迪發展有什麼期望,他顯得一臉無奈:
「卡巴迪的一個特色就是你從來不知道何時會有國際賽事,以其他運動來說,它們的亞洲錦標賽或世界盃都會有一個固定的時間表,但卡巴迪就很難說……」
卡巴迪的國際比賽主要是由國際卡巴迪總會負責,然而,印度在總會有很大的影響力,常帶來一些不穩定因素。2017 年 3 月,我第一次探訪臺灣卡巴迪成員,那時他們正為幾個月後在伊朗舉辦的亞洲錦標賽作密集訓練,而在 4 月的時候,賽事宣佈取消,對運動員來說,臨時取消賽事,理應感到非常失望,但對臺灣卡巴迪運動員來說,他們說是司空見慣,因這並非第一次。
在這樣苦無機會參與國際賽事的情形下,驅使我很想知道他們何以有動力繼續參與這個運動。
2017 年 6 月,我有機會跟威暘和他的弟弟謹韓到新竹探訪玄奘大學的卡巴迪隊伍,這卡巴迪隊伍是第一隊能以非體保生為骨幹成員而奪全國冠軍的隊伍,訓練過後,我們一起到快炒店,喝啤酒,吃小菜,晚宴中,大家笑聲不斷,主題圍繞著 2013 年一起參與亞青培訓隊的訓練經過,謹韓憶述說:
「那時天氣很炎熱,訓練要跑很長的路程,共 10 公里……我們每天早上也期盼雨天來臨,取消訓練……有一次在賽道上,隱約看見賽道旁的樹林有一隻很大的狗……」謹韓比劃著那隻狗,大概有他的身驅這麼大,同桌的也紛紛點頭,笑著和應。「我不斷叫其他隊友,不要望,不要望,繼續跑,繼續跑……」
那次集訓,他們過著同樣的生活節奏,一起的增重、一起的鍛鍊肌肉和體能,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最終亞青錦標賽也告取消。

卡巴迪在臺灣十年間從無到有,運動員從充滿希望到失望,最後學習處之泰然。過程中,運動員不單學習了卡巴迪的技術,也建立了同樣的生活節奏和生命脈搏。
於花蓮的訓練營當中,有機會跟幾位高中女運動員訪談,問她們何以參加卡巴迪,其中一位說:「為國爭光!」其他成員立即討論:「臺灣是國家嗎?」「不這樣說,該怎麼說?」然而有一位運動員說:「我希望為我的高中帶來一點回憶。」
人類學過去的研究經常指出,「親屬關係」(kinship)並非建立於血緣關係之上,而是建立於生活節奏和情感分享,卡巴迪在臺灣的特殊處景,使運動員有著同樣的生活節奏和生命脈搏,大家情同手足。
玄奘大學的卡巴迪隊伍,於 2016 年奪得全國冠軍後,寫了一份名為「不斷失敗,不斷前進:我們的卡巴迪冠軍夢」的報告書,報告最後部份是運動員的個人分享,其中一位說:
「卡巴迪是一個讓人覺得很可怕的運動,但實際上我不那麼認為,因為這個運動讓我清楚了解到一旦牽了夥伴的手就放不開的一種又愛又恨的運動……」
防守的時候,卡巴迪運動員需要手握著隊友的手腕,並一起捉拿進攻者,於我觀察,這種相連,對臺灣卡巴迪運動員來說,實在不只肢體上,更多是生活上和生命上的相連。

備註:如欲了解更多臺灣的卡巴迪運動,可留意 2017 年 10 月臺灣的全國運 動會,這是卡巴迪第一次成為全運會的正式項目。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參考文獻:
- Bairner, Alan, and Dong-Jhy Hwang. 2010. “Representing Taiwan: International Sport,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46(3)231-248.
- Chiang, Ying, Alan Bairner, Dong-Jhy Hwang, and Tzu-husan Chen. 2015. “Multiple Margins: Sport, Gender and Nationalism in Taiwa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Science 4(1)19-33.
- Yu, J.W. and Alan Bairner. 2011. “The Confucian Legac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European Physical Education Review 17(2):219-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