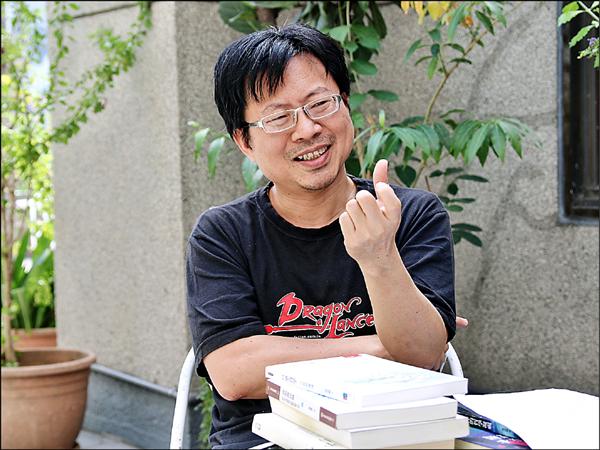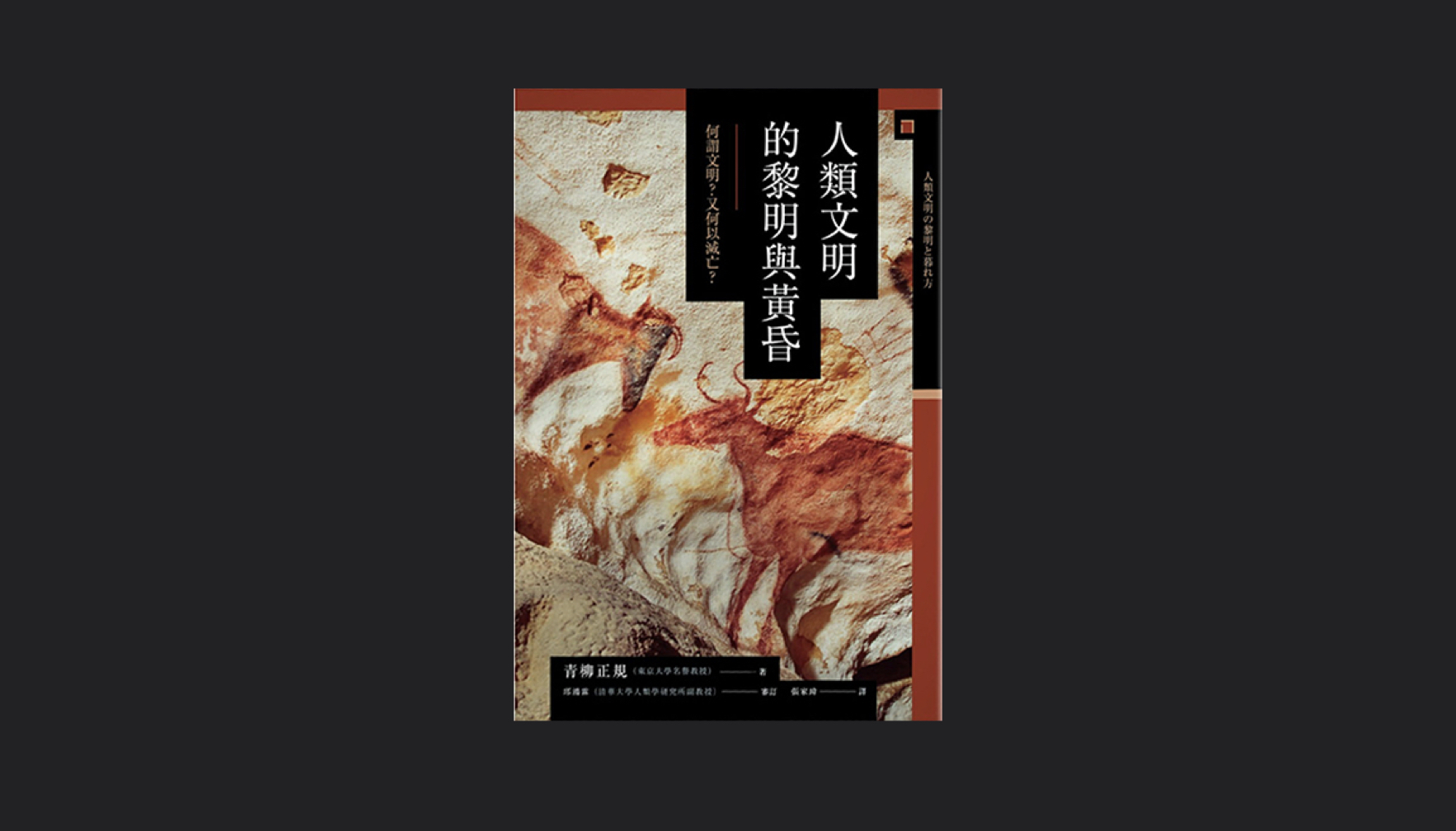「他是要出來嗎?還是要進去呢?」:淺談臺灣研究的窘境
身為一個在外文系所苦蹲了六年的學生,筆者除了被學術領域的朋友半強迫地凹去翻譯英文文章,或是解決文法難題以外,最常被問到的基本題不外乎:「所以你們都用英文寫論文嗎?」;以及接之而來的:「那你們的研究要怎麼跟臺灣觀眾溝通啊?」誠然,在臺灣以英文書寫的尷尬,是外文系所師生長久以來皆默然以對的矛盾[1]。讓我們冒著在以外文書籍推砌而成的象牙塔裡自說自話的風險的,是第一手接觸以美國學術圈為首的「西方」知識的窘迫,以及在全球化時代下以「國際」為名進行英文學術交流的渴望。
還記得,筆者在大學部時期嘗以中文初試筆墨,在不同的網路平台投書撰稿,為的就是自己對「溝通」的焦慮感。然而,或許是耳濡目染師長的作風,彼時特別喜歡大量引用「西方」的高深理論,套用至臺灣的個案,並且在專有名詞後面加上括弧與英文註解,彷彿那括弧是個帶有權威的飛地、一個異空間,在一片熟悉的語言中給人一種陌生而吸引人的感受。
當然,自以為是的註解非但達不到翻譯理論的效果,還會引來他人對這種中二傲氣的訕笑[2]。為了解決這種兩難,我們是否應該全然的放棄「進口」外來知識或理論呢?還是選擇以打入英美的學術場域為目標,一概放棄回到臺灣?筆者曾這麼詢問自己。
這本由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合編,今年(2016)甫出版的《知識臺灣:臺灣理論的可能性》,正是以更為宏觀的角度,來看待前述的一個年輕臺灣研究生所面臨的人生難題。近十數年來,由於政治與社會環境持續變化,尤其是廣義臺灣主體性的想法普遍落實於大眾意識中,海內外的臺灣研究社群不斷試圖脫離中國研究的影響而自立,在危機感十足的狀況下,詢問臺灣研究的實質內涵以及可能的發展方向[3]。
可喜的是,根基於臺灣內部的學術社群,近年來學術本土化的努力甚豐,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各領域幾乎皆有考察臺灣本土經驗得之的學術研究成果[4],其中當然不乏綜合「西方」與「本地」理論知識者。然而,本土知識的考掘,似乎尚不足以消解對於本土理論的需求焦慮,一種將特定情境抽象化至可供參考乃至引述的企圖。這與筆者前述的簡單矛盾似乎有相似之處:「難道我們只能『進口』理論來解釋本土現象嗎?還是我們最終也可以『出口』理論呢?」《知識臺灣》一書,似乎正是以回應這樣的問題作為出發點。
不要再「已讀不回」:臺灣的知識、社群,與理論權力
讀者可能質問:既然本土知識已有所建樹,那又何須本土理論?追求理論是否只是模仿「西方」學術領域的動作?而理論又究竟是什麼?與一般的知識形構有何不同?
《知識臺灣》一書的編者們顯然考慮到了這樣的問題,因此以陳瑞麟帶有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色彩的分析論文〈可以有臺灣理論嗎?如何可能?〉作為適切的開卷之作。帶有跨領域視野的陳瑞麟,首先論證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的變動性,與自然科學的普遍性(universality)大不相同,也因此不同的研究範圍內所歸結出的理論,往往難以輕易橫跨疆界去有效地解釋現象;正因如此,陳認為建構一套後設式的「理論的理論」有其必要性,藉此觀察不同理論的異同屬性以「提供我們建構新理論的參考」。
在陳瑞麟的觀察中,所有理論都具有:模型、概念架構、論題、版本家族,只是這些框架下的內容可能因研究對象而有所不同。若是我們接受陳瑞麟的假設,則認為理論的建構只是模仿「西方」學界的批評就失去效力了,因為不論什麼樣的知識形構,都可被視為某種程度的理論化。回到臺灣,陳瑞麟並未因為其「理論的理論」的普遍性而忽略臺灣的特殊性;反之,他強調「臺灣學的研究社群是臺灣學的必要條件,臺灣歷史經驗與脈絡下的臺灣現象是臺灣學的充分條件」。換句話說,臺灣理論知識的建構,所需要的不只是對源自於臺灣的現象的研究,而更必須是來自一個對彼此有所互動與回應的跨領域學術社群。
同樣地,讀者可能再次質問:許多臺灣在地的學術社群早已有頻繁的互動與產出,何須以「臺灣」之名,再度將不同脈絡的研究者整合,並試圖產出以「理論」為名的知識?
對此,陳瑞麟首先提出理論本身帶有的「跨脈絡性」,來作為一種增加臺灣知識的影響力的方法:「理論都是區域性和脈絡性的,但它們都可以被跨區域、跨脈絡地「投射」到不同的區域和脈絡上,換言之,理論也同時具有『跨脈絡性』(cross-contextuality)和『可投射性』(projectibility)」[5],並且進一步認為掌握臺灣理論的重要性便是可以取得「理論權力」(theoretical power),使臺灣研究學群在「面對歐美擁有強大『理論權力』和競爭力的理論版本家族時」,不至於「失去『抽象』、『概念化』、『結構』、『跨脈絡投射』等理論權力的掌握」。
雖然這本龐雜的論文集並未詳細說明其編排邏輯,綜論的部分亦只有開頭短短幾頁的介紹與結尾的學群宣言(可視為呼應陳瑞麟對建構學術社群的呼籲的實際作為),但以陳瑞麟的文章作為開端,其實已經從相當有效的理論層次回答了可能的質問。
不過,陳文較為抽象的觀點所難以回應的,便是臺灣學術圈許多實然的困境,包括如何面對「西方」理論的殖民問題、本地學術圈彼此「已讀不回」的困境,以及造成這一連串問題的歷史過程。這或許正是為何接下來史書美與湯志傑兩篇概論式的文章,各自選擇以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後殖民角度來耙梳學術社群中的實際困境的原因。本文因篇幅關係,只以史書美的文章作為範例討論。
(作者為臺大外文所碩士生)
[1] 筆者在此討論的只是常見的情形,並不是要忽略諸多外文系所學者在臺灣所進行的中文翻譯與學術工作的努力;事實上,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所舉辦的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便是以中文進行發表。當然,中英夾雜造溝通問題的困難也不是只有外文系才面臨的情況,只是筆者認為在比例上,外文系乃面對此問題的一大要角而已。
[2] 在最近出版的書籍中,《賤民解放區2014-2015:318佔領運動以及其後》即見作者群們對括弧中英文註解的習慣的嘲諷,其在不重要的慣用詞語之後加上英文(如「非常」(very))可謂對西方知識的引進提出質疑的一種手法。另外,史書美在《知識臺灣》中則是提出以「諧音雙關翻譯理論」的方式來消解這種尷尬,使得臺灣的思考方式可以與「西方」知識混雜。實際的作法可見諸於由其所主導的數屆「臺灣理論關鍵詞工作坊」。
[3] 在歐洲臺灣研究學會的簡介中提到,臺灣面臨的難題並非是沒有足夠的注目,而是由於「一連串意識形態的集合將對臺灣的研究緊緊地與中國文化與文明綁在一起」(筆者自譯;此後若無註明,外文資料皆為筆者自譯)。而《知識臺灣》一書編者史書美更是早在 2003 年即批評在北美「研究臺灣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臺灣對於北美學者來說「太小、太邊緣、太模糊,也因此太不重要」〔“Globalisation and the (In)Significance of Taiwan,” Postcolonial Studies 6, no. 2 (2003): 144〕。近幾年,雖然臺灣研究已在部分歐美大學有一足之地,但學者們也開始對臺灣研究的整合性提出憂慮,可參見李宜澤於「芭樂人類學」的〈北美的臺灣在哪裡?記二十年的「北美臺灣研究學會」〉一文中記錄蘇利文(Jonathan Sullivan)提到:「與其說臺灣研究被邊緣化,不如說臺灣研究處於碎裂化的狀態」。這似乎也預示了臺灣研究的跨領域走向,如今年的北美臺灣研究年會便以「跨」(Trans)為題(亦可參考《跨界跨代的臺灣研究:北美臺灣研究學會(NATSA)二十年》一書)。對於跨學科的討論,筆者亦會在本文文末稍微著墨。
[4] 諸如社會學為根底的《帝國邊緣:臺灣現代性的考察》、歷史社會學的《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哲學史考察的《存在交涉:日治時期的臺灣哲學》、文學的《臺灣研究新視界:青年學者觀點》,乃至於「說書 Speaking of Books」已有評論的半宣言式《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見:「臺灣的西西弗斯之途──讀《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等等,更不必提諸多臺灣歷史文化研究相關叢書。
[5] 陳瑞麟所提出的比較企圖,事實上與其他臺灣研究學者不謀而合。梅豪方(Frank Muyard)即在Comparatizing Taiwan一書中批評,「在臺灣,我們只能夠找到極少聚焦在比較方法或正在發展比較研究的中心、機構,或研究團體,若是有這些團體的存在的話;而且,少有研究使用比較的方法來探索臺灣的歷史社會形構或導致這些形構的主要過程。大多數的研究仍舊只為了這些歷史社會發展與過程本身而關懷他們,而不是為了他們如何可能被連結到世界性的現象,以及他們能夠告訴我們與其他國家比較後,他們在臺灣的特殊性與共通性」(頁 15)。而如前述,北美臺灣研究年會今年也以「跨」(Trans)為題,呼籲將臺灣置入比較性框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