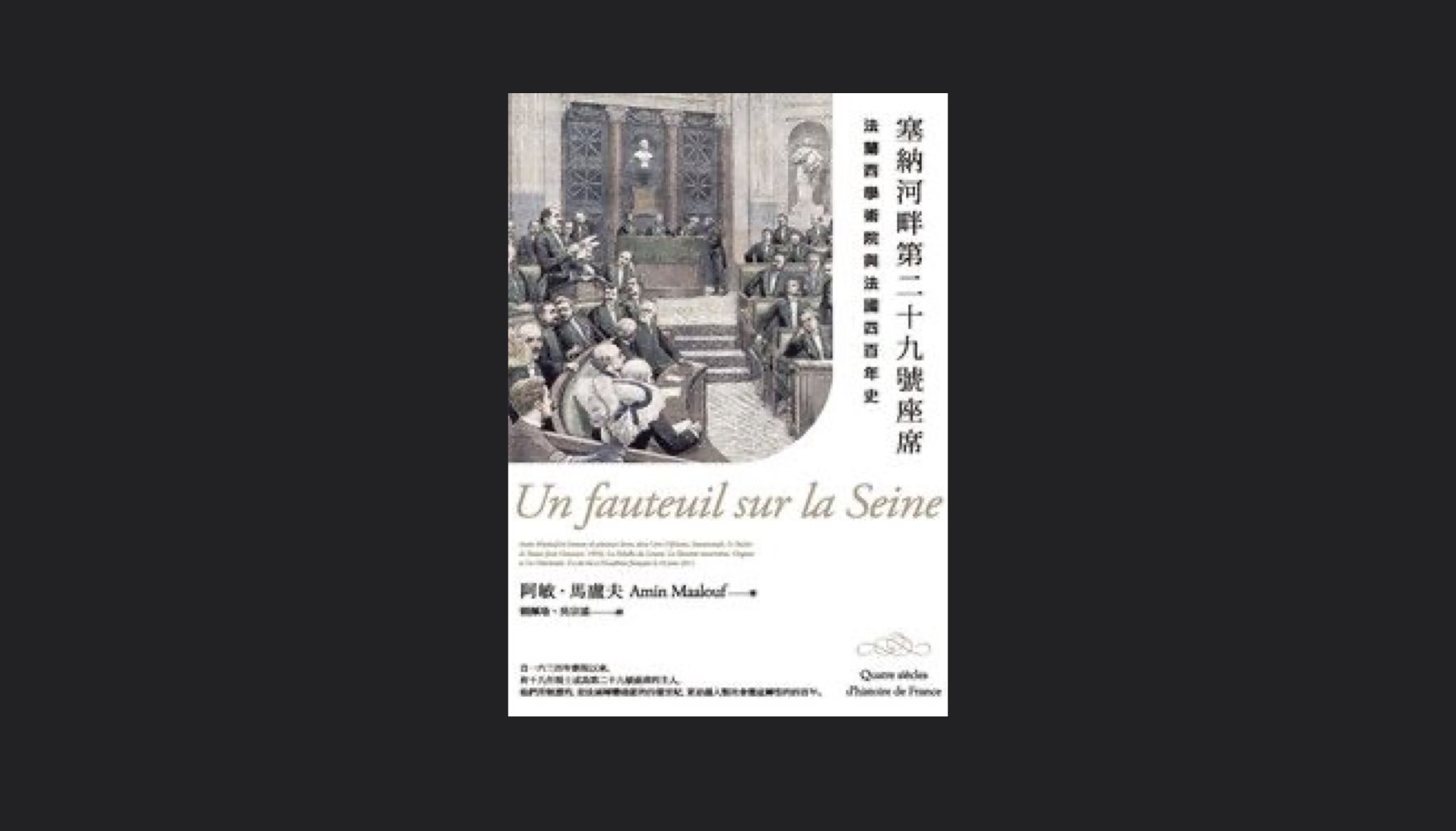分裂的國度:極端年代下的兩個法國
一九一四年,全面戰爭籠罩法國,這是極端年代的第一個徵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高漲的民族情結與國家全面動員的體制,迫使法國人不得不暫時團結對外。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約》在巴黎和會上簽訂,終結了這場長達四年餘的歐陸大戰。表面上看來,法國人在付出了慘烈的代價後獲得了勝利,一躍成為歐陸最強的國家,而鐵血獨裁的德意志帝國則在戰後土崩瓦解,這彷彿證明了法蘭西的民主共和路線正確。
有那麼一段時間,法國看起來似乎可以掙脫戰爭的陰霾。人們欣喜和平的到來,巴黎則重拾往日歐洲文化之都的光輝。然而,在光鮮亮麗的表象底下,卻潛伏著許多令人憂心的危機。
這場大戰將法國推向了崩潰的邊緣。它摧毀了法國近三分之一的家園與最精華的北部地區,更奪走了法國十分之一的總人口數。若按人口比計算,法國是損失最慘重的歐陸列強,有超過一百三十萬名法國人失去了性命。法國在戰爭中損失了一整個年輕世代的勞動力與生產力,惡化了原本就在戰爭中背負了難以計數債務的法國經濟狀況。
任何在世界大戰後關注法國新聞的人都會發現,法國政府正用前所未有的速度更迭:光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二五年這短短一年間,就連續換了七屆內閣。然而,無論是哪一黨派上臺,都無法解決日益嚴重的財政問題。
比經濟危機更嚴峻的挑戰,則是法國那低迷的生育率。
早在世界大戰爆發前,法國的生育率就已敬陪末座。在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一年這段時間,法國人口總共只增長了八.六%,而同一時間英國與德國的成長率則分別是五十四%與六十%。
法國政治人物競相將低生育率列為國安問題,但對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卻莫衷一是。保守主義者將問題歸咎於家庭傳統的破壞,他們祭出的手段是提高對墮胎的懲罰,然而成效卻十分有限;激進左派則試圖透過賦予育有子女的婦女投票權來鼓勵生育,但這個提案最終隨著婦女參政權一起胎死腹中。共和制度的擁護者們擔心,開放婦女投票權,會讓傳統上對婦女有較多影響力的天主教會得到更多選票,進而危及好不容易確立的共和體制。
經濟與人口的消長嚴重衝擊法國保守派的榮譽感,他們開始感到法國不再像過去一樣強大,日子似乎也不如過去般「美好」了。
這種相對剝奪感表現在各個層面上。在路易十四的年代,每五個歐洲人中就有一個法國人,且法國握有歐洲三分之一的財富,而在一九三○年代,只有不到十二分之一的歐洲人是法國人,且法國的財富已縮水到占全歐洲的八分之一不到。在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首次將英語與法語並列後,法國人也開始意識到,法語正逐漸失去歐洲主流語言的地位。
有愈來愈多的人開始質疑共和國與議會制度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種不滿的聲浪,很快就在隨後的經濟大恐慌中進一步激化,成為孕育極端意識形態的溫床。
極端意識形態的對立,則是極端年代下的第二個徵候。
一九三一年,早已襲捲全球的經濟大恐慌降臨法國。由於法國遲遲不願放棄其金本位制度,使得經濟大恐慌在法國影響的時間遠比英、德等國來得長。經濟衝擊再次反映在政府的更迭頻率上:在接下來的一年半時間,內閣又有如洗牌般地連換五屆,且每次政黨輪替、就會爆發許多金融醜聞。
戴高樂日後在回憶一九三○年代的法國政府時,如此感嘆道:
當人民開始對自己國家的民主體制失去信心,他們往往會往外找威權國家作效仿的模範。極左與極右派的支持者們,很快就在共產蘇聯與納粹德國找到了各自的楷模。
經濟蕭條刺激社會運動,也刺激著勞工階級階級觀的形成,法國共產黨與工運團體發起罷工,溫和者試圖替勞工爭取更多的權益,激進者則試圖在共產蘇聯的指導下,加速無產階級革命的進程。
在這樣的氛圍刺激下,部分的保守右派團體終於按捺不住。他們認為當前的政府對左派太過軟弱,而黨派林立的議會制度所導致的低效率與政府更迭,更是他們眼中必須矯正的「亂象」。這些團體於是效法墨索里尼的黑衫軍與希特勒的衝鋒隊,訴諸街頭武裝鬥爭的路線。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以極右翼團體愛國青年團(Jeunesses Patriotes)為首,上萬名示威者聚集在巴黎協和廣場,矢志「消滅共產主義」與「導正錯誤百出的國會」。他們試圖衝進國會,並與反對者和巴黎警方爆發激烈衝突。準備不夠充分的警方,在群眾的棍棒和石塊攻勢下被突破。
總理愛德華.達拉第(Édouard Daladier)與其他議員只得狼狽逃離一團混亂的國會。不幸的是,達拉第在回家路上被暴民認出。要不是憲兵隊及時趕到,這位法國總理只怕要被暴民扔進塞納河。

(Source: wikipedia)
當時,政府中有人力勸驚魂未定的達拉第宣布戒嚴並派遣軍隊鎮壓暴民。然而,達拉第本人不希望看到共和國陷入真正的內戰,更不確定當時掌管陸軍的保皇派將軍是否值得信任。幾天之後,他黯然宣布辭職下臺。這起事件造成近千人傷亡並直接導致政府更迭,堪稱法國第三共和建政以來最瀕臨內戰的一次危機。
面對右派的強勢挑戰,左派決定團結對抗。在經過短暫的混亂後,包括激進的法國共產黨與溫和的社會黨在內的左派,共同組成了政黨大聯盟: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並成功在一九三六年拿到政權。這是法國歷史上第一個左派政府,而人民陣線的領導者布魯姆(Léon Blum),更是法國歷史上第一位猶太人總理。
人民陣線上臺後,立即推行了一連串的激進改革:包括查禁愛國青年團等右派團體、推動賦予勞工罷工權與降低工時的新勞動法、擴大公部門推動公共建設的支出、把軍火工業國有化、首次在內閣中納入女性閣員。
不難想像,這些改革皆遭到了保守右派的強力反彈。他們憂心這個國家將會被聽命於蘇聯的共產主義者操控,陷入可怕的革命失序與無政府狀態。如此一來,法國的傳統價值將被永久破壞。
無論保守派的擔憂是否言過其實,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卻真切存在。他們對秩序與穩定的推崇,使得他們難以接受極端年代下的各種社會變動,並傾向將一切負面的狀況皆歸咎於共產主義。
曾經在德雷弗事件堅信德雷弗有罪的魏剛將軍,在一九四○年法國陷落的當下,為了合理化自己的停戰提議,甚至子虛烏有地向內閣官員宣稱,巴黎已經發生共產革命,必須趕快停戰以維持秩序。
魏剛不是唯一開罪於共產主義的人。當人民陣線在一九三六年勝選時,年邁的貝當元帥就曾私下表示,法國已然陷入了「精神危機」。而當他被雷諾政府重新請出山來挽救法國時,老元帥再次感嘆道:「我的國家被打敗了,然後他們要我回去談和與簽署停戰協議。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盛行三十幾年來導致的結果。」
對共產主義的敵視貫穿了一九三○年代至維琪政府時的法國政壇。這份擔憂最終讓法國在一九三九年開戰前夕查禁了法國共產黨,也讓法國錯失與蘇聯共同對抗納粹德國的機會。
一九三六年七月,人民陣線剛上臺不滿一年,鄰國西班牙就爆發內戰。
這場內戰加深了法國的意識形態矛盾。法國保守右派擔心法國會成為下一個西班牙,也擔心人民陣線會讓法國也陷入內戰與分裂的泥沼中。就連左派本身,也因為這場內戰而分裂。
左派分裂有內部的因素。法國共產黨希望增加軍事支出以對抗日益猖獗的法西斯主義,社會黨希望投資社會改革,而激進黨則希望維持共和傳統、降低改革幅度以免刺激右派。左派各黨之間的利益不一,導致整合困難、無法團結。
左派分裂也有外部的因素。蘇聯在國際上對其他社會主義流派日益高漲的敵視態度,除了讓其他左派難以與共產黨合作外,亦讓右派長期攻訐法國共產黨是蘇聯代理人的說法,愈發得到法國人的支持。
兩年後,內部分裂的人民陣線終於瓦解,留下困惑與失望的法國人民。許多對政治失望的人,加入了新成立法蘭西社會黨(French Social Party),這是一個標榜法蘭西傳統價值的右派保守政黨,前身是遭到政府打壓而解散的火十字團。這個政黨的口號「勞動、家庭與祖國」,日後將成為維琪法國的國家格言。
有愈來愈多的法國人,受夠了議會政體的無效率與眾聲喧譁,並期盼能有一位強人來領導法國。保守派報紙《小報》(Le Petit Journal),甚至拿「最受歡迎的獨裁者」這個題目來做讀者票選,而獲得第一高票的法國人居然是貝當元帥。對照第三共和立國初期對布朗熱將軍等軍事強人的敵視,這樣的轉變不可謂不大。
對一八七○年代的第三共和制奠基者們來說,共和制是最不分裂法國的制度。但對於一九三○年代的法國人來說,這句話的效力早已大打折扣。
極端年代下的意識形態矛盾將法國一分為二。這不只削弱了法國整體的國力,更讓對造的雙方無從妥協,從根本掏空了民主共和體制作為各黨派最大公約數的共識。有的史學家甚至用「法國對法國的戰爭」(Franco-French War)或「隱形內戰」這樣的詞彙,來形容第三共和時期法國內部的分裂程度。
然而平心而論,法國的分裂趨勢在一九三○年代晚期,似乎有好轉的跡象。
一方面,透過放棄金本位與投資軍事工業等手段,法國開始逐漸走出經濟大恐慌的陰霾;另一方面,接替人民陣線的新政府,採取了若干折衷妥協的政策,也有助於緩和左右分裂的程度。
一九三九年納粹德國違反慕尼黑協定後,法國更在外患的威脅下,展現了空前的團結。一切彷彿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重新來過:遭遇分裂危機的共和國,即將因共同的外敵而團結。
但歷史畢竟不會單純重演。
法國在戰場上犯了致命的戰略錯誤,它在錯誤的地方投入了最精銳的部隊,而德國如閃電般迅雷不及掩耳的機動攻勢,則讓法國來不及像上次大戰一樣彌補自己的失誤,最終導致了雪崩式的潰敗。
軍事上的失利,讓一切的復甦跡象都成了宛如迴光返照的泡影,也讓法國人發現,一九四○年的法國並沒有一九一四年的法國團結。那些從一八七○年代就對第三共和抱持各種不滿的人,即將得到一個重新改造國家的機會。
塵封的記憶:放棄民主的國度
一九四○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隕落。
「我感覺此時此刻法國社會徹底瓦解了,軍隊、政府、民心都渙散了。」當時正在巴黎報導新聞的記者夏伊勒這麼回憶。
震驚的法國人迫切地需要一個足以解釋現狀的說詞。而貝當元帥已經準備好了一套。他說:
我們比二十二年前還要脆弱。我們的朋友更少,我們沒有足夠的小孩、足夠的武器,也沒有足夠的盟友。這是我們戰敗的原因。
然後,他話鋒一轉,繼續說道:
我們讓自身的享樂精神壓過了犧牲精神。我們要求的太多,但付出的太少……我不會讓陸軍來承擔政客所犯的錯。
在今天來看,貝當此番言論像是在怪罪過去二十年來的人太草莓,而那些不負責任的政客,則要對這二十年來的政治亂象,乃至於對法國陷落本身,負起主要的責任。
一九四○年,有太多飽受分裂之苦的法國人,已經準備好接受貝當這套說詞。他們成為維琪法國的潛在支持者,並透過支持貝當的說法,將戰爭的痛苦與戰敗的恥辱,轉嫁到第三共和的體制本身。
法國已經準備好要放棄它的民主。
一九四○年七月十日,除了少數逃往北非的議員外,法國國會以五百六十九票對八十票的懸殊比數,全權授予貝當元帥修改第三共和國憲法的權力。法國國會此舉形同宣判了自己的死刑。貝當隨即頒布一系列的修憲法案,包括賦予自己指派與辭退內閣官員的權力、凍結既有國會並改透過自己指派的官員來負責立法。
在新的憲政體制之下,貝當形同掌控法國的行政、立法與司法大權,甚至還可以挑選自己的「繼承人」。從太陽王路易十四以來,沒有一個法國元首擁有這樣大的權力。
彷彿自我實現的預言般,一個萬眾期盼的強人誕生了。
在國民英雄貝當元帥的帶領下,法國終於揚棄了民主建制,轉而投入「國家革命」的懷抱。無論真誠與否,許多人相信貝當的「國家革命」能夠帶領法國走出過往的政治亂象與重回昔日的榮耀。既然自由、平等、博愛是導致失序與混亂的潛臺詞,維琪法國於是把國家格言置換成了勞動、家庭與祖國。
一系列「撥亂反正」的措施很快展開。
維琪法國透過打擊個人主義來重振家庭在法國的核心地位,將法國重新塑造成一個由貝當爺爺領導的家父長式威權國家。
維琪法國透過打擊女性主義與自由主義來提倡婦德和挽救生育率。女孩被要求接受家政教育,學校的教材開始將聖女貞德描寫成精於裁縫與廚藝。它修改民法的離婚要件,凡是結婚三年內一律不得離婚;墮胎自然是非法的,墮胎與協助墮胎者最重甚至可以求處死刑。
維琪法國還禁止罷工與工會,以避免人民陣線時期的亂象再現。新政府強調回歸農民與鄉村的傳統價值,以杜絕階級鬥的可能。此外,反猶主義受縱容,年輕人則被鼓勵加入天主教會。新政府認為恢復教會在生活中的權威,有助於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不是所有人都贊同維琪法國的作為,但共和國堅貞的捍衛者卻不夠多。前首相雷諾、達拉第、布魯姆等人都被長期拘禁。先前反對停戰最力的內政部長曼德爾展開最早的地下抵抗運動(他在一九四四年遭到維琪政府殺害),而戰爭部次長戴高樂則流亡海外,從零開始號召法國人反對維琪政府。
貝當的國家革命終究沒能持續。隨著二戰局勢的逆轉與納粹德國愈發糟糕的占領政策,法國人對貝當與新政府的支持迅速冷卻。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第三共和的滅亡與維琪法國的誕生就成了法國人所不願面對的一段回憶。
在二戰結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一九四○年自願放棄民主、擁抱獨裁的往事,遭到了法國人的刻意遺忘。
在戰後的審判草草定罪了若干維琪政府的官員後,關於第三共和國隕落前夕的記憶似乎就此塵封。或許,正如同研究法國史起家的英國史學家東尼.賈德(Tony Judt)在《戰後歐洲六十年》(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當中所說的,像這樣的集體遺忘有助於國家復原。
法國年鑑學派的史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在一九四○年法國陷落時正在法軍服役,並在德國戰俘營度過他的二戰歲月。布勞岱爾在一九七二年的個人遺囑中自陳,當年之所以會用結構性、長時間的角度去寫他的成名作《地中海史》(The Mediterranean),有部分原因正是出於自己不願面對當年經歷的悲慘事件。他只能選擇拒絕、否定與降低這些事件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他想要相信,歷史與命運都是在一個比這些事件更深遠的層面上被書寫。
與遺忘並行的,是對過往的選擇性記憶。
多數法國人選擇相信,他們是遭受貝當與維琪法國政府的欺瞞,他們選擇相信自己,也很快響應戴高樂號召的抵抗運動,為民主和自由而戰。這或許是法國人在面對放棄民主的這段難堪過往時,一種自我調解的方式。
「抵抗運動」就此成為二戰後法國的國家迷思。
戴高樂與許多共和支持者們特別助長這樣的迷思,因為這有助於他們否定維琪法國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強調維琪法國的異常與非法,有助於戰後的新共和維繫自身政權的正統與延續。這樣的迷思持續了數十年。直到一九七○年代以後,才有愈來愈多的法國人願意回頭檢視這段失落的記憶。
即便如此,維琪的幽魂從未遠去。維琪二字,象徵著法國人自願放棄民主與擁抱獨裁的那段過往,更提醒著當年有許許多多的法國人因此失去生命,包括那些被維琪法國送至納粹集中營的法國猶太人,以及不受「國家革命」歡迎的人們。
一九八一年,左派社會黨領袖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當選法國總統,他早年曾支持貝當政府、並在維琪法國任職的往事又再度成為政壇話題。一九九四年,即將卸任的密特朗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他認為法國不該為猶太人的死負責,應該負責的是維琪政府,而維琪政府不等於法國。密特朗的「切割」言論引發喧然大波,並遭到繼任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的嚴厲駁斥。
同樣的爭議在二○一七年的法國總統大選中再次上演。「民族陣線」的候選人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同樣認為,法國作為一個國家,無須替猶太人的死負責,因為維琪法國無法代表法國。

(Source: wikipedia)
密特朗和勒朋的說法,顯然也是選擇性遺忘(或記憶)的呈現,而這自然是因為面對真相並不容易。法國人很難去承認自己選出的國會代表曾經用相對民主的方式,自願在一九四○年法國陷落的當下放棄了民主共和的建制。
「共和前進」的候選人馬克宏對這樣的態度深深不以為然。他在當選總統後,於二○一七年七月接見以色列總理時表示:
將維琪法國視作一個誕生自虛無、又回歸到虛無的政權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是的,這很方便,但它是虛假的。而我們不能將自尊建立在謊言之上
.png)
一本透過歷史了解世界局勢的書:12件關鍵年代的關鍵事件。
在這個紛亂吵擾、光怪陸離的時代,新聞幾乎以分秒為單位更新,電視頻道似乎就快要不夠看,網路又闢出多重戰場,世界在每個人的點指間鋪展,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動態成百成千從我們眼前溜過,每個瞬間都在創造歷史,而歷史,是連結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力量。美國歷史學家提摩希.史奈德就在《暴政》一書中如此評價歷史:「歷史不會重複,但它為我們燃起提點的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