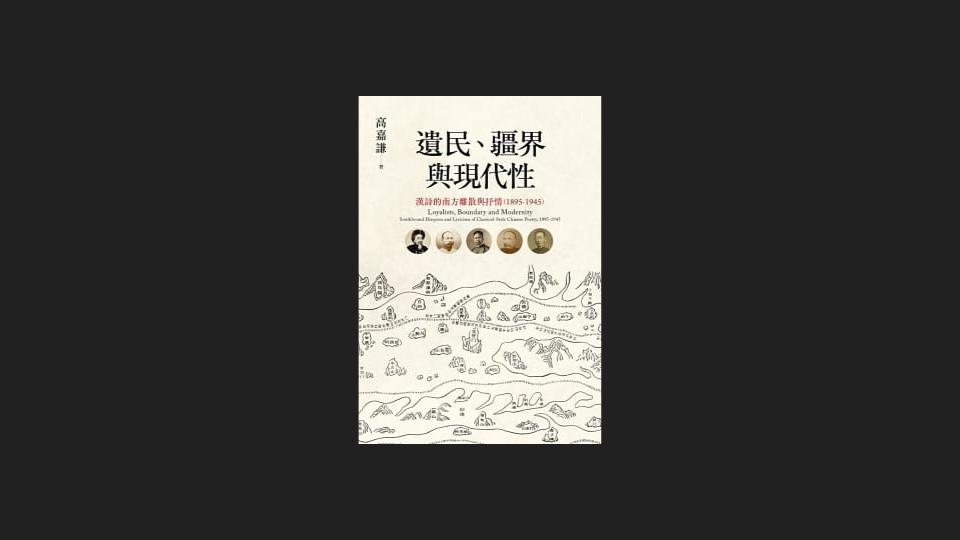南明時期,兩位典型的儒家文人跨境出海,流離飄泊,終老異域。
朱舜水( 1600-1682 )和沈光文( 1612-1688 )是同樣生於明朝萬曆年間的士人,兩人相差十二歲。完整的儒家教育根基與易代亡國的際遇,讓他們在亡明之後奔走南明政權,投入反清運動。
當反清終不可為,朱舜水轉徙越南,最終根留日本。而沈光文本想避居泉州,卻巧遇颱風,無意之間飄抵臺灣。當時的臺灣遭荷蘭佔據,漢人政權還未曾建立。二人的離散路徑顯得獨特且偶然,卻同時預告了異於傳統的南渡,而有了跨界的境外遷徙。
※※※※※※※※※※
流亡日本的朱舜水
為了反清與避禍,朱舜水數度流寓越南、暹羅,七次赴日。當中曾為恢復南明政權而屢赴日本借兵,還曾投入鄭成功部隊會師入長江的作戰。困居越南期間,受盡病苦與囚禁之禍。
其間給魯王奏疏,望其拯救,詳述了自己流離慘狀:
「使臣目送歸舟,血枯腸斷。況資裝俱竭,肘見履穿。僮僕遁逃,伶仃孤苦,肌膚憔悴,形容枯槁,遣日如歲。若至明年此日,誠恐雞骨支離,久填溝壑。」

他後期旅居日本,經濟窘迫,只能靠友人接濟。幾經波折才受到禮遇往江戶講學,但晚歲病痛纏身,離鄉二十餘年後始有家書返鄉,最後自行以檜木製棺,孤孓終老異地。
家國危難,士人境外離散,本來風險不小,際遇難料。朱舜水以遺民姿態在海外行旅,生前死後在中土國境內都沒有影響。
亡命天涯的遺民,苟且偷安已是大幸。抵日初期,因為復明抱負的失落,以致遺民心志起伏不安。但朱舜水對異域環境的感嘆:「孔、顏之獨在於中華,而堯、舜之不生於絕域」,卻又表現他以中原為本位的遺民主體。
後來受到水戶侯源光國的禮遇,以致後續的興館授業,傳播儒家思想,在日本延續中華文化命脈,恐怕不僅僅是飄零的遺民經驗,而是表現遺民意志與家國認同的一種文化播遷形式。
他以大明的國家認同作為自我的歷史意志,終身堅守明代衣冠,政治與文化認同合一,鞏固了遺民身分的貫徹與實踐。在有限生命之中,他意識到「一旦老疾不起,則駭骨無所歸,必當葬於茲土」,因此唯恐身後弟子不懂明朝禮制,又擔心屍骨棺木快速腐朽,遂在生前自選優質檜木製棺。
這種保留故明衣冠的做法,無異於遺民自建生壙,以身體政治的形式,抗拒滿清入關的鼎革易服。然而,朱舜水遠在東瀛,堅持的遺民形象在中原境內竟無人知曉。

他唯一在異域日本安身立命的依據,只有儒學思想的教化與漢學教育的建立。這是漢人知識菁英流亡的文化使命,凸顯自我國家與民族認同的關鍵手段。這種以遺民心志成就的文教事業,以身體言行自我表述的遺民面貌,或許在朱舜水的意料之外,展現了另一種離散的中華文化路徑。
※※※※※※※※※※
然而,這些終老異域的遺民,顯然是中原遺民政治裡的錯置。朱舜水落葉歸根的願望,只能等到帝國末日的清末民初,新時代降臨前夕;一大批將棄絕在古典傳統的文化遺民,重新發現、發揚朱舜水所表徵的文化情感與民族精神。因此,作為「亡命儒者」的朱舜水,成了召喚明季歷史記憶重要的文化想像,一種政治身體的現代觀照。
時過境遷,清末民初一批批新人物先後抵達日本出使、留學和考察,在新世界發現舊時代的故人,竟然對日本儒家文明做出重要貢獻。
黃遵憲駐日期間,對朱舜水事蹟做了評價:「海外遺民竟不歸,老來東望淚頻揮。終身恥食興朝粟,更勝西山賦采薇」。「分海外遺民」讓黃遵憲感到如此驚異,在於朱的不食周粟與亡命日本,塑造了值得讚嘆與欣賞的知識分子風骨。
朱的事蹟提供了對遺民正統浪漫的想像,成為往後帝國潰散,遺民再興的一個參照的典範。遺民的離散之路,吸引了這批探訪新世界的知識分子的好奇目光。
相對朱舜水的孤獨身世和飄零羈旅,他們的境外流寓懷抱強烈探求新知與救國的欲望。而朱以一介遺民布衣,在日本講學授業,傳播境外儒學,卻走在歷史的另一端,和這些出訪異國,研究日本風貌的官方使者,形成弔詭的對照。
流寓不歸的遺民,觸動了他們的家國神經。於是,朱舜水的思想與事蹟,開始在中國境內反滿愛國的氛圍內傳播,構成時人重鑄晚明符號的一環。 1915 年,郁達夫留學日本期間,在朱舜水紀念會上,曾賦詩一首:
采薇東駕海門濤,節視夷齊氣更豪。赤手縱難撐日月,黃冠猶自擁旌旄。白詩價入雞林重,綠耳名隨馬骨高。泉下知君長瞑目,勝朝墟裡半蓬蒿。
郁達夫除了讚嘆朱的節氣,和赤手抗清的豪情,還平實呈現出朱舜水重新被「經典化」的際遇。他以白居易詩受到普遍愛戴,隱喻了朱舜水名重於異域。朱的遺民分量,一如千里馬的市價行情,行家趨之若鶩。這表現了中原境內重新發現朱舜水的熱烈情景。
當然更值得朱舜水在九泉之下感到寬慰的,正是滿清帝國已成昨日黃花,清帝陵早已淹沒在蓬蒿之中。從郁達夫的理解看來,域外遺民的複雜心路,實已簡化為固定的亡國抗清遺民形象。
這波「朱舜水熱」重塑的遺民典範,其實建立了一層學術意義。
梁啟超撰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兩畸儒」嘗試為他做了學術史的定位。但梁著眼的仍是離散儒學的價值。尤其剛烈抗清的精神感召,搭配正統漢學的實踐,中華道脈在異邦延續。
將朱舜水的作為放在晚清帝國與文化淪陷之際,確實有振奮人心之功。看在海外流亡十六年的康有為眼裡,「先生浮海能傳教,卻望神州應大悲」,「我遊印度佛教絕,一線儒傳或賴君」。朱的跨境越南,儒教東傳,正好跟他在周遊南洋群島,在華人社會鼓吹的孔教復興運動有了相似的離散際遇。
換言之,士人離境,流竄絕國,開展具體的文化事業,反而映襯帝國境內的困局。自此中原疆域意識一再懸擱、延異,呈顯士人離散的積極意義,儘管流離旅程哀毀難耐。
於是,在晚清新興人物與民初遺民眼中,境外離散勾連上一重慾望想像:憂患避禍的流亡之途,延續斯文於一脈。境外因而構成士人延展的文化地理。清遺民瞿鴻禨對朱的事蹟展開頌揚,勾勒出歷史形象的深沉迴響:
崎嶇島海間,起仆爭寸尺。漢鼎亦已淪,楚弓幾可得。……窮荒一儒冠,黃髮專經席。天將紹箕子,傳道昌其跡。……大招三閭魂,嘉薦崇鄉邑。遐哉斯逸民,尚有古道直。聞風興頑儒,仰式穹碑刻。
朱舜水在清末民初重新登場,建祠堂以供紀念。這流亡在歷史時間之外的際遇,恰恰回應了這批遊走乙未、辛亥的歷史遺民的內在心聲。
飄零臺灣的沈光文
1652 年,與朱舜水同屬浙東遺民的沈光文被颱風吹往臺灣,在宜蘭上岸,從此在臺灣居住了三十六年。
他先後經過荷蘭、明鄭三代政權與清朝統治的多重政治際遇。政權嬗變,自身的應世進退尤其顯得飄零無根。他先遭荷蘭人猜忌、偵伺,後被鄭經恨惡,幾遭不測。清領時期舊識浙閩總督姚啟聖本欲安排返鄉定居,卻因姚病故而不了了之。唯有在鄭成功渡臺之時,受到禮遇。
他的流寓生涯顯然兢兢業業、飢寒交迫。他曾出家避禍,入番社行醫,教人識字讀書。流寓者恰似拓荒者,一身儒家教養走入窮荒異域,試圖以個體的教化涵養來改造與命名這邊陲孤島。
當時諸羅知縣季麒光有如此評價:「從來臺灣無人也,斯菴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始有文矣。」指出沈光文將文教南遷的功業。
但這不也同時勾勒出流寓者走在境外的蹣跚步履。那存身的學養技藝,將眼前流離地理轉化為書寫與定位自我的出路。
他晚年與清朝來臺士人共組臺灣第一詩社「東吟社」,細數重頭之際,不禁慨嘆初抵臺灣的鬱悶與邊緣處境:「同志乏儔、才人罕遇,徒寂處於荒埜窮鄉之中,混跡於雕題黑齒之社。」畢竟他登陸臺灣時正值荷蘭統治。作為抗清的南明志士,這種不見中原文化命脈的陌異感,必然是放逐絕域的感受。

沈光文將自我從中土走向邊陲的悲情,訴諸於教化與詩文,基本表徵了境外遷徙的一組概念:憂患共生的跨界經驗,將地理流動轉化為文學書寫。當飄零個體在境外呼喊中原,沈光文詩裡「歲歲思歸思不窮,泣岐無路誰更同?」(〈思歸〉其一)、「歸望頻年阻,徒歡夢舞斑」(〈歸望〉,頁一二),其實導引出從遺民轉向移民的現實依據。當歸鄉無望,眼前久居的異域漸漸成為故鄉。
在他表現亡國之痛的遺民情懷之際,筆下不忘記錄生存異域的風土民情。地理遷徙讓古典詩文進入異域,展開命名、紀實與想像的循環。這些類似竹枝詞的漢詩寫作,已間接帶出境外地理遷徙的寫作倫理。沈光文有一組狀寫水果的漢詩,隱約展示了這樣的改變:
稱名頗似足誇人,不是中原大谷珍;端為上林栽未得,只應海島作安身。(〈釋迦果〉,頁 7 )
種出蠻方味作酸,熟來黃玉影欒欒;假如移向中原去,壓雪庭前亦可看。(〈番柑〉,頁 7 )
枝頭儼若掛繁星,此地何堪比洞庭;除是土番尋得到,滿筐攜出小金鈴。(〈番橘〉,頁 7 )
平常可見的海島水果,在簡易的咏物格式裡,卻彰顯了地理意識。詩人比較中原與海島,凸顯無論釋迦或番柑,都有其異於中原的特質與美感。

水果進入漢詩內容並非創新,但沈光文的家居日常經驗裡,熱帶水果凸顯地域概念,以異樣的詠物感性進入了漢詩,無形之中詩人書寫的倫理已在改變。處身邊陲海島,對比過往的中原大陸經驗,中原/海島的對照自然作為詠物的框架。
「只應海島作安身」、「假如移向中原去」,詩人目光的游移、想像,表現的已是遠離中土後的地方性眼光。又或一邊是「此地何堪比洞庭」的中原想像,另一邊則是「除是土番尋得到」的臺灣實景。但真正的寫作趣味不在故園情懷,而是「番橘」構成詩的在地感性。這種出入詩人眼界的比較,展示漢詩美感之餘,不也同時檢驗著詩的表現力。
作為第一位替海島水果命名的中原詩人,他的漢學教化與遷徙事實,融合為眼前寫景狀物的視野。他在狀寫水果,進入日常生活景觀,何嘗不是描述在地感的一種形式。沈光文詩裡的感性,其實是地理意義上的感覺結構。從中土到邊緣的經驗架設了他的比較視野,同時也形塑書寫空間。
眾所周知,臺灣的遺民論述始自鄭成功入臺開闢的島上明鄭政權。
這是南明延續的抗清勢力,代表明室的海外正統,同時也是明衣冠的文化命脈。但對照沈光文這樣的遺民際遇,入臺實屬因緣際會,而且比鄭成功還早了九年。
他進入番區,實行漢學教化和行醫,儒者的實學精神深化了遺民的歷史意志。走在境外絕域,遺民的志業不僅是環繞在單純的中原政治,反而在複雜地域實現了不同於中原境內的遺民精神。
明鄭統治臺灣僅二十二年,遺民正統終成過眼雲煙。沈光文居住臺灣的時間從荷據、明鄭到清領,他見過窮荒異域,受過禮遇,也遭到陷害避禍,最後組織臺灣最早的詩人結社唱和,一番心路轉折,遺民眼光已複雜多變。
沈光文在臺灣島內度過的餘生,可以總結為海東文獻的鼻祖,其文教深耕已成島內遺民論述的一脈香火。如此說來,遺民意志經過歷史時間的變遷,已慢慢變成地域性的文化實踐。
※※※※※※※※※※
綜觀南明遺民朱舜水和沈光文的流亡,他們跟糾葛於境內遺民傳統的錢牧齋、王船山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實踐了境外離散的路徑。
這不同的四種遺民類型,在遺民傳統的關鍵論述上都共同主導了近代遺民視域。錢牧齋、王船山、朱舜水在清末民初的重新粉墨登場,不但拓展了遺民論述氛圍,也直接支配座落在「現代時空」的乙未、辛亥遺民一代,他們對遺民及其背後的古典價值與離散面向的再度詮釋與安置。
無論明季遺民是一種傳統的「發明」或「發現」,在帝國裂變、殖民臺灣、民國建立的複雜情境下,這套遺民傳統相應有著重新辯證與詮釋的歷史空間。

中國境外的「南方」書寫
本書將透過遺民、離散、境外等關鍵的幾個概念範疇,
去開展二十世紀漢詩寫作呈顯的現代性的種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