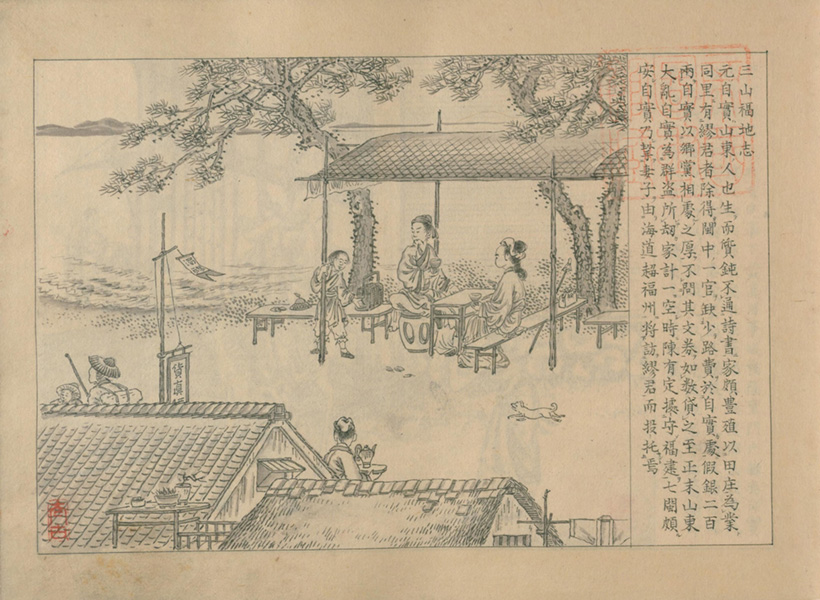《剪燈新話》
1442 年三月(明正統七年二月),國子監祭酒李時勉(明永樂二年進士)上書皇帝,稱自己對於目前那些「假托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的作品,於市井坊間流傳氾濫的憂心。他特地舉出一部名為《剪燈新話》的怪誕、情色小說作為例證。
這部小說的序言作於 1378 年(明洪武十一年),並且於 1420 年(明永樂十八年)重新刊行。不巧,很可能是因為有國子監學生在讀這部小說,使得李時勉見到該書的抄本,這使他相當不悅,李時勉並未清楚說明這部小說犯忌之處何在,只是含糊指出該書內容的不得體。
令他更為憂心困擾的,看來並不是這部小說本身,而是小說的讀者群,因為他描述說:「至於經生儒士,多捨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在李時勉看來,這絕非受過高等教育的文人學士所應有之舉,他還悲觀的想像,事態如再這樣發展下去,將會產生骨牌連鎖效應:「若不嚴禁,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

究竟什麼才算是「邪說異端」?而一位學者在被認為偏離「正學」之前,又有什麼樣的門檻限制,能夠對其發揮攔阻作用呢?對此,李時勉沒有詳細的解釋,而我所過目關於十四、十五世紀書籍檢查的奏摺,也同樣語焉不詳。從儒門正宗的嚴肅觀點來看,李時勉想必會覺得自己這番主張其理自明、無須多加解釋;然而正如我在別處地方曾經討論過,儒家思想當中並沒有打壓輕佻、標新立異主張的傳統。
自然,也不是所有的書籍都承載了正道,宋儒程頤曾經針對和他同時代的若干十一世紀著述發出警告,認為不好的作品足以「損道」,浪費時間去讀這些著作,將會荒廢學業;可是,儒家士大夫並沒有因此更進一步,贊同國家應取締這些書籍。倘若閱讀使「道」有損,錯在讀者,而不在書籍;如果讀者的偏差需要被矯正,責任在其師長,而不在國家。
可是,此時某些明代的官員卻想把國家給拉進來,動用國家的資源來追查那些他們認定有問題的書籍。李時勉正是如此,他要求禮部,訓令派駐各省的御史去搜繳《剪燈新話》:「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從兩層意義上來說,李時勉的這項要求顯得極不尋常。
首先,明代並沒有合適的國家監察機制執行這類任務,由於現有體制內欠缺反映、回報此種事項的程序,各省官員們在不能確定自己努力辦理此事是否能獲得回饋、甚或得到朝廷的重視之時,還能夠帶著熱情來執行此項任務,著實讓人懷疑。因此,當皇帝的閣臣將李時勉的奏摺發交禮部討論時,禮部尚書的回覆意見就帶著一種小心和審慎,認為這樣的訓令「切理可行」。但是,這道訓令發出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在現存的史料記載中並沒有交代。
李時勉說「問罪如律」,顯然是要藉由訴諸《大明律》來支持自己奏摺中的建議,不巧的是,《大明律》實際上並沒有圖書檢查的條款。官員們如果一定要懲治《剪燈新話》的持有人或販售者,可以在《大明律》裡找到兩處類似的罪名。
頭一處出現在「禮律」部分,即禁止民眾持有朝廷專用器物,如玄象器物、天文圖讖、歷代帝王圖像、以及金玉符璽等。
該條款十分逗趣的,以朝廷時常出現的循環論證方式,禁止「當禁之書」。這種循環論證說明,如果不是《大明律》的制定者當初有意將這類罪名模糊化,就是更為簡單的表明,該條款的適用性是不言可喻的,因為皇權的神聖與正當性是無論如何都不得冒犯的。既然天象向來總是潛在地與政權合法性相連結(在歐洲也是一樣),任何解讀這些天象的途徑管道,諸如占星器物、天文圖盤等,都在禁止之列。
不過,這種焦慮並未導致律法將「書籍」這一種類列入懷疑的對象,所以也就與李時勉建請檢查書籍的提議產生不了直接關聯。相反地,該條款倒是確保了專屬於皇帝的特別權利,不致於脫離朝廷法令的掌控,而在民間流通。
官員們還可以運用《大明律》中的另一項條款來取締書籍的擁有人與販售者,那就是針對編著或收藏「妖書」的條款。根據《大明律》的解釋,所謂「妖書」,即蠱惑人心的著作。這項罪名在「刑律」當中相當顯眼,被列在第三順位,僅次於「謀反大逆」和「謀叛」之後──這條法律意在將保護皇權的範圍,延伸到創作領域當中,因為創作可能以明文表達,對國家的權威造成威脅。
該條款和前面所述的「禮律」條款不同,它將懲罰的範圍,由因為著作內容觸犯皇權者,擴展到在言論上有威脅君主統治之虞者,特別是那些預言或宣稱即將改朝換代的文字或言論。這項條款還可以進一步延伸,適用於某些並未主張推翻明代統治、但是鼓吹想像中國度的文字或言論,像是民間祕密宗教裡經常提及的千年救度,特別是那些以道教作為標榜的文字著述。
我在《明實錄》的記載中發現時間最早的一起檢查案例,就是這類標榜道教的文字著述。1390 年,有一名開封府民眾向朝廷進呈一千多部名為《九宮太一》、《太一入運》、《太一草算》等的禁書。由於「太一」向來被視為世間萬物的神祕起源,其是預知未來的重要概念,因此有人認為值得向朝廷舉報這類圖書,也就不足為奇。
《明實錄》中並未將這些著作冠上「妖書」之名,也沒有記載皇帝對此事的反應,不過大致上應該是將其歸入律法中這一類範圍。《明實錄》之後在記載不為國家所認可的著作時,最常使用的名詞,正是「妖書」一類。
例如 1481 年(明成化十七年)時,一名廣東民眾,運用其「偶得妖書並印文地圖」,起來「惑眾倡亂」;1498 年(明弘治十一年)時,北直隸一名男子糾眾攻打縣城,行前先「造妖書惑眾」。兩人後來都被處決,不過他們所持有或製造的「妖書」,可能是與之後聚眾公開叛亂的罪行相連,因此才被認定為有罪;倘若他們之後並未公開叛亂,朝廷似乎不會注意到這些「妖書」的存在。
《明實錄》中記載的大部分這類案件摘要,都沒能提供「妖書」的內容,然而在 1578 年(明萬曆六年)時,湖廣出現一部名為《大乾起運錄》的「妖書」,書名就清楚表露反朝廷的意圖,自然也就逃不過遭到鎮壓取締的下場。
回到 1442 年的《剪燈新話》一案,難道李時勉真想將《剪燈新話》這部小品歸入惑眾作亂一類禁書?所有接觸過這部小說的人,都將一概遭到處決?如果和萬曆年間《大乾起運錄》一書內所隱含煽惑叛亂的威脅相比,對《剪燈新話》的處置似乎是太過嚴厲了。
我懷疑無論李時勉認為該作品敗壞道德的程度如何,他都會請求皇帝將其視為「邪書」加以查禁。同樣的,李時勉對此書「惑亂人心」的評斷,以及認為這部小說將會引來道德淪喪骨牌效應的信念,都暗示著誨淫誨邪的作品,日後被歸類於「妖書」一流,此時已經踏出了一小步。
三個世紀後,《大清律》完成了「淫書」與「妖言惑眾」之間的連結。《大清律》幾乎是逐字照錄的沿用了前述《大明律》的兩項條款,而在「妖書」條款之下則附加了新的適用範圍。
在 1740 年(清乾隆五年)修訂版的《大清律》中,又在「妖書」條款下補充了四條章程,指名應受檢查的著作範圍較明代更廣。該補充條款詳細列舉出三種文字形式,應被視作「妖書妖言」,分別是「妄布邪書,書寫張貼,煽惑人心」、「造讖諱妖書妖言」、以及「以鄙俚褻嫚之詞刊刻傳播者」。

如果是在清代,李時勉便可以毫無困難的將《剪燈新話》歸入「妖書妖言」這一類中。他在 1442 年向朝廷呈上的建請,對於將律法中關於「妖書」一類的禁令適用在取締政治、道德方面的違禁作品,在實際上起到了推動作用。
上述《大明律》的兩款條例,都沒有對書籍這種文字刊布形式給予特別關注。這正是我將兩款條例中的「書」字英譯為「著作」(writings),而不譯為「書籍」(books)的原因。(在中文裡,「書」既有著作之意,也可指書籍。)
本朝初年制定律法時,並未意識到日後印刷技術將會威脅帝國的統治。然而,這種不在意的態度,到了明代末季開始發生變化。1609 年(明萬曆三十七年)時,紹興有一位名叫陳應明的男子被控「假印偽敕妖書」,儘管此案的重大關鍵在於陳偽造朝廷敕命,不過「假印」這個奇怪的措辭用語,代表印刷技術問題在此時已經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了。
當 1626 年(明天啟六年)時,十方僧人福本將自己私下收藏的揚州知州劉鐸(1616 年進士)題寫在扇面上的詩句印行出版,當中收入錦衣衛知事歐陽暉作的一首詩,沒想到就因此惹禍上身;南京刑部在審查之後,判定詩中「陰霾國事非」一句犯禁。
在《熹宗實錄》裡關於本案案情的短短三行簡介裡,就有四次提到「圖書」或「製書」等詞。這一情況說明了圖書在市面上流通的可能性,和書籍本身的內容一樣,開始成為讓朝廷感到棘手的問題;同時也表示印刷技術作為圖書檢查的充分條件,在這時已經逐漸顯露頭角。
不過,一直要到 1740 年《大清律》修訂之時,印刷、商業流通等問題才正式躍上檯面。法律細則中明確地舉出「刊刻」(出版者)、「傳播」(散布者)、「坊肆」(販售者)和「刻印」(印刷者)等字眼。當朝廷準備要查禁某一部書籍時,上述與這部書籍相關的人等,就可能會遭到懲處。
法律條文的更動,總是遠遠落後於社會變遷的腳步,甚至還落在法律實踐的後面。對於那些想要動用國家力量取締違禁圖書的人,他們注意到印刷所引來的問題,應該不需要花上四個世紀的時間。當李時勉在奏摺上主張按照《大明律》對那些「印賣及藏習」書籍者「問罪如律」時,顯然已經對商業印刷造成的問題有所認知。
《大明律》的制定者並未提到印書者及販售者,但是李時勉卻提到了,很可能正是由於那部 1420 年版《剪燈新話》帶來的衝擊,促使李時勉尋求以國家力量作為出面介入干涉的適當機構,從國子監學生手中,將這部小說收繳過來。
印刷技術的發達,使得原本不該接觸如《剪燈新話》這樣小說的人們,讀到此類著作的機會大增。除了取締學生手上的這種小說之外,還必須做一件事情,不多不少,就是那件事情。
《焚書》與《藏書》
明代圖書檢查最為知名的事例,莫過於言官張問達彈劾素有爭議的思想家李贄(1527-1602),並導致後者自殺一案;此案經常被後世學者引用,作為明代實施圖書檢查制度的證據。

1644 年之後的學者,經常評論這個案例,他們讚揚張問達的攻擊,認為這是對於明代思想誤入歧途的一次公正審判,同時還將李贄當作是早於他之前即發生的明代道德崩潰之代罪羔羊,而明末的道德淪喪,最終造成國家的土崩瓦解。
在他們看來,李贄的著作有部分已經危害到中國文化的存續命脈,因此禁燬他的著作,並不是濫用國家權力之舉。然而在另一方面,年齡只較李贄略為年輕一些的那個世代,儘管對李贄在北京所遭受到的待遇感到驚駭,卻仍然拒絕向隨之而來的圖書檢查服軟低頭。
李贄在 1570 年代時開始有系統的批判儒家權威思想,當時他是一小群知識分子講學結社當中的成員,這群人以南京為主要活動場所,銳意思索德行以及儒佛合一的可能性。李贄從官場退下來之後,逐漸開始懷疑以外在標準建立內心絕對道德判斷的可能性。在他看來,所謂真理,並不是登載於儒家經典上的那些文字;人唯有透過良知內省,才能夠求得真理。此後,李贄逐漸和之前往來的友人疏遠,並且在 1588 年(明萬曆十六年)落髮為僧。
不過他並未正式出家,而是以儒佛合一的居士身分度過餘生。在一場論戰過後,李贄終究還是被迫離開他位於湖廣北部的暫時棲身處。1602 年(明萬曆三十年)四月,當張問達(卒於 1625年)上書彈劾李贄之時,後者正住在北京近郊(通州)、亦友亦徒的馬經綸(1589 年進士)處。在張問達向李贄提出的諸多指控當中,其中有一項,認為李贄的著作將會對年輕世代造成危害。
從 1590 年起,李贄就勤於將所著的文章、讀書筆記和書信刻印刊行,並且廣為傳播流通,他為這些著作取了兩個頗具煽動性的書名──《焚書》與《藏書》。張問達請求將這些著作如同其書名那樣付之一炬。
李贄在為自己辯護時,承認「罪人著書甚多」,卻辯稱其全部著作「於聖教有益無損。」在氣氛嚴酷肅殺的當時,李贄這番自我辯護,太容易被看成是虛詐的狡辯,我們可以從一位當時人的著作中感受到這種氣氛。屠隆(154-1605)在其於 1600 年出版的《格言集》序言中提到,曾有一位友人提出警告,不要任由自己的著作「遠播通都」。屠隆決定聽從朋友的忠告,表示將著作「姑庋之篋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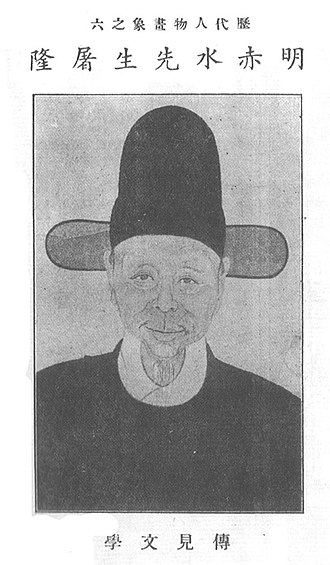
可見,兩年之後將李贄掃入監獄的這股圖書檢查寒流,同樣也曾影響他人;不過李、屠兩人仍然敢於公開宣稱自己的著作中有若干具爭議性的內容,從這一點來看,他們並不認為自己的著作會立即成為朝廷禁燬的對象。或許他們如此宣告,並不是有預感朝廷的圖書檢查將要降臨,而是想要表達一種不受俗世所羈絆的思想自主。
朝廷是否真的認為屠隆和李贄的思想很危險?
張問達在彈劾奏章之中,確實曾譴責李贄對儒家經典與孔子的批判和嘲笑,但是張對李贄批判的重點,在於李的行為,尤其是聲稱他和門下一位女弟子有不正當關係。這種人身攻擊是張問達的彈劾背後帶有政治意圖的鐵證。張的這一指控,涉及李贄門下一位身分特殊的弟子,即名臣梅國楨(1583 年進士)孀居之女。當時,梅國楨正與內閣首輔大學士沈一貫(1531-1615)為首的黨派(背後有宦官支持)發生衝突,而沈一貫正是張問達的政治後台。張問達在聽聞李贄準備攻訐沈一貫的傳言後,決定先發制人。
然而傳言並不確實。當時之人都認為李贄只是被犧牲的砲灰,梅國楨才是張問達要攻擊的真正對象。「人未嘗不知此老之不能惑世,未嘗不知此老之不能宣淫」,提供李贄居停的馬經綸,在他自殺之後不久即如此說道:「然今日獨恝然為此事者,其意不在此老也昭昭著也。」
朝廷後來對李贄的判決是暫時處以緩刑,但是責令他將其書籍刻版焚毀。不過判決的詔令留在宮中遲遲未能發下,於是李贄寧可選擇自我了結性命,而不願面臨被押解回鄉的公然羞辱。
歷來對於李贄一案的討論,大多聚焦於李贄思想的實質內容,張問達的彈劾在道德層面是否適切,以及思想衝突所涉及的本質問題。但是學者姜進相當具說服力的論證指出,朝廷之所以迫害李贄,並不是因為他的思想犯忌。李贄的各種主張或許引來不少爭議,不過如果李贄謹慎地遠離京師這一是非之地,通常朝廷不會去注意到他的思想。
姜進因此做出結論,使李贄招禍上身的是他種種離經叛道的「異端行徑」(heteropraxis),非關離經叛道的思想:「正是由於李贄本人現身於京師近郊地區,使得朝廷有了對他採取行動的理由,而不是因為他的著作流傳的緣故。」
這一論斷很有道理,李贄離經叛道的思想,朝廷可以將其視為他個人的誤入歧途,無須動用國家力量加以撲滅;但是我並不認為李贄刊行的著作與他所遭受的指控毫無牽連。試想李贄所撰著作,不但是承載其精神思想的實質載體,同時更是他個人身分的象徵,能夠將李贄的名聲廣泛散布到各地。
張問達就相當重視李贄的著作,特別指出李贄「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譯按:李贄號卓吾)」之事實,以及「流行海內,惑亂人心」的後果。張問達的建議是這些著作「不可不毀」。如果這起書籍檢查的案例實因李贄的行為而起,而非由於思想惹禍,則李贄積極將自己的著作付梓刊行,正也是他的離經叛道行為當中之一環。李贄著作的出版,雖然為他帶來聲譽,但是卻也威脅到某些人的地位,使他們煩惱不安。
儘管張問達請求朝廷銷毀李贄的著作,但是在此後的四十餘年間,人們還是繼續刻印、收藏和流通李贄的作品。若干李贄生前未曾出版的文章,於 1618 年(明萬曆四十六年)集結成冊,而且直接了當的以《續藏書》為名問世。編纂這部作品者不是別人,正是在南京學術界資望頗高的焦竑(1540-1620)。
正如李維楨(1547-1626)在這本書的序言當中所說:「李卓吾先生沒,而其遺書盛傳。」在其序文之末,李維楨甚至還相當大膽的列舉出所有與李贄有關聯的著名人士。七年之後,御史王雅量再次請求禁燬李贄的著作,但這一次矛頭所指還更進一步,除了李贄的著作,更包括流通散布其書籍的商業網絡,要求「不許坊間發賣。」
官方對此事的反應和上次一樣,似乎有些漫不經心,因為就在第二次針對李贄著作的禁令下達十五年後,錢啟忠(1628 年進士)又發起一場募款活動,欲敦聘寧波一家書坊重刻《李卓吾制義》一書,這本書是李贄以所謂的「八股」或「制義」撰寫而成的科舉應試範本集。雖然清代末季時,人們對於八股取士迭有批評,但是在晚明,李贄、錢啟忠,以及當時知識階層的其他人士,包括屠隆在內,卻都不認為「八股」這種文體有何過錯。
朝廷有令禁止李贄著作,錢啟忠對此並非不知,因為在他倡議募款重刻李贄著作時,就曾提到「聞先生被逮時,當事者火其書,一切制義之在版者,以壞文體,並禁。」但是對錢啟忠來說,此種禁令實在無關緊要,並不能改變他閱讀、出版李贄著作的決定。「(衛道人士)甚欲埋其(李贄)名,而不能投其字於水火。」錢啟忠如是欣慰的表示。
事實上,朝廷對李贄著作的禁令,在京師之外廣受鄙視、嘲弄,這反映出當時的知識分子,都認為此種基於黨爭而起的決策,沒有維護贊成的義務,更遑論因而感到恐懼了。
此事還有其他的象徵意義,無論國家多麼希望將某些書籍從公共領域中移除,只要坊間還繼續刊印這些書籍,而讀者也願意購買,朝廷實際上難以阻止這些書籍的流通。從清代乾隆皇帝留下的豐富「文字獄」史料,就能清楚看出朝廷失去對民間書籍貿易的掌控,已經到了什麼樣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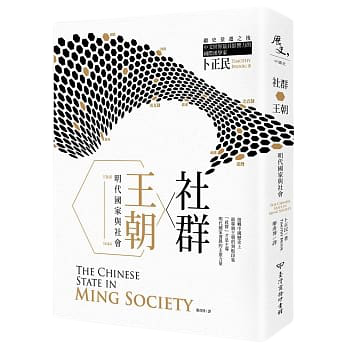
作者透過原本安靜地躺在史料裡的歷史事件,論述地方社會在地圖繪製、農業生產、出版貿易等方面與國家政令的拉扯,讓我們重新理解明代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