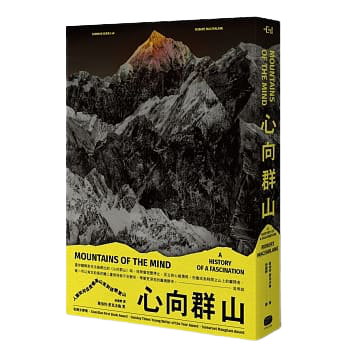在十九世紀這一百年間,湧向阿爾卑斯山和其他山岳的旅客日漸增加,死亡率也升高了。反對登山的聲浪從一開始就沒斷過,例如莫瑞就在瑞士導覽《手冊》中宣判攀登白朗峰的人「心智不健全」。不過這類警告大部分都無人在意,還是有越來越多人誤蹈布爾渥利頓(Edward Bulwer-Lytton)稱之為「 突如其來的危險」 中, 包括雪簷崩塌、意外落石和雪崩之類。
在羅斯金寫信給父親提及危險對有助於提升道德的兩年後,也就是 1865 年,馬特洪峰發生了一場著名山難,登山運動的危險被宣揚到駭人聽聞的程度。當時三個英國人(一位勳爵、一位牧師和一個劍橋的年輕學生)及一位瑞士嚮導在創下首登紀錄開始下山,途中從一千兩百公尺高的陡峭山壁墜落到下面的冰河。另外三位同行的登山客倖免於難,原因是他們和墜落隊友之間的繩索斷了。
救難隊到達冰河後,發現三具屍體赤裸殘缺。死者所穿的衣物在墜落過程中被扯掉。瑞士嚮導柯洛茲一半的顱骨都沒了,所戴的念珠深深嵌進他下顎的肉裡,救難隊不得不用摺疊小刀挖下來。至於道格拉斯這位勳爵, 現場除了一隻靴子、一條皮帶、一副手套和一管外套袖子之外,屍骨無存。

這場馬特洪峰山難傳開後,登山活動的黃金時代蒙上了黑影。尤其是在英國,國民對這樣明顯的白費性命既恐懼又著迷。不列顛貴族的藍血居然灑在追求高海拔上,許多人因此理所當然認為未來還有更多血要流。
狄更斯偏好端坐家中神遊北極,認為那樣付出心血才明智, 在他看來登山根本荒唐可笑, 於是在倫敦城到處鼓吹他的觀點。他毫不同情地吼道:「自吹自擂!爬到那樣的高度……對科學進步的貢獻,就跟一群年輕紳士跨坐在聯合王國所有大教堂尖塔頂的風見雞上一樣多。」
當時的幾份報紙果然也像風見雞,不過幾個月前還極力讚揚登山客的勇敢無懼,現在風向變了就改口憂心地質問英國人為何如此醉心於「走向深不可測有去無回的深淵」,或者乾脆譴責登山,斥之為「墮落的品味」。
社會大眾對那些殞落的生命倒是著迷多過於恐懼,毫不意外對山難細節表現出冷酷的興趣。而且, 對許多人來說, 死在山上的行為顯得高貴莊嚴。巴特勒(A. G. Butler)為幾位墜亡者寫了一篇輓歌,把他們捧成半神的地位,並把登山活動比喻為宇宙戰役:「他們力抗大自然,就像往日力抗諸神,/巨人泰坦;也如泰坦般墜落/從他們寄予希望的峰頂一落而下……」
別管死亡那些慘不忍睹的細節了(毫無摩擦直直墜落那恐怖的幾秒鐘,骨頭與器官在衝擊下變成一團膠狀物),在巴特勒的詩句中,墜亡者的命運轉變成先祖的壯舉。登山不只是狄更斯所譴責的那種學生笑鬧作戲的昇華,而是史詩事蹟:迎戰所有敵人中最頑強的精銳,也就是大自然,為此冒上任何風險都在所不惜。
馬特洪峰山難是登山冒險史上的關鍵時刻。如果當時不以為然的意見蔓延開來,變成社會的正統意見,那登山活動也許就不會像後來那樣蓬勃發展。不過最後流傳至今的,終究是巴特勒誇張的盛讚,而不是狄更斯的輕蔑鄙視。
登山活動日漸風行,連不爬山的社會大眾也越來越迷戀山岳與冒險,阿爾卑斯山區小村莊的墓地葬滿了絡繹不絕前來登山的外地客。懷伯爾這位山難倖存者後來為馬特洪峰山難和登山活動撰寫了一則墓誌銘:「想爬就去爬,但要記住,如果沒有謹慎小心,勇氣和力量都會化為烏有, 瞬間的疏忽大意會毀掉一生的幸福。做任何事都不要匆忙, 每一步都要看清楚,從一開始就想好最後可能會如何收場。」懷伯爾遵照自己的指示,度過長長的暴躁人生,許多人都沒他那麼謹慎或幸運。
人在山上有許多種死法:凍死、摔死、餓死、累死,死於雪崩、落石、落冰,以及高山症這種無形攻擊引發的腦水腫或肺水腫。當然,墜落永遠都可能發生。地心引力永遠不會忘記或者疏忽職守。法國作家克勞岱爾(Paul Claudel)說得很好,我們沒有翅膀可飛,但始終有足夠的力量墜落。
如今每一年都有幾百人在世界各地的山區遇難死亡,還有幾千人受傷。歷來光是白朗峰就奪走 1000 條人命,馬特洪峰 500 人,聖母峰大約 170 人,K2(喬戈里峰)100 人,艾格峰北壁 60 人。1985 年,光是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區就有接近兩百人死亡。
我在世界各地都看過山難死者。他們集體葬在山區小城的墓地或基地營的臨時公墓裡。在高山上,死者的遺體常常無法運下山,或甚至連遺體都找不到,所以很多死者只以物品或象徵代替:用螺絲把名牌整齊地釘到岩石表面、名字刻在巨礫上、石頭或木材粗略做成的十字架、玻璃紙包起的花束,還有一貫的悼詞與之相伴,這些悼詞頻頻執勤,且每次值勤時的力道及哀切都不曾或減:此處躺著……於此處墜落……紀念……所有壯志未酬的生命。

對於山難死者,我們很容易惋惜或頌揚。但應該要記住的(常常被遺忘),是死者拋下的人。那些父母、子女、丈夫、妻子和夥伴,都把所愛的人輸給了山。所有裂了一塊有待補回的生命。經常上山冒巨大風險的人,應該被當成極度自私,或不憐惜愛著他們的人。
我最近在一場酒會上遇到一位女士,她的表弟在前一年墜落身亡。她對此感到憤怒又困惑。為什麼他非得爬山不可?她開口問我,但並不想得到答案。為什麼他不能就去打網球,或者釣魚呢?讓她更憤怒的是死者的弟弟還繼續在爬山。
她說,她的姨母和姨丈失去一個兒子已經夠淒涼,可是另一個兒子卻還繼續投入讓他哥哥喪命的消遣。或者,至少一星期前還在登山,結果摔下山跌斷兩條腿。她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很高興,她說,因為她猜想他從此就不會再爬山了吧,這樣他的命就保住了,沒辦法再那麼自私了,她餘怒未消地咬緊牙關嘶聲說道。我後來聽說,他雙腿恢復了,石膏拆除不到一個月,就又上山了。
遇到這樣的情形, 難免讓人覺得是某種邪術或催眠術在作祟, 登山之愛變成了某種類似洗腦的狀態。這是登山活動黑暗面的一個例證,提醒人們登山潛在的高昂代價。不可否認,人沒有必要把自己的性命賭在山坡上或崖壁上。登山並非天命,不一定得發生在一個人身上。
現在我充分體認到, 死在山上並沒有什麼內在的高貴可言,反而有種令人深惡痛絕的浪費。我大致上已經不再冒險。需要綁繩索以策安全的路線, 我已經不太爬了。我發現,待在高山上而且冒的險比,隨便說,在城市裡過馬路更小,是絕對有可能的。而且我現在也更容易害怕,恐懼的門檻已經大幅降低。那種血脈賁張、令人反胃、隱約激發性欲的真實恐懼,近來會更快控制住我。五年前我會高高興興沿著懸崖邊緣走,現在則會敬而遠之。[1]
像大多數登山客一樣,現在對我來說,高山的吸引力更多源自美麗而非艱險、源自享受而非恐懼、源自驚歎而非痛苦,以及,源自活著而非死去。
然而事實是, 很多人仍舊禁不住誘惑而到山上冒險, 仍舊死於山間。法國境內的霞慕尼可能是登山愛好者人心目中最偉大的聖地,是我所知道僅有的一個旗杆上裝著鋼釘倒刺以免有人攀爬的地方。那是人口密集的小鎮,公寓、教堂和酒吧全擠在阿爾卑斯山區的一道峽谷裡。
看到小鎮坐落的位置總是讓我驚訝。從日內瓦陡急的山路蜿蜒而上,你不會想到那裡還有足夠的平地可以建一棟房子,更不用說是小鎮了。可是居然就有這麼一個小鎮,就位於山谷之中。鎮上四面八方都是岩石斜坡,沾上冰河水,把人的視線帶往白朗峰閃閃發光的銀色峰頂,以及聳立於每一道天際線上的鐵紅色岩石尖頂。
霞慕尼每年夏天的登山季中, 平均每天都有一人死亡。他們無聲無息地死去,不會有死者的朋友在酒吧紅著眼睛緊盯著某些空位,也不會有氣喘吁吁在炎熱的街道上呆呆走著一臉哀戚的父母。唯一的線索是小鎮上空縱橫交錯的救援直升機螺旋槳發出的轟隆聲。每回有直升機飛越, 酒吧的人都會抬起頭來, 簡略判斷一下是要往哪邊飛。
有一年春季, 我在傑昂冰河(Glacier du Géant)上健行。那是霞慕尼東南面山間的一座高海拔冰斗, 分布在法義交界。越過這座冰斗, 你就從一個國家走到另一個國家, 寬度差不多有八公里。沿途你會穿過寬闊到足以容納一整排房子的冰隙。望進去,你能看到冰河的橫切面:一層層多彩的冰,靠近表面的是白色,往下是漸層的鈷藍色、深藍色,有時是海綠色。這些冰隙底部的冰層是由幾世紀前的降雪構成。
在你周遭, 在這片耀眼冰河之外的, 就是白朗峰山脈有名的尖峰, 黃褐色的岩塔與岩尖, 上千公尺高聳入雲。在晴朗的天氣裡, 冰斗的配色, 紅岩、藍天、白冰,像三原色本身一樣明亮清晰。
這些尖峰大部分都有名字,有的叫「大修士」(Le Grand Capucin), 罩著棕色岩袍, 嚴守沉默的修道紀律。還有「 巨人牙」 (La Dent du Géant),斜斜向上,像根染上咖啡鹼色的犬牙,或者說是兩百公尺高的巨人牙齒。人們會攀上這些尖峰。沿著冰河走,你常會看到上千公尺的高處,岩壁的裂縫裡插著一個小紅點或小白點。

那天我們從義大利橫越冰斗到法國。才剛開始橫越,我就發現離路跡九十公尺左右,好像有叢耐寒的野花從冰河裡冒出來。這似乎不大可能,那裡沒有土壤供花朵生長,只有冰。我走幾步過去,想看個究竟。
那是一小球綠色的黏土或者橡皮泥,約拳頭大,一半埋在冰裡,上面插了十二枝綢緞花,纏在短短的鐵絲花莖上。花瓣的緞帶原來應該很鮮豔,但經歷風吹日曬,所有花朵都變成了深棕色。有張塑膠夾小卡片吊在其中一根花莖上,像產科醫院裡嬰兒戴的那種身分牌。我用冰斧斧尖輕推卡片。濕氣已經滲入塑膠夾,把墨水暈開了,但是還能辨識出幾個模糊的法文字跡:雪莉……死亡……山……永別。
我納悶她發生了什麼事。是如何死的,在哪裡。是誰在哀悼她。是不是全家人都來到這裡為她種下了這小小的花園。之後我走回原來路徑,繼續朝法國前進。
我們順利越過冰河。兩天後我回到家,答錄機裡有某個認識的人死於山難的消息在等著我。他當時剛攻上本尼維斯峰(Ben Nevis),正在峰頂較為平坦的地面收繩,一個異乎尋常的小小雪崩把他從懸崖邊緣推回到他才剛爬上來的 300 公尺之下。他才 23 歲。一架蘇格蘭山岳搜救隊的焦黃色直升機把他的遺體從奧塔穆林(Allt a’ Mhuilinn)運出來, 那處峽谷一直延伸到本尼維斯峰和卡恩莫迪格峰(Carn Mor Dearg)包夾的馬蹄形花崗岩上。
聽完留言, 我手持電話站在那兒, 前額抵在涼涼的牆上。自從某年除夕夜我們一起去爬愛丁堡的峭壁「 亞瑟座」(Arthur’s Seat)之後, 我就沒再見過他。那回我們喝醉了,笑著走在愛丁堡下雪的街道上,看著雪花飄進每一盞街燈照下來的橘色光錐中。在那之前,我們從「亞瑟座」陡峭的那一面挺進,花了大概一小時,有時直接爬上結冰的崖壁,有時也試圖橫越。我還記得當時我們肩並肩,離地有三公尺,從冰冷的岩石上向外傾斜,去尋找下一個抓點,由於地心引力的作用,我們的頭髮整束向後立起。
[1]我最近才發現自己的膽小程度,還無法與馬塞爾・普魯斯特相提並論,他曾經公開說過,光是從凡爾賽旅行到巴黎,就飽受登高暈眩與高山症的混合折磨,凡爾賽只比巴黎高 83 公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