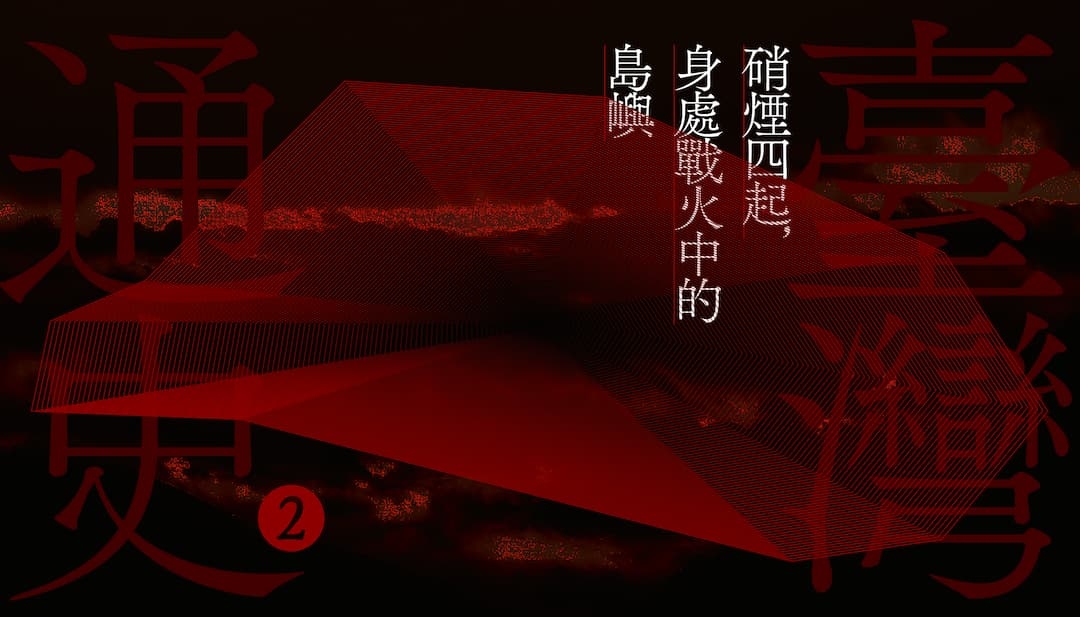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後,以歐洲為首的西方工業國家基於原料與市場需求,逐漸將全球整合為一體,在國際頻繁的交流下,不符合近代國家體制的政治秩序都將面臨威脅。
1860 年臺灣開港通商後,開始遭遇的一系列國際紛爭,便是清朝邊疆政策與近代國家概念之間的衝突而產生。1867 年日本明治維新後,在東亞海域的紛爭,更增加了一場日本想要直接挑戰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的行動,那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的牡丹社事件。
東亞政治秩序下的牡丹社事件
近代國家的衝突得從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所打造的朝貢/冊封體系談起。朝貢體系從明代開始逐步完善,依照與中國朝廷的親疏關係,將其周邊的國家劃分為數個等級,著名的例子有朝鮮與琉球王國。這些國家間等級上的親疏關係,與其延伸的貿易活動,共同建立了東亞的政治與經濟秩序。日本位於此體系較為邊緣的位置,在戰國時代長達上百年的動亂後,強大的諸侯德川氏以「幕藩(幕府、藩屬)體制」,建立起長達兩百年穩定的江戶幕府時代。江戶初期的 1609 年,位於日本最南端九州的諸侯薩摩藩島津氏,出兵征服了琉球王國、控制其內政,但仍維持了琉球王國與明朝朝廷的朝貢關係,這種同時受日本控制、又朝貢於明朝的「兩屬」狀態一直延續到日後的清廷,一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受到近代國家挑戰後,問題才開始浮現。
1867 年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政府,想要進入西方的近代國家體制,積極尋求機會挑戰既有的朝貢體系,藉此改善自身的國際地位。往後數十年的一連串外交與軍事行動均是圍繞著此目標而來。為了確立國界、終結琉球兩屬問題,日本外務省選擇 1871 年的琉球漂流民遇難事件,以「懲罰兇番」為理由出兵臺灣,但主要的「戰場」仍是雙方在北京總理衙外交折衝,使琉球王國正式成為日本的領土。
不過若仔細探究,其實遠自十七世紀的薩摩藩島津氏,便有攻占臺灣的企圖;再觀察牡丹社事件中均是出身於鹿兒島(即明治維新後薩摩地區)的日軍,不顧外務省終止行動的命令而「暴走」出兵、設立「臺灣蕃地事務局」等事,均表示著日本選擇臺灣做為解決外交紛爭的地點,並不是件偶然發生的事情,而是有長期潛伏的野心。日本欲改變琉球的兩屬狀況,加上思想淵源中的對於經略臺灣的野心,促使了牡丹社事件的發生。
邊疆政策下的問題
上述國際紛爭的導火線,為清朝邊疆臺灣的「番界」定位問題。清朝在十七世紀的一系列擴張行動中,為了東南沿海的安全考量,首次將臺灣併入清朝版圖。臺灣過去所具有的海洋貿易與移民特質,為清朝所首要壓抑的對象。在有限成本的考量下,清朝頒布了一系列限制移民的措施,如族群分而治之、移民申請許可制等,其中最核心的便是「番界」政策。
在十八世紀逐漸定型的番界政策,其核心精神,在於劃定漢人移民的界線,禁止漢人移民前往山區拓墾,成為秩序不穩定的因子。其延伸的族群政策,為利用界外的「生番」(指未負擔徭役的原住民)的獵首習俗,嚇阻漢人移民;界內則積極利用積極運用、部署「熟番」(在清朝秩序下負擔勞役的原住民)作為防範漢人反抗的政策。此政策形塑了臺灣往後 150 年的特殊樣貌。
1860 年代臺灣開港通商後,由於番界政策造成的一系列關於近代國家的權責、領土問題始浮現。番界之外占臺灣三分之二的土地是否為近代國家意義下的領土,成為必須迫切加以釐清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時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仙得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李仙得於 1872 年離開領事職務後轉往日本發展,並被日本外務省聘為外交顧問。過去七年在臺經驗,成為日本了解臺灣的一手資訊來源。他日後在日本所倡導的「番地無主論」,也成為日本出兵臺灣的理由。
牡丹社事件的來龍去脈
1867 年,發生在臺灣南端瑯嶠地區羅妹號事件,點燃了番界外海難漂流民上岸的救濟與責任歸屬問題,引起在外交場合與現場幾近爆發戰爭的衝突。美國駐廈門李仙得,最後與瑯嶠十八社代表卓杞篤達成協議,未來瑯嶠地區若有海難漂流民上岸,若未表示敵意,瑯嶠十八各社一律會加以救助,此為〈南岬之盟〉。但這看似和平落幕的協議,其實留著兩大未解決的餘音:首先,清廷並未正式回應、或是改變番界定位的問題,換句話說,〈南岬之盟〉的效力其實不被當時的國際政權所承認,這也是李仙得所認為的。其次,在瑯嶠十八社方面,卓杞篤雖然代表十八社與李仙得承諾,但效力是否遍及十八社內部,則仍是未知數。
1871 年 11 月,琉球王國宮古島的貴族,至首都首里城進貢後的歸途遭遇海難,倖存者漂流至八瑤灣(今屏東九棚)的海灘上岸後,因為文化、語言的隔閡,而與瑯嶠十八社北部的牡丹攻守同盟的高士佛社發生衝突,最後多數漂流民遇害。這是一則〈南岬之盟〉效力有限的例子。即使最後倖存的漂流民在後續清廷既有的救濟程序中已經返回琉球,但新成立的日本明治政府注意到此事件,於是在數年的準備與調查之後(即使最後外務省取消出兵行動),於 1874 年 5 月正式出兵入侵臺灣瑯嶠地區。
日軍於界外瑯嶠駐軍長達半年的時間,採取避免與清軍衝突的方針,雙方有默契地在番界邊境枋寮一線對峙,以作為雙方在北京總理衙門談判上的籌碼;在瑯嶠方面,日軍實際的軍事行動,僅有 5 月 22 日的石門之役,與 6 月初攻下牡丹社群的戰役。在 5 月 22 日的石門之役,牡丹攻守同盟領袖、牡丹社頭目阿祿古父子,於四重溪天險石門抗拒日軍而陣亡,但牡丹社群仍拒絕投降。6 月 1 日至 6 月 4 日,日軍憑著優勢兵力,征服並焚毀了四重溪流域的牡丹社群。
日本畫家月岡芳年的浮世繪,紀錄著牡丹社事件中的石門之役(Source:wikipedia)
受到嚴重打擊的牡丹社群於七月正式向日軍投降。到九月的這段時間,恆春半島各地的番社均前來「歸順」日軍,與日軍結盟對象甚至遠達花蓮後山的番社。日軍在番界外儼然建立起以大本營為中心的秩序,對比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征服最大對手麻豆社後立足於安平的過程,竟有些許類似。以上這個模式在日後清廷二十年「開山撫番」、日本殖民統治初期將重複上演。
作為主戰場北京的總理衙門,清日雙方代表在該年十月簽訂了〈北京專約〉,清廷補償日軍出兵行動的受損,並承認日本入侵瑯嶠為「保民義舉」,具有一定的正當性,形同在外交條款中放棄了長達數百年的朝貢體系下與琉球的宗藩關係。日本在外交上取得預定的目標後,便下令撤軍,結束了日軍於瑯嶠長達半年的入侵行動,並永久改變的東亞歷史的進程。
事件之後,什麼事情被改變了?
牡丹社事件為臺灣開港通商後一連串國際風波引爆的轉捩點,各方政權在各自的實踐中積極盤算著,被視為東亞政治秩序之改變也不為過。
臺灣的部分,清廷為避免落人口實,正式取消施行長達 150 年的番界政策,指派欽差大臣沈葆楨的「開山撫番」,對於山區改採開闢道路、積極籠絡原住民的方式,並在番界以外設立新的行政區畫如恆春縣、卑南廳等,希望能徹底控制掌控山區資源。連橫也以「臺灣局面一變」形容牡丹社事件後的清廷應對措施。但即使清廷往後二十年的銳意經營,收取的成效依然有限,番界外的原住民,如恆春的瑯嶠十八社依然保有相當大的自主性,一直到日本殖民初期的五年理蕃計畫後,國家才能正式全面管制社會與經濟的各個層面。
日本則首次在挑戰朝貢體制的行動中獲勝,終結了琉球兩屬問題,並開啟了「軍人暴走」的模式:即軍人先行,外交追認的狀況,被視為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原形。事件後,日本持續東亞國家間挑戰朝貢體系的秩序,如朝鮮的藩屬問題,根本改變了東亞間的政治情勢。此外,這八個月的「臺灣經驗」,如當時的軍官佐久間左馬太、水野遵,以及這段時間的第一手調查,讓日後臺灣在成為日本殖民地的過程中發揮顯著的作用。
在琉球王國的部份,琉球被迫接受日本的「琉球處分」,在短時間內從獨立的王國、經歷「廢藩制縣」的改組後變成日本的地方行政區劃沖繩縣。原本為獨立王國的琉球,被迫成為日本領土後,但卻在日後承接了日本對外擴張的苦果,如今美軍基地問題依然在沖繩的政治議題中迴盪著。
在偶然的時間點下,恆春半島周邊生意盎然的珊瑚礁海岸下的洶湧洋流,使得不同國度的人們因海難、或是包著各自的期待匯聚於此,這些人們又讓距離更遙遠的國度,如瑯嶠十八社、琉球王國、美國、清國、日本等,彼此牽連在一起,永遠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延伸閱讀:
1.《臺灣通史─原文 +白話文注譯》
連橫著,蔡振豐 、 張崑將等譯,點此購買
2.《臺灣通史》
連橫著,點此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