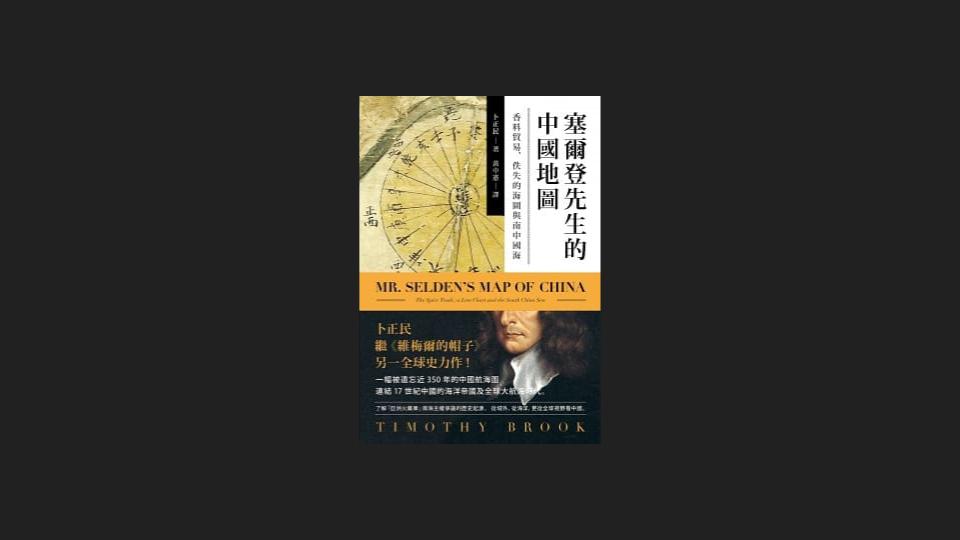「無湘不成軍」等語,流傳久矣。
研究近代中國史者,鮮有不留意「湖南」作為地理/政治單位之人。清季太平天國變起,曾國藩、左宗棠率湘軍轉戰各地,有中興再造清廷勳功;三湘子弟因此遍佈帝國,包括吾土臺灣。革命風潮繼起,湖南人士如黃興、宋教仁輩,更是革命陣營的中堅。民國肇建後,湖南依舊是全國知識界的焦點──儘管這部份有些不幸的色彩。
由於政局動盪,南北軍閥混戰,常使湖南陷於戰禍。蓋湖南位處衝要,北軍常欲得湘以控西南,西南亦欲得湘以制北軍,故戰火彼落此起,而有志之士愈加奮發。民初「聯省自治」運動重心在湖南,國民革命北伐戰爭的導火線在湖南(唐生智與趙恆錫之爭),共產革命在農村的燎原之火也起於湖南[1]。這都不是偶然。
意識到湖南的重要性是一回事,而要將湖南當作獨立單位來分析,又是另一回事。
晚近史學研究重視「地方」,並不拘於傳統史學的「中央」視野。也因此,相當數量以湖南為分析對象的歷史論著,在近十數年紛紛問世,例如吾友羅皓星先生的「湖南新政(1895-1898)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研究。
但即使如此,近代中國史書寫的大敘述(grand narrative),係以中國國族主義為核心;多數論者一般傾向於視湖南為中國研究的案例,而非特例,更鮮少用「認同」的角度來單獨看待湖南。美國學者裴士鋒(Stephen R. Platt)的《湖南人與現代中國》(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則是迴異中國國族主義主流觀點的作品,抑且在西方學界,也不能算是典範性的操作方式(儘管將來會越來越常見)。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
這不是第一本出自西方學者之手的有關湖南的書,卻是第一本避免把湖南當成個案研究(case study)的書。已有人寫出把湖南當作近代中國縮影的出色著作,而要抓到整個中國的趨勢,這是較容易辦到的研究路徑。但就本書的目標來說,湖南不是中國的縮影,就像中國不是亞洲的縮影,湖南就是湖南。
這種以湖南作「整體」的分析取徑,是否恰當,當然是讀者可以討論的。
《湖南人與現代中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前半部分析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1619-1692,亦為湘人)的著述,在晚清如何重新被發掘、運用、以及復興。特別是,晚清湖南知識分子透過重新解讀王夫之著作,經過數代的歲月,進一步將王夫之轉變為令人仰慕的現代湖南精神象徵。當然,王夫之作為湖南的精神象徵,不是抽象且不變的,而是有所待(contingent)且處於動態變化的,必須擺在人的時空情境(human context)裡去瞭解。
例如,王夫之著作裡的「夷夏之防」敘述,在道光年間刊行的《船山遺書》中被刻意隱去,但並非毫無留存蛛絲馬跡;其後曾國藩、曾國荃等清代「中興名臣」著手重刊,心態上似乎是耐人尋味。終於,二十世紀後眾多青年湖南士子,對王夫之學術作出迴異鄉賢前輩的解讀,視之為激進排滿觀點的靈感泉源。
在裴士鋒看來,欲適切理解湖南知識分子的激進化過程,必須用獨立的眼光,不能單純視之為中國國族主義的切片。傳統的中國近代史認識認為,儒家忠君愛國的觀念自然而然轉化為對中國大一統的想望,於是順理成章地,中國知識分子無一不懷抱著中國一統的夢想。

然而,裴士鋒強調,前揭說法乃是一種歷史學家的刻意構造,用意在試圖以近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形式保住古老帝國(empire)版圖;事實上,在大清帝國趨於崩解之際,許多重要的湖南改革派只把湖南當成首要效忠對象,甚至提出「湖南人應該讓中國步羅馬帝國之後塵消失於歷史舞臺,湖南本身則要成為法國或英國之類的國家」的一類說法。不過,裴書於尾聲處仍不得不指出,以「湖南」為認同單位的政治運動,隨著 1920 年代初期聯省自治運動失敗、地方軍人藉自治之名行割據之實,難逃無疾而終的厄運。在這之後,湖南人依舊扮演政治上的重要角色(書中所舉之例是毛澤東),但情勢已大有不同。
無庸置疑地,個別史料的解讀、詮釋姑置不論,斐書的「分離主義」觀點帶有相當爭議性。汪榮祖教授曾批判該書,立論似應著眼於此。不過,筆者認為,傳統基於大中國國族主義的歷史敘事,確實存在很多可商榷之處。至少,湖南的鄰省廣東,亦有相對應的分離主義現象。
1911 年辛亥革命起,廣東由革命派的胡漢民出任都督,宣告獨立。一般看來,這個獨立舉動並不具備文化認同的意涵,更沒有脫離「中國」之意。但其實,當時由前清宿將劉永福(也是過去教科書上的中華國族英雄之一)出任的廣東民團總長,曾發布安民通告,略稱:「夫吾粵,東接閩,西連桂,北枕五嶺,南濱大洋,風俗言語嗜好與中原異,固天然獨立國也。秦之趙陀,隋之馮盎、鄧文進、元之何真,接乘變亂時代,崛起一方,安輯人民,鞏衛疆圉。今兵力雄厚,獨立之局告成矣」,又語及「廣東省,廣東人之廣東,斯言聞之熟矣。」[2]。類似分離主義言論,在當時似乎並不稀見,卻鮮少於今天的主流中國歷史敘事出現。從某個角度說,將來若陸續有其它「□□人與現代中國」的書著問世,並不會令人詫異吧。

或許有人認為,正如前揭廣東獨立文告提到的「乘變亂時代,崛起一方」等語;每逢中國朝代鼎革、天下撥亂之際,出現獨立性的「地方」政權或意識,並非怪事,而且不會危及中國大一統的思想。另一方面,晚近中國知識份子亦不乏深刻反思「統一」/「分裂」者,例如葛劍雄認為分裂時代的「地方政權」往往帶來活潑的思想、更平衡的區域發展[3]。就此而言,閻錫山治下的山西、陳濟棠治下的廣東等地區,也會是很好的例子。
可是,多數分析「地方」政權或意識的書著,有意無意間常忽視粵人自稱「風俗言語嗜好與中原異」、湘人追求「成為法國或英國之類的國家」的一類看法,後者被認為是隱約帶有解構中華國族想像共同體的意味,不再是單純的「地方觀念」。斐書的精采之處,正是用連慣性的鋪陳,強烈對比湘人「省」與「國」的認同差異,並以新穎方式說明地方根源與民族意識的聯繫,有力地質疑「聲稱中國從帝國走向民族國家乃勢所必然」的國族主義敘述。
不過,筆者不贊同以斐士鋒的觀點來作為解構中國國族主義的工具。事實上,全書最大的主要弱點就是在於,雖有力地挑戰傳統國族主義的敘事模式,卻無法令人信服地說明:作為政治認同單位的湖南,何以最終仍被「大中國」的認同所吸納。
特別是,全書的核心論證止於 1920 年代初期,並未觸及 1920 年代後諸多影響當代中國認同形塑的諸多重要事件,例如起於鄰省廣東的國民革命怒潮,以及中日戰爭的爆發。簡單說,這是一幅還缺很多拼圖圖塊的圖畫。其次,如果說「中國」是一種國族認同的想像,那麼作為認同單位的「湖南」未嘗不也如此。實際存在的認同單位可能更小,例如湘南、湘西。
抑或者,單位是介於省與國之間,例如「南」與「北」。當時,北洋軍隊駐防各省,權柄操之於督軍,兵士則盡為北方壯丁。南人(自然包括湖南)視之,謂其「等於滿州駐防」,民怨已積十餘年之久。及遇南北戰興,一般鄉民輒助「語音近似,而紀律較佳之南軍」。前揭南人「厭惡北軍之心理」,實有助於國民革命軍北伐初期進展甚大,但在黨派宣傳之下,被簡化為「民眾簞食壺漿迎革命軍」云云的革命神話,此為後話。不論認同單位是「中國」、「南方」、「湖南」或更小的地方區域,都還有待更多的考察。
總此而言,「中國」作為一個龐大的政治單位,在其疆界之內,確實存在地區性的飲食、方言和習俗的差異,這點應該是學界內外的共識。爭議是在於,一旦「政治上的地方主義」逐步發展,是否就會威脅到國家的凝聚力?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對廣西軍閥的研究便認為「桂系同時既是地方主義者,又是民族主義者」,兩個因素有衝突、互動,但最後是結合。這是一種解釋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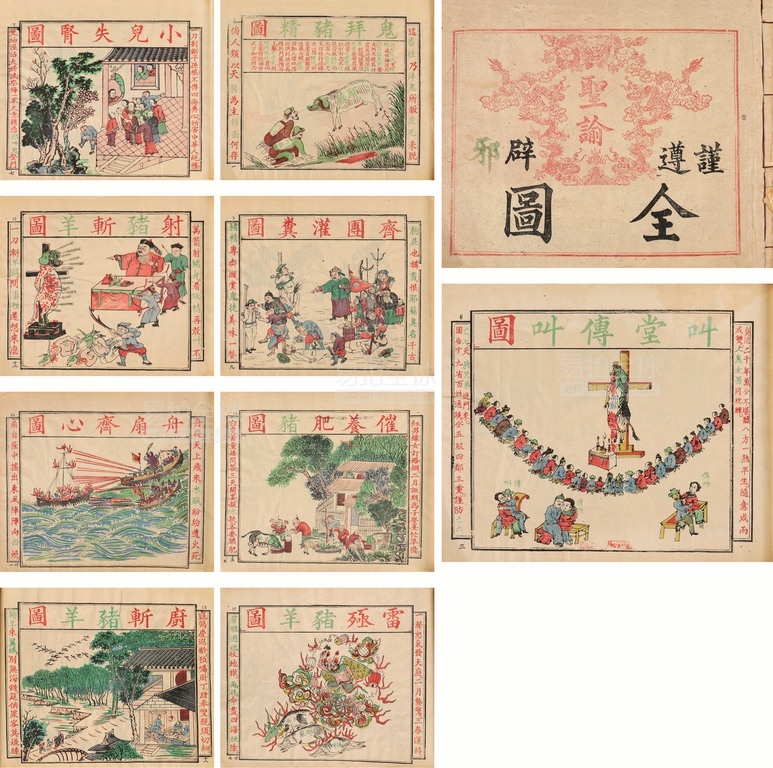
裴士鋒在《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中提出的是另一種解釋框架,試圖發掘被埋沒在「大中國」敘述中的湖南認同。其實,細究起來,如果意識到歷史學研究往往是對現狀的回顧,後一種取徑的採用,並不能取代前一種取徑的地位。不過,注意到湖南知識份子曾經洋溢湖南認同的一段歲月,已經足以提醒世人很多事物不是「勢所必然」。無論如何,值得研究者繼續探討、省察。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1] 參見湘人毛澤東 1927 年的著名〈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2] 羅香林輯校,《劉永福歷史草》,台北:正中書局,1969 增訂台三版,頁 290-292。
[3] 參見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增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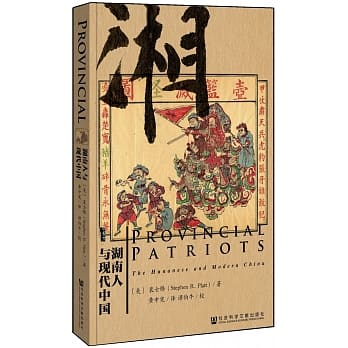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