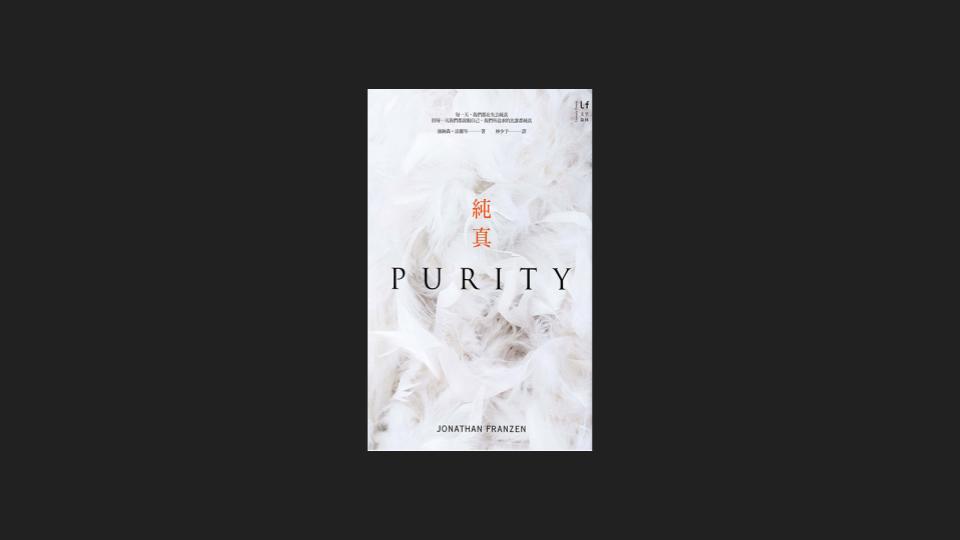回紐約之後,我們決定自己動手做西西里式的煎茄子與番茄義大利麵,由於實在美味,我們覺得應該每週吃兩次,也真的每週吃兩次,連吃了好幾個月。問題是,這道剛開始幾口就讓我覺得好吃、而且能夠全部吃完的美味,幾個月後,我卻覺得噁心,不是逐漸覺得噁心,而是突然、激烈,長時間覺得噁心。
我放下叉子說,我們得暫停一下,不能再吃煎茄子和番茄了,這是道完美、好吃的菜,不是它的問題,是我實在太常吃了,吃到現在覺得像在吃毒藥一樣。所以,我們停了一整個月沒有吃它,但安娜貝爾還是喜歡這道菜。一個非常暖和的六月晚上,我到家時,聞到她在煮這道菜的味道。
我的胃長嘆了一口氣。
我站在廚房門口說:「我們過頭了,我再也受不了了。」
安娜貝爾絕不會錯過任何語言的象徵,說:「湯姆,我不是茄子義大利麵。」
「我要出去一下,不然就真的會吐出來。」
她嚇了一跳,說:「好,但你晚一點會回來吧?」
「會,但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同意,我也一直在想這件事。」
「好,我晚點回來。」
我跑下五層樓梯,跑到 125 街地鐵站。我也不知道要跑去哪裡,也沒有熟到讓我能講心事的朋友,我只想脫身。
那年頭,有幾個衣著破爛的放克樂手,不定期會出現在 125 街站往下城方向的月台。貝斯手和吉他手每次都會在,偶爾缺席的鼓手出現時,總是帶著一套像是從垃圾箱翻出來的鼓,有時候那位鑲金牙、一身骯髒的亮片洋裝的歌手也會現身。這幾個人當中,只有歌手會跟觀眾互動,其他人完全沉溺在自己的痛苦回憶中,靠音樂短暫喘息。吉他手汗流浹背,卻能亳不受地鐵經過時發出的隆隆聲干擾,彈出一段段精采的即興樂章。
那天晚上只來了三個樂手。地上打開的吉他盒裡,已經有一些一元鈔票,我丟了一張一元鈔票進去,用白人在哈林區必須表現的尊重,退到月台另一頭。後來我一直在找他們演奏的那首歌,卻始終找不到,也許那是他們自己創作的歌,從未錄音發行。那是首簡單的小七合弦反覆節奏,說的是在無法治癒的傷痛中,一則美麗的故事。
我還記得他們表演了二十分鐘,或者半小時,時間很長,普通車與快車都過了好幾班。最後,終於出現由上城與下城同時吹起的幾股風結合而成的完美大風,一股強大、潮濕、還帶著尿騷味的風從月台這一頭吹過去,吹回來,再吹過去。樂隊演奏時,吉他盒裡面一張張一元鈔票往上飄,像秋天的落葉,隨著風從月台這一頭吹向另一頭,紙鈔到處翻滾滑行。月台上每個人都知道,這是完美的美麗,完美的傷痛,沒有人彎腰撿錢。

我想起我的安娜貝爾獨自一人在公寓裡受苦,我看到我的生活。我往回走,從樓梯上樓。
她就站在大門口,似乎一直在那裡等我。一看到我她就說:「你能幫我嗎?我知道有些地方一定得改,但沒有你,我一個人做不到。你能不能幫我看看,然後告訴我,我忽略了什麼?」
我說:「只要別再叫我吃煎茄子。」
「湯姆,我是說真的,我需要你幫忙。」
我答應幫她忙。我們走進她的工作室,這房間長久以來都是我的禁地。她很不好意思地拿出一些短片給我看。一捲是她拍左大腿上某個網格曝光不足的黑白特寫,經過人為加工,製造出黑暗海洋湧浪的印象;另一捲是膝蓋獨白,雖然影音同步有些許瑕疵,但內容非常好笑;還有一捲是將地鐵月台的影片與她大腳趾的影片剪接成一段故事,慘白如死屍的大腳趾還掛一個寫著她名字的吊牌,暗示她想跳到地鐵軌道上被火車撞死。這些短片都讓我印象深刻,接著,她打開筆記本讓我看,我更覺得振奮,心頭湧出一陣暖意。
她一直將這些筆記本當成絕對隱私,現在願意讓我翻閱,代表她已經一籌莫展。我以為裡面是漂亮的字體和分鏡圖,結果是一份折磨日記。每一則記事都以當天的待辦事項開始,字跡逐漸演化成難以辨認的自我診斷;接著,她跳到下一張空白頁,將身體各部位的拍攝計畫做成表格,但只有前幾個表格裡面有內容;然後,她用潦草的字跡修改這些內容,劃掉,再潦草地在頁面邊緣空白的地方寫上修改內容,並畫線將相關內容連起來,在關鍵的想法下面畫三條線;然後,她把全部內容畫上一個大大的、生氣的 X。
她說:「我知道這看起來不像筆記,但裡面有些想法其實很不錯。有些地方看起來被劃掉了,但我並沒有放棄,它們其實都還在。但是,那些地方如果不劃掉,我的壓力就太大了。我現在一定要從頭到尾再看一遍這些筆記,」—筆記至少有四十本—「我在腦袋裡想一遍,然後訂出明確的計畫。但是東西實在太多。我沒有發神經,我只是在找一個壓力不那麼大的方式,把這些想法整理清楚。」
我相信她。她很聰明,想法也很精采。但是,一頁頁翻完這些筆記以後,我看得出來,她不可能完成這個創作計畫。長久以來,我一直覺得她無所不能,但她其實還不夠堅強。我覺得,因為我沒有早一點出手幫忙,現在就必須扛起責任。
即使我厭惡這段婚姻已經到了想吐的程度,我還是不能離開,既然我讓她陷入困境,我就必須幫忙她脫離。我本來希望我能靠這段婚姻擺脫罪惡感,沒想到,我的罪惡感卻愈來愈深重。
在人類情感特質中,罪惡感一定是最可怕的一種。
我當時為了減輕罪惡感所做的決定—就是繼續維持這段婚姻—正是後來,也就是婚姻結束後,我覺得罪惡感最深重的事情。義大利麵和煎茄子晚餐事件之後,她第一次意識到我可能會離開她,便開始提起我和她可以生個小女孩(她從沒想過要個男孩)的時間,也就是十八個月後。
這個想法,一方面是替她的拍攝工作進展到肚子以上訂個目標與截止日期,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不讓我離開所出現的實際想法,我們不能永遠拖延懷孕。
我看得出來,我們這時可能就是需要一個嬰兒。
寶寶或許能拯救我們,但我也看得出來,只要她的創作沒有完成,照顧嬰兒的大部分工作都會落在我頭上。所以,只要她一講到養育孩子的事情,我就把話題轉到她的創作計畫。我究竟是希望她加緊腳步,好分擔照顧嬰兒的工作,還是希望她一切都好,以便我能放心和她離婚。說實話,我真的不記得了。但我記得 我一想到這件事,就會想起煎茄子的噁心。如果我為了腸胃健康著想而跟她分手,她可能還有時間找別人生個小孩。
「我有個大膽的建議。」義大利麵事件後第二天早上,我在她的工作室說:「妳把網格放大十倍。我可以幫妳全部重新規劃,把所有網格畫出來,這樣妳就不必把所有事情都放在腦袋裡。然後,花個兩年時間完工。就這樣。」
她不以為然地搖搖頭,說:「我不能做了一半才改變網格大小。」
「但是,如果網格放大十倍,只要兩個月就可以重新拍完一隻腳。至於那些不是身體部位的鏡頭,挑妳最喜歡的再剪接就好。」
「我不要丟掉八年的心血!」
我指了指那些已經沖洗、還沒打開、堆得像山一樣高的軟片盒,說:「妳的計畫根本沒完成啊,用什麼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完成。」
「你也知道,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完成一件事。」
「所以這可能是個好的開始,不是嗎?」
她說:「我有我的想法。我要你幫我,不是要你幫我丟掉八年的心血,是要你幫我整理已經有的想法。原來,請你幫忙是錯的。天啊!天啊!我真是個笨蛋。」
她懊惱不已,握起拳頭猛敲腦袋。我花了兩個小時,才安撫她平靜下來;再用一小時,檢討自己庸俗的審美修養,才哄住她不再生悶氣;接著,我花了三小時替她擬定一個粗略的完工時間表;最後,我用一個小時,把四十多本筆記中第一本上的重要想法,重新謄寫在一本新的筆記本上,我全部自己謄寫;然後,她運動三小時的時間到了。
此後一年,這種日子一再重複。為了替她排出鏡頭順序,我花了十小時弄出我認為可行的順序;然後,就在她運動時間快到時,她卻說,這種鏡頭編輯的方式看起來太新聞風格,不是她要的電影。我們只好再花一整天討論,由她告訴我她要的順序,一旦我無法理解她的邏輯,她就從頭到尾再解釋一次,就算我還是不懂,她的運動時間一到就完了。
我減少工作,放棄一次替《滾石》雜誌採訪杜卡吉斯選舉行程的機會。我經常在最後一分鐘取消約會,結果,我就像毒蟲一樣,朋友愈來愈少。早上起床時,我感覺不到一絲喜悅,連一個微小的喜悅粒子都沒有,只能感覺到對前一天沒解決的問題的厭惡。我們就像無法自拔的毒蟲,只求毒癮不要愈來愈重。這種生活日復一日,要不是我母親收到了死亡判決,恐怕還會繼續上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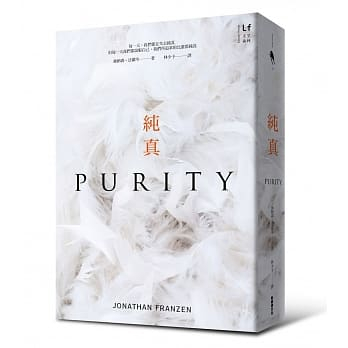
謀殺、集權、洩密網站
每個被揭開的真相,
都有隱藏難以啟齒的真實
純真曾經是我們美好的原貌,
如今卻成了我們最後的假面
法蘭岑從來不滿足於寫好看的小說,
他還要寫出一本讓當代人思索當代困境的小說。
繼《修正》《自由》得到最高推崇後,
挑戰無隱私網路時代的傑作。
他想探問:網路帶給我們實踐純真夢想的可能。
但我們面對正在發生的,
是美麗新世界,還是失去自我的美好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