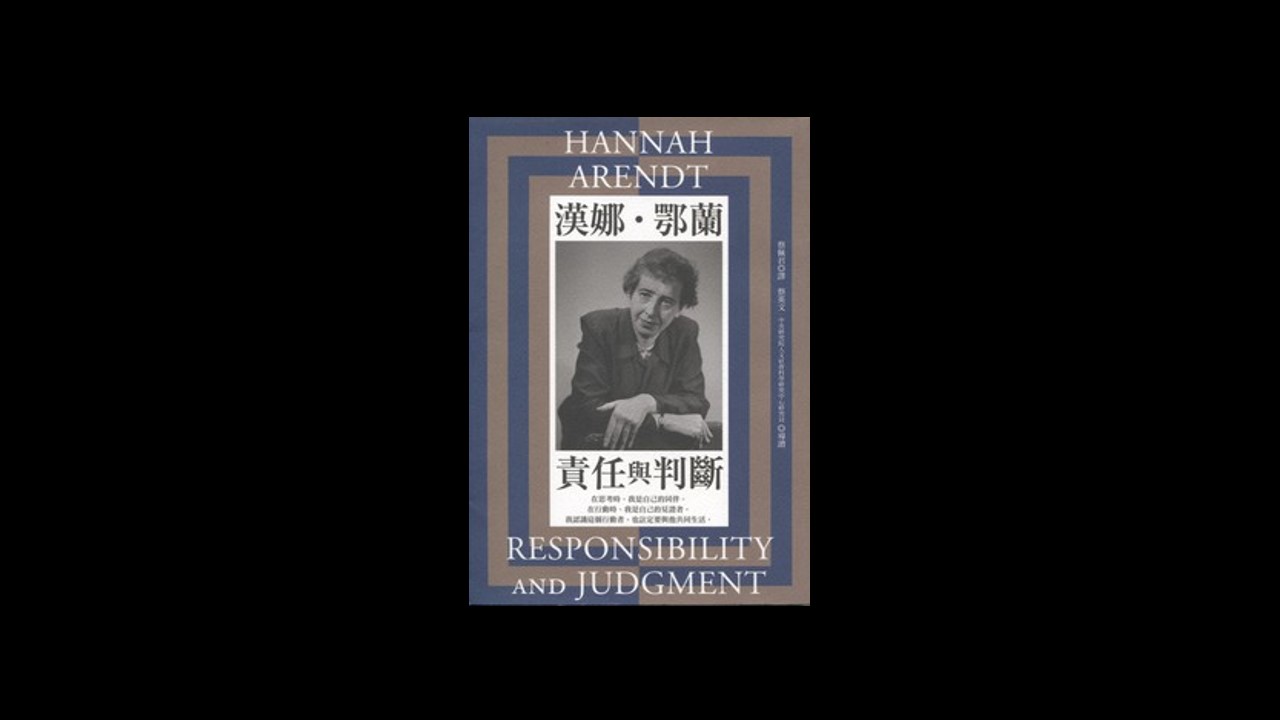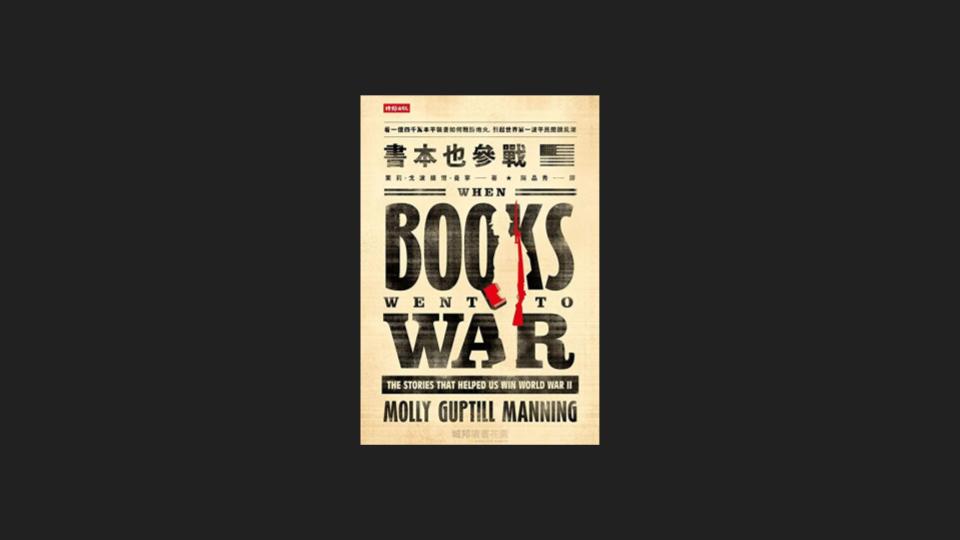前言:世紀大審與平庸之惡

1961 年 4 月,前納粹黨衛軍幹部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開始受審,知名尤太裔[1]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也到了現場。在觀察與報導過程結束後,鄂蘭樹敵無數,被許多尤太社群稱為叛徒,因她提出了一嶄新概念──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2]。
在一般的想像中,為惡者必有為惡的動機,否則不足以支撐他持續推動惡行。根據這種觀點,艾希曼長期負責最終解決方案(the final solution),想必有著強大的惡念,方使他得以持續將尤太人送往滅絕;對很多人而言,法庭上的艾希曼是裝瘋賣傻,企圖用「依法行政謝謝指教」這說詞掩蓋他的惡魔心腸。但鄂蘭認為這人其實就像小丑似的,並不抱持著人們想像中的「對尤太人的憎恨惡念」。鄂蘭的想法遭致許多批判,認為她企圖替艾希曼開脫。
對此鄂蘭並未公開回應,但她仍心繫著在耶路撒冷所見的現象 ─ 如果這般的罪惡不是由極端惡念所遭致,那會是什麼?我們又該如何面對它呢?對這些問題的思索不斷出現在她的文字與課堂講稿中。在她死後,弟子傑洛米.柯恩(Jerome Kohn)將之編輯成冊並於 2003 年出版,即目前這本《責任與判斷》。
平庸但不意味著無罪責
在審判過程中,艾希曼主張自己只是大機器中的小齒輪,一切都「依法行政謝謝指教」。事實上,抱持這想法的不只艾希曼,甚至是在整個德國都大為興盛。按這種思維,所有人都是邪惡殺人機器中的小齒輪。將這種想法推到極致而論,並沒有人真的造就了悲劇,所有人也因此都無罪責。
鄂蘭自然不接受這想法,在她看來,討論罪責就要放在行為者個人層面上來討論,不能隨意牽拖到這種大結構中迴避。因此,她十分贊同耶路撒冷的大審,該審判並未被那膚淺的齒輪理論迷惑,在《平庸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一書結尾可看到鄂蘭深表贊同的這段話:
對鄂蘭來說,艾希曼的確有責任。
但令人意外的是,鄂蘭並不是援引我們所熟知的「汝不應殺人」這般倫理法則來指責艾希曼。最終解決方案並不只是大量「殺人」之積累,而是企圖以單一的觀點去否定與消滅不符合其觀點的人群,直接消弭與毀滅了人類的多樣性,是一「反人類」(anti-humanist)罪。
再者,鄂蘭認為高舉倫理法則本身未能完全阻止罪惡。
我們平常總會認為,之所以能夠判斷是非對錯,是來自於特定的倫理道德法則,比如十誡的「汝不應殺人」。而要堅守善行而不為惡,就應服膺這些法則。但最可怕也正是這點。鄂蘭指出,倫理一詞的英文是 ethic,其字源是希臘文 Ethos,就是風俗習慣或習俗,而這些風俗可經由人為而改變。在納粹政權底下,最可怕的並不是他們用暴力脅迫人民支持,而是將政治體制整個翻轉,使得人們原本習於服從的法則產生質變。
因此,不加思索地服從當局的規定與指令,僅僅仰賴規定而遮蔽、迴避當中的思考,把一切都交給規定與領袖說了算,沉淪其中而不自拔,這才是鄂蘭認為的罪惡之源。艾希曼這樣的服從則進一步透過其行為轉換成了最實質的支持,他順從指令,一點一點地透過簽署與指派,將原本不該喪命的人們送入死亡。對鄂蘭而言,這種邪惡的平庸是最可怕、最無法言喻、又讓人難以理解的惡。

思考:與自我的無聲對話
在鄂蘭的眼中,不思考是邪惡之源。那什麼是思考?
在當時的德國,跟隨納粹政權旨意的不只是普羅大眾,亦有許多文人知識份子。這些人往往飽讀詩書,享受文化的豐碩成果,難道這些人也都不思考嗎?
鄂蘭認為,被動享受知識不等於思考本身;思考本身絕非被動過程,而是一種對話:與自我對話。而這個關於思考的故事可從蘇格拉底開始說起。蘇格拉底用自己的生命帶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寧受不義而不做惡。
對蘇格拉底來說,他相信「我」並非完全孤立的存在,而是一個「二合一」的自我。這個自我始終與我們相伴。如果我們的行動或意見與他人產生矛盾,我們大可以遠離或是離開這些人,但是我們始終無法逃開自己,這個自我是我自身的夥伴與見證者,我們固然可以暫時無視於它,投身於其他各種事務中,但終究無法完全與之分離。
對蘇格拉底來說,這樣的能力十分基本,每個人都能具備而不假外求,不需要仰賴特別的官能去接收。因此他不斷地要求要「將事情想通透」,不斷地刺激著更進一步的思考。蘇格拉底所設想出的質疑並非為了好玩或使對方蒙羞,而是因為他真誠地無法信服;他必須透過質疑與思考清除眼前的迷惑與不解,而不甘只是庸庸碌碌地照做就好。這股思索的動力出自於與自身相伴的自我,這個自我不斷與我們進行對話與交流,我們不可能逃避它的存在。蘇格拉底的立場是:寧與世人不和,也不願與自身傾軋。
是故,在考量是否服膺或追隨他人意見前,我們最該做的是與自我一致而不矛盾。與自我產生矛盾,就像招來一個無所不在的仇鄰或敵人,我們必須一直與這般矛盾相處,這絕不是愉快的體驗。我們可自問,自己是否願意讓我們原本所看不起、無法接受的那種為惡之我與自己常相伴隨?
鄂蘭相信,若我們夠真誠,那麼我們絕不會做如是想。我們可從迎面而來的狂潮中抽身而出開始反思,使自己站到事務之後開始自問。這樣的力量或許只是種消極不為,使人不再投身惡行,不見得能直接指出善行為何。但在重大危急時刻,當原有倫理法則與律法都不再能遏止人們之時,透過這種方式紮根於自身,至少能使自己不隨波逐流地做出那些不堪的惡行與災難。沒有一個認真如此思考的人能夠再度成為服從者與同流者,她的行動將成為長相伴隨的記憶,而記憶喚起那在自身之中的聲音與感受。
若能用這種方式重新思考平庸之惡,我們將更理解為什麼一群缺乏堅強惡意的人們能喚起二十世紀最可怕的罪惡。這群人未對事情加以思考,因此不能自觀自我的行動而化為記憶,也無法產生一股遏止的力量與聲音。因此,這些人忘卻了自我的存在而缺乏自我的根基,能輕易委身於各樣的口號與命令中隨波逐流。正因如此,他們缺乏拴住自己的最後限制,一旦外在浪潮迎面襲來,他們將可一路隨潮而去,滑落到讓人難以想像與接受的極端罪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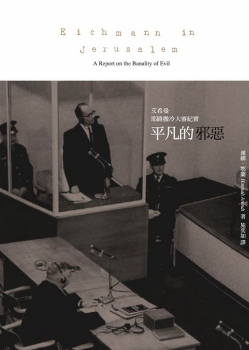
判斷:想像力是你的超能力
上述這種透過思考來中止為惡的作法有著一項特性,它要求人們自我反思,而這看來相當的「個人性」、甚至是主觀性。鄂蘭自然知曉這項特質,但她亦不認為我們因此就要掉到純然的主觀論,變成一種人人都能理直氣壯地自稱「反思之後認為自己沒有錯、自認問心無愧」的情況;但她也同樣不願意重新回到先前的老路,去建構一套可以放諸四海普遍有效的客觀倫理法則來指引大家該如何行動。晚年的鄂蘭遂開始從康德的思想之中挖掘理論資源,從康德的《判斷力批判》中尋找突破口,嘗試將康德原本的美學判斷論用以闡述道德判斷。

讓我們先從美感判斷出發。好比我們說:「今晚月色真美」,我們確實做出了一個美感判斷。但是,這種判斷並不是我們先掌握了美的法則作為大前提之後,再將眼前的月色涵攝到這法則之下。我們是直接對於月色之美有所感知,而做出如是判斷。在此同時,我們並不只將這般的美之宣稱視為一種純粹個人意見,我們也是在對他人提出,並信賴著這個判斷能傳達到他人心中,對於他人而言一樣有效。
在鄂蘭的眼中,這蘊含著兩件事。一方面,我們對於美之判斷並非援引普遍法則而做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美的典範事物,並直接從中對於美加以感知並做判斷。當然,典範或許不完全可以放諸四海或萬世不變,它可能會有文化上或時間上的特殊性,但它確實可與他人共享,因為我們與這些人亦共享了同樣的感覺(sense),這作為 Common Sense,即這群人普遍共享的常識。
因此,當我做出一個美感判斷時,我並非完全地陳述個人感受而已。當我對人們做出這項宣稱,要與人溝通時,我勢必是想像著,在人們與我共享的這般感覺之下,有可能亦會認可我的判斷。在此,透過想像的過程,我們將自己的宣稱予以擴展,試圖將他人的可能感受與想法亦納入其中,使自身判斷的有效性進而擴展,而形成一擴展的心靈。[4]而這個想像如果能越發考慮與觸及到越多人的處境與狀態,越能增強我的判斷所具有的代表性:我的判斷不再只是純然的一己之思和一時之興,而是盡可能地將各種可能都涉入其中,而克服了原本所可能蘊含的自我本位。
對於鄂蘭來說,這樣的美感判斷帶來了突破的可能性,如果我們能將這樣的判斷套用到道德與政治判斷中,那麼我們就可以設想一種既非法則援引亦非純然主觀斷言的是非判斷,而是主體間相互交融(Intersubjectivity)。而這個嘗試在她看來是可行的。政治生活與美感判斷一樣,雖然都充滿著各式各樣的人,蘊含著人的複數性(plurality),但判斷的有效性不因此就只能建立在各種零碎意見的隨意總和、或是各種利益的相互妥協。
另一方面,如果鄂蘭想將這種美感判斷模式帶入道德與政治之中,那麼下一個問題是,是否有足夠良好的典範可供我們參照。鄂蘭相信,蘇格拉底的真誠本身就是值得人們參考的歷史典範,這個形象屹立於西方文明的記憶中。另一方面,這種典範本身不見得是真人真事;我們亦可能在史詩與文學作品中,感受到諸多偉大心靈帶給我們的深刻印象。
回到關於平庸之惡的討論。
深陷於平庸之惡的人是不願思考的人,他們喪失了自我而缺少了真誠的記憶,他們所擁有的只是泛泛之言的表面之物。他們無法看見、亦無法與他人共享著良好的典範,因而亦無法與他人形成真實的聯繫。在這樣的不真實聯繫中,他們可能對於世界產生一種毫不在乎,他們可以依附於任何人與任何事物之中,不再關注與思索裏頭的是非善惡。也正因如此的不關注和不在乎,最大的罪惡才有了誕生的可能。
黑暗時代的星點路標:鄂蘭的遺緒
作為鄂蘭晚年思考嘗試的紀錄,本書並非鄂蘭一本完整的著作,其中的某些想法可能有些不甚嚴謹與不完整。書中關於康德《判斷力批判》的援引即是一例。
鄂蘭晚年本想對人類心靈活動做深入完整的探討,並著手撰寫《心智生命》一書,但在鄂蘭1975年去世時,鄂蘭晚年對於判斷的最終完整思考 ─〈判斷〉一卷才正要開始撰寫。另一方面,如同鄂蘭的另一名弟子,《康德政治哲學講稿》一書的編輯者羅納德‧貝納爾(Ronald Beiner)所言,鄂蘭對康德《判斷力批判》一書的援引其實仍是嘗試之舉,是她在面對與思索自身問題時做出的詮釋;讀者若想從鄂蘭的文字中直接獲取康德關於美感判斷的觀點,則可能會受到誤導[5]。

此外,自鄂蘭觀察艾希曼大審並寫下文字後至今已五十年餘。在這期間,有研究者透過艾希曼所留下的各種文件,試圖挑戰鄂蘭當時對艾希曼的觀察,認為艾希曼並不完全是一無所知地完全盲從,甚至對於自身的作為曾引以為豪。[6]因此,我們也不應毫無保留地採信鄂蘭對於艾希曼之觀點。
但即使是本未臻完善的著作,即便我們的時空條件都已遠離鄂蘭當時面臨的那場世紀大審,但這並不代表鄂蘭的思索過程不值得我們所借鏡。
回顧鄂蘭的一生,其問題意識即是不斷對於過去政權之罪惡進行反省與思考,以回應於自身所在的「處境」。現在的我們固然不再建造那些視人為草芥的集中營。但別忘了,我們這塊土地上也曾有段服從威權的歷史,也有許多不是那麼正義、侵害人權的過往,或許至今都未能好好地面對與正視,也才會有「威權時期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嗎?」[7]這種辯護的說詞出現。
對於這些未竟之業,需要我們不斷地去理解事實與反覆思量。鄂蘭本人雖未能及時完善她自身的思考,但也在本書中留下些許路標。至於這個未完成的思考會終將指向何方,本文無法以先知的口吻提供預言與指示(事實上,我亦尚未明確知曉),只能留待各位閱讀之後一同延續思考。
[1] 按雷敦龢教授在《平庸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一書之〈導讀〉所言,傳統慣用的「猶太」一詞是十九世紀傳教士刻意選用犬部「猶」字,當中包含對尤太人的貶抑,故應以「尤太」一詞代之。
[2] 當然,鄂蘭被譴責的另一部分,是因為她在書中寫道尤太長老與納粹政權的妥協,為了保命(以及保持部分族群的存續)而同意將另一些尤太人送入集中營。
[3] Hannah Arendt(2013),《平庸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施亦如譯,台北:玉山社,頁307。
[4] 以上討論是出自於鄂蘭之見,或許並非是對康德美學的適當理解。見後述。
[5] Ronald Beiner(2013),中文版前言,收於 Hannah Arendt(2013),曹明、蘇婉兒譯,《康德政治哲學講稿》,頁1-1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6] 騙子-艾希曼的四重面具:Tom Teicholz評《耶路撒冷前的艾希曼:大屠殺劊子手不為人知的生活》
[7]「威權時期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嗎?」 蔡英文為謝文定辯護反惹議
-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蘇友貞譯,《心智生命》,臺北:立緒,2007。
-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施亦如譯,《平庸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臺北:玉山社,2013。
-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曹明、蘇婉兒譯,《康德政治哲學講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責任與判斷,蔡佩君譯,臺北:左岸,20021。
- 蔡英文,《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漢娜‧鄂蘭的政治思》,臺北:聯經出版,2016。
- 蔡英文(2016),轉型正義的議論: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觀點,發表於「加害者的過去與現在式:轉型正義的法律與政治哲學論壇」(10.29.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