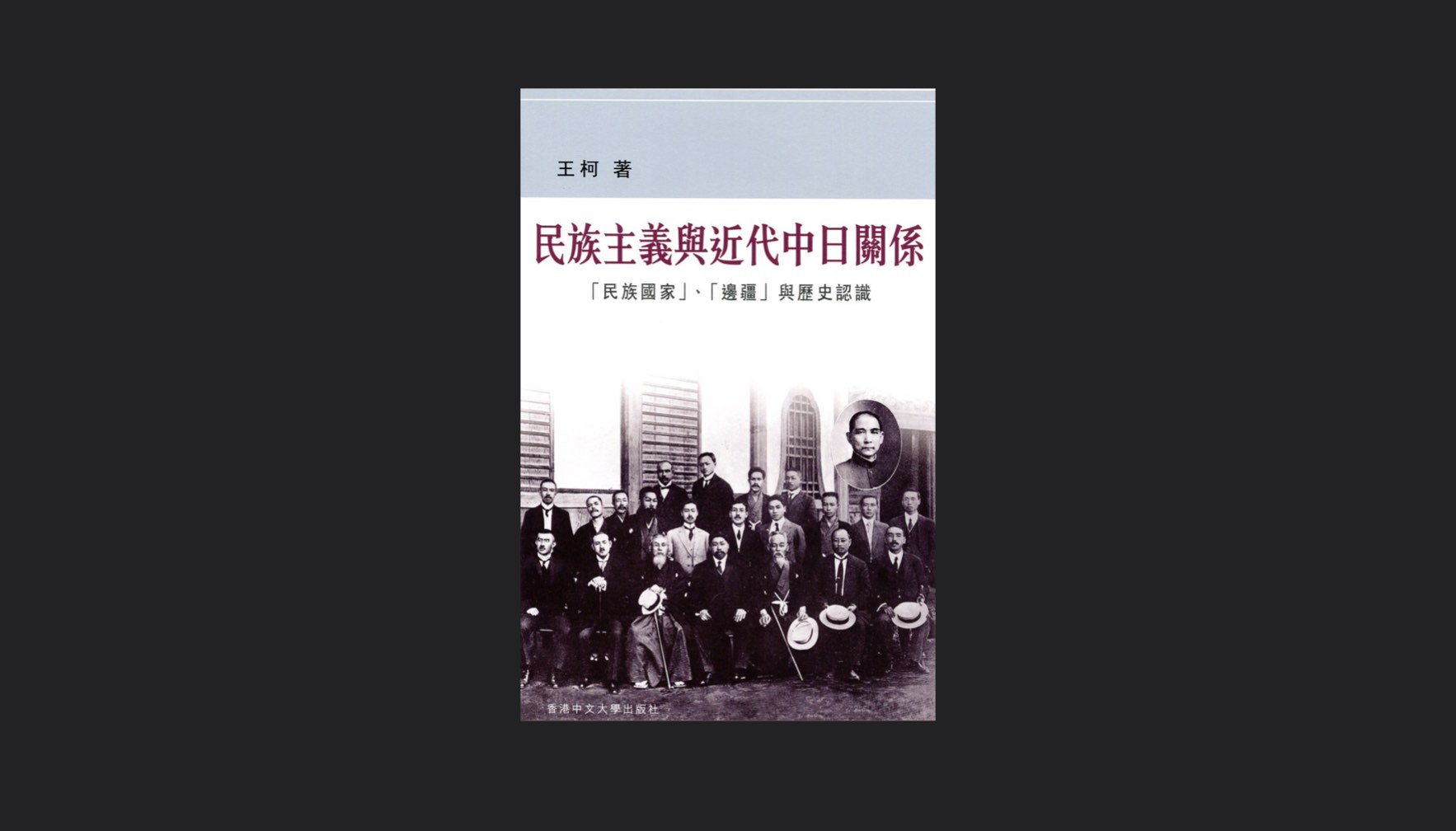1989/11/18
河裡的魚要如何看到它正游在其中的河水?牠無法離開水從遠一點的地方或另一個觀點來看。
類似的情況正發生在柏林。
一切都在流動,每一刻都有新的事件、新的報導;只要一踏出門,幾分鐘內我就成為人群漩渦的一部分,人們對著我大喊報紙頭條:再會島嶼!一個德國!人民勝利了!八十萬人征服西柏林!銀行和郵局裡,東德人大排長龍領他們的「歡迎金」。

老人們一臉茫然,三十年來第一次再次踏上城裡這一邊的他們,是來尋找自己的回憶的;柏林圍牆之後才出生、住在才幾公里之外的年輕人,走在一個未知的世界,開心到連柏油路都快承載不住他們。
我寫著這些字句的同時,四面八方的教堂都在敲鐘,就像前幾天威廉皇帝紀念教堂突然隆隆響著鐘,傳達圍牆開放的消息,街上的人們都跪下來哭。
看得見的歷史總是讓人狂喜、感動、且擔憂。沒有人會錯過。而且沒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城市經歷了太多。
成千上萬從東邊湧進西德的人隨身帶著激動的情感,彷彿那是有實體的東西。他們的情感從這邊的人們臉上反映出來,也被忽然變徒步區的街道上的百萬腳步聲、警笛和教堂鐘聲、眾人發問和謠傳的話語聲而強化,無人創造的腳本裡沒寫出來的字句。無人,也是所有人。
「Wir sind das Volk!」(我們就是人民!)兩個禮拜前他們才在萊比錫吶喊。我們就是人民!現在人民在這裡了,把領袖留在家裡。
東柏林的大規模示威發生在八天前。
西蒙娜去了,但被腓特烈車站(Bahnhof Friedrichstraße)眼睛如鷹眼的邊界守衛挑出來。不, 她不能通過。「為什麼其他人就可以進入?我跟其他人一樣在這邊等了一個半小時了。」「抱歉,但我們不需要給理由。明天再試試看。」

當時我出另一項任務去了, 我在遙遠的西部有幾場朗誦會:亞琛(Aachen)、科隆(Cologne)、法蘭克福(Frankfurt)、艾森(Essen)。就連在那裡,柏林還是經常出現在每一次對話裡。
星期一晚上是艾森,魯爾區(Ruhrgebiet)的黑暗中心。朗誦會結束,在昏暗咖啡店的討論,Erbsensuppe(豆湯)、Schlachtplatte(香腸拼盤)、大杯啤酒。幾個年輕人出席,出身劇場的女孩、書商、生化學家、作家。
總是同樣幾個字眼不斷重複: Übersiedler(難民)、Aussiedler(移民)、Wiedervereinigung(重新統一)。住在荷蘭的人不怕德國重新統一嗎?不怕嗎?嗯,會怕。我們不想重新統一,要也不是跟那些薩克森人和普魯士人。
他們受獨裁主義教育長大的,根本什麼都不懂。每天早上六點就去工廠大門口報到。這要叫我們做何反應?他們或許是德國人,但是不一樣的德國人。
那群人裡頭一成會投給共和黨(Republikaner),六成會投給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Democrats,C.D.U.)。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看過民調。
德國會再次成為一個大國,但是傾向東邊,傾向波蘭人和俄國人。歐洲其他地方應該會開心了吧。這是你們要的嗎?平衡全面挪移,我們只好再次成為一個大國。
我唯一能想到的回覆是,它已經是個大國,它的相對密度將終結人為的分裂。大國施展自己的重力,不多久將把一切吸引過去。到時只有德國人自己才能應付後果。
談話結束之後,他們送我去搭最後一班到科隆的列車,類似有軌電車那種。這一趟無比折騰。列車上空無一人,很冷,而且每站都停,連沒人也停。車外是重工業區的冷酷剪影,地獄的火焰映在黑夜中。
到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的時候有炸彈警告,我們在寂靜無聲的黑洞裡停頓。我車廂裡只有我一人。我聽見老駕駛的聲音從擴音器傳來,氣喘吁吁: Bombendrohung,炸彈警告。
我們無止盡地等待,不知是因為夜晚,或是因為沒有別人,或是我們稍早的對話還是只是我的年紀,我忍不住想到戰爭,想到這個奇怪國家的強烈吸引力,它總是有意或無意地,把其他國家拖進自己的命運。
週四晚上。我回到柏林,跟我的攝影師和一個朋友坐在計程車上。在我們說話的同時,我忽然從汽車收音機的聲音聽出什麼,我認得這種聲音:重大事件才有的迫切、急促、不可置信的語氣。我請司機把音量調大,但沒有這個必要;她知道我們聽得懂德語了,便親口把新聞告訴我們。
她很激動,她把金色長髮向後撥,幾乎用吼的。柏林圍牆開放了,所有人正前往布蘭登堡大門,全柏林的人都往那邊去。我們要的話,她現在可以載我們去,因為她自己也想看看。假使我們同意立刻就去,她說她會把計費表關掉。
塞車隨著每一秒鐘越來越嚴重;勝利紀念柱(Siegessäule)以外一百公尺就已經動彈不得。我們旁邊是一輛冒煙的衛星汽車,年輕的東德人秀出簽證給我們看,路燈下,他們的臉色興奮得慘白。
我跟司機說走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大道(John-Foster-Dulles-Allee)到國會大廈會比較快。杜勒斯、國會大廈、戰爭、冷戰——在這裡,一開口就不可能不提到歷史。國會大廈的黑色船艦在人海裡;所有人朝著布蘭登堡大門的大柱子和上方奔馳的馬逼近,馬兒曾經是往反方向進攻。

可俯瞰菩提樹下大街的觀景台被人群的重量壓得搖搖晃晃,我們努力穿越人群,一有人下來我們就爬上去,一次一個人。柱子前面空曠的半圓形現在被橘色人造燈打亮;半圓形內成陣列的邊界士兵,看起來無力阻擋我們這邊人群的力量。每當有人爬上柏林圍牆,士兵就試圖用水柱把他們沖下去,但水壓通常不夠強,孤單的人影停留在上面,渾身溼透,被發亮白色水氣泡沫包裹的活生生的雕像。
人們吶喊、歡呼,幾百台相機亮著閃光燈,彷彿水泥圍牆變透明了,彷彿它已經不存在。年輕人在水柱下跳舞,脆弱的士兵列隊是他們芭蕾舞劇的背景。昏暗中,我看不見士兵的臉,而他們只看得見舞者。由其他群眾組成的大型動物長得越來越大,只聽得見他們的聲音。他們的世界正在毀滅,他們唯一認識的世界。

回程時計程車司機也沒跳表。她說她很快樂,她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刻。她的眼眶濕潤。她的男友現在正在柏林圍牆附近,她想和他分享這一刻,但她不知道他在哪裡,而且她的班要到早上六點。
隔天早上,星期五。我站在老鷹咖啡(Café Adler)的窗戶內,這是從西德過查理檢查哨之前最後一間咖啡店。「你正要離開美國防區」——這句話今天沒有意義。一切似乎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剝落。

衛星汽車組成的車流慢慢流過邊界。某人拿錢給車裡的人;另一個送他們花。車裡的人在哭或不知所措,彷彿他們現在把車開到這裡,那些人對他們揮手呼叫,都是不真實的事。
東德邊界守衛站在路對面,離西德邊界守衛幾公尺遠。雙方沒有交談,只是在蜂擁而來的人群裡站定。我發現他們的表情跟昨天黑夜裡一樣,難以解讀。然後我自己走到另一邊去排隊,我發現一切都跟以前一樣:簽證,五馬克,絕望的一比一匯率,雖然實際匯率應該是十比一才對。
隊伍動得快,十五分鐘內我已通關,但另一邊的隊伍排到漫無止盡,繞過街角一直到腓特烈大街。我走到出過我兩本書的人民與世界出版社(Volk und Welt)辦公室那條街。裡頭安靜無聲,但門是開的。我找到一位校對員,得到柏林式的幽默問候:「你來看我們真好,正當其他人都往另一個方向去的時候!」但他們顯然也被捲入事件裡。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說我從一個匈牙利友人那邊聽到,在「改變」——我想不出更適合的字眼——發生之後,新成立了兩百多家出版社。他們自然早就曉得,但最令他們擔心的是,如果這件事為真,要如何取得足夠的紙。
對於統一,沒有人說得出合情合理的話:「經濟上要如何行得通?這裡沒有人買得起西德的書。我們的書才賣一、兩馬克。」他們有精彩的外國文學書系——從莒哈絲(Duras)、弗里施(Frisch)、格諾(Queneau)、川端康成、卡內提(Canetti)、齊佛(Cheever)、卡爾維諾(Calvino)、貝恩勒夫(Bernlef)、薩洛特(Sarraute)到克勞斯(Claus)——然而一旦西德出版社可以在東德自由運作,會發生什麼事?人民與世界還有辦法取得發行權嗎?
幾百個類似的問題到處流竄;整個國家就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巨大問題,而每一個可能的、無法想像的答案,無論經濟或政治,都深切影響幾百萬人的生活。

雕琢出現代德國轉變的私密肖像。
作者以目擊者的觀點,
別具洞察力地描述 1989 年的關鍵事件,
及日後頗為艱鉅的兩德統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