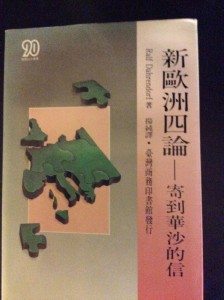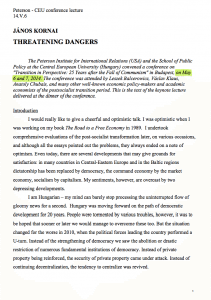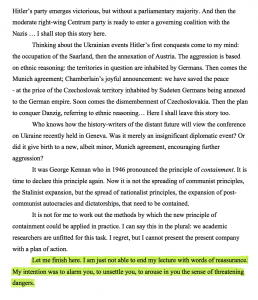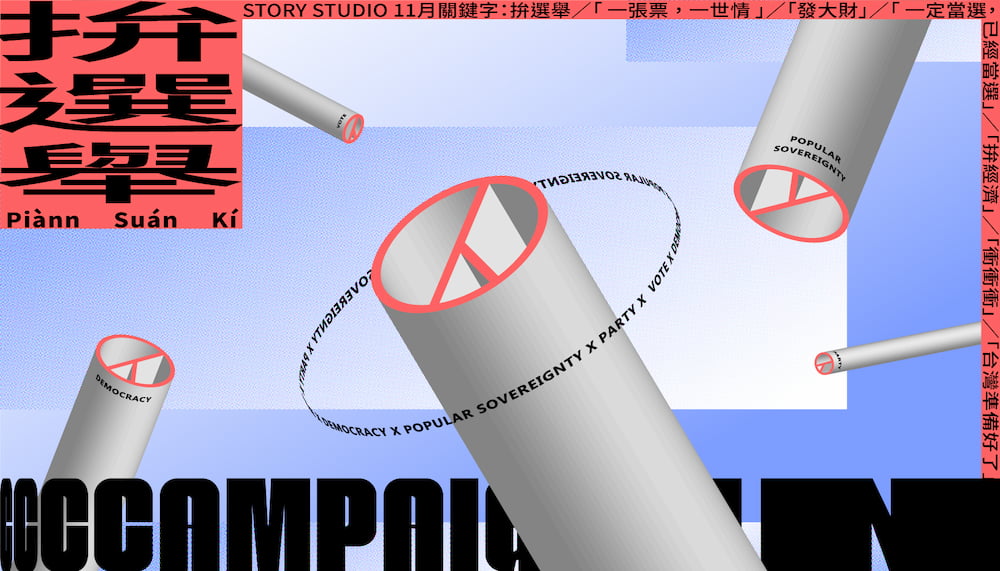五、民主化之路的一點感想
談到這裡,我們不免會問,這樣一個民主的道路是漫長艱苦的,那它會不會倒退呢?理論上是有可能的,歷史上也曾經發生過。比方說最有名的不是發生在落後國家,而是在文化先進的德國,成立於 1918 年的「威瑪共和」是個德國史上燦爛的「黃金二〇年代」,其最後的死亡卻導致一段最為黑暗時代──納粹時代──的誕生。
那就是一個民主的倒退。誠如許多威瑪共和史家指出的,希特勒用民主的合法程序上了臺,但一上臺就摧毀他才剛宣誓遵守的威瑪憲法。那就是一次民主倒退。民主並不是一建立以後就不會倒退的。歌德曾經講過一句話:「人想要安睡,上帝不斷地把你搖醒,使你保持儆醒。」我想,我們對民主也應該保持這樣儆醒的態度。
民主是要處理權力關係的,民主的形式建立以後,權力關係並不是就像康德所說的心中的道德法則自律地運轉起來。臺灣的民主化是從有著東方專制主義意味的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體制。東方專制主義下的權力體制幾乎是不太有自主社會存在的空間,我們在前面也提到,民主轉型能成功的契機在於出現一個能自主作為的民間社會,且不受國家權力體制宰制,但從權力的本質來看,國家權力體制是一定會展現其權力宰制性的,因此,國家跟民間社會之間的權力互動關係是一個很複雜的關係。
我二十幾年前為紀念美麗島事件十週年寫了一篇長文,在文後針對這個問題,引述了英國社會主義學者 John Keane 的一段話,他強調:
民主化既不是把整體國家權力擴充到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之非國家領域的同義詞,也不是指國家(state)的廢棄並在公民社會內建立公民間自發的協議。
他說這是兩個不能實行的極端。在我們這裡,或者華語的語境裡,我們有時候會聽到一些所謂「進步」的論述,強調什麼「人民民主」或「大民主」,如果去分析其潛在的意識結構,恐怕不難看出這兩個極端後面的意識結構是同構的。如果只是不能實行,那也許只是一種「戲論」(借用熊十力的詞),怕的是硬要在現實中實踐起來。
現實歷史中血的教訓還不夠鮮明麼?John Keane 指出,「民主化是一個把權力分配到公民社會之內和公民社會與國家之間制度地不同領域之多樣公共領域的困難的、長期的過程。」我是很同意 John Keane 這觀點的。這是我們在思考民主化以後怎麼樣進行民主鞏固必須細細品味的。
歷史上,許多變革是打著民主化的旗號的,是打著人民的旗號的。但我們也在歷史上看到很多像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結果,我們也可以看到希特勒、史達林用鮮血來教訓人們天真的心靈。臺灣在一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在半個世紀的親身經歷中,多少先人,多少我們週遭的友朋,為了一個比較合理的權力安排,為了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生活秩序,默默地付出過。這一切的一切,只為了臺灣的民主、自由。現在,我們走上民主化了,但未來真正要制度化地讓民主成為我們政治、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路還是很漫長的。
最後我要引曾當過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院長、德裔社會學家 Ralf Dahrendorf 在 1990 年東歐巨變後不久講的一段話,我覺得蠻有意思的。東歐巨變後,他仿英國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反省法國大革命的方式,寫了一本小書《歐洲革命的反省──寄到華沙的信》(商務印書館的中譯本書名改稱《新歐洲四論──寄到華沙的信》,以下引文出自該書)。他在書中討論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時這樣說:
他說的基礎就是公民社會。正如他接著說的,關鍵是公民社會,「沒有公民,律師與政治家也就前功盡廢了。」我覺得這個反省非常有深遠意涵。
我們是一個深深受到東方專制主義影響的社會,要建立起一個比較健全的公民社會,應該是一段還有待我們走下去的漫長旅程,我們必須像歌德說的那樣,時時保持著儆醒。今天我藉著回顧這段歷史,把我的這些反省和感觸,拉拉雜雜地提供給各位參考。這絕對夠不上是一個系統的討論,我們也希望將來臺灣能夠出現一些比較簡明扼要的、整理臺灣民主運動歷史的書,我覺得會是很有意義的。如果有人進一步去反省臺灣的民主發展,像 R. Dahrendorf 或 E. Burke 那樣的反省,可能會對我們社會更有幫助。希望你我大家共同來做這樣的努力。留下一點時間聽聽各位的意見,或接受各位的詢問,謝謝。
來賓問答
第二個就是在美麗島大審是公開審判大放送的狀況,讓施明德可以講他一些想法,這一段我一直很好奇,為什麼要讓他公開這樣講?甚至美麗島大審為什麼不殺人?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在後來的發展,包括林宅血案、陳文成案,因為這畢竟還是懸案,我一直覺得說這兩件案子是不是只是偶然,或只是一個不小心失控的狀態,而並不是國民黨真的那麼想要殺人?如果想要殺人的話,美麗島事件就可以殺人了,謝謝。
答:我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現在好像沒有資料看到美國有干涉臺灣對雷震的逮捕跟審判,如果有,可能也只是一般外交關係的瞭解(當時臺灣跟美國是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我沒有研究,不是很清楚。這一方面可能跟當時的冷戰體系有關。美國這個國家是很複雜的,論國力,可說是今天的羅馬帝國。你看它一方面講民主、自由,講人權外交,但另一方面它又介入很多到底是它國國內事務還是國際事務不很清楚的各種事務,所以你說它對當時的「雷案」有沒有介入,我沒辦法回答。我不是研究這個,但是好像沒聽說有人著墨過美國有沒有干涉蔣介石抓雷震一事。
就第二點來講,我願意這樣講。你說美麗島事件為什麼要公開審判,做大放送?當然,國內外壓力很大是一個因素,但是在這一點上,我作為一個「美麗島案」的受難者,蔣經國的囚徒,我過去也講過,蔣經國在「美麗島案」沒有殺人這一點是不能抹煞的。我出獄後聽說好像是沈君山他們跟蔣說這個案子不能流血,如果流血,會帶來仇恨等歷史問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這樣,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像他老爸一樣寫日記,當時的心境是如何,是怎麼想的。這些恐怕只能留待以後史料來提供佐證了。
至於你說像陳文成案、林宅血案,到底是蔣下令還是下面失控?不曉得。以我個人的揣度,陳文成案應該是特務單位的失誤造成。像跟我關在一起的一個老政治犯魏廷朝就揣測說,那可能是刑求失手,然後棄屍臺大,故佈疑陣。但真相我也說不上來。林宅血案比較複雜一點。林宅血案到現在還有一點仍不清楚,那就是當時權傾一時的特務頭子王昇及所謂的劉少康辦公室究竟有沒有介入。沒有證據說那是蔣的下令,也沒有證據說蔣完全置之事外,不曉得。恐怕要等未來更多史料出土來解答,但是,老實說,是不是還有史料我都很懷疑。
第二個問題我想請教的是,在民主政治基本框架大體成型的時代,公共知識分子到底應該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因為在威權的瓦解過程中間,我們看到臺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包括您在內,大半的知識分子是不斷地在呼籲吶喊,甚至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我想如果是民主和法治已建立的框架下,知識分子是應該用他的社會聲望表達他對某個政黨的鮮明態度,還是說他需要做一些什麼其他的事情?謝謝。
答: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剛剛已經提到,從歷史的客觀結果而言,我這個蔣經國的囚徒願意對他在本案沒殺人這一點有一點正面評價。我覺得,蔣經國到生命最後死之前,要在臺灣用「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態勢把正在興起的反對勢力壓下去,有沒有可能?是有可能的,你看當時的王昇恐怕就是這個態度。但真這樣一定會在後來臺灣民主轉型、民主化發展的過程中,增加很多亂度,他沒有這樣做,某個角度說他是對民主發展留下一個比較正面的遺產也可以。
那麼他究竟為什麼會這樣選擇?是他當時體力衰了、意志力比較弱了,還是他有這樣的自覺,還是怎樣?不曉得。有人猜測,江南案也許是一個關鍵。因為蔣經國是特務出身,他來臺灣以後幾乎是管特務。一個不算太燙手的案子竟處理成這樣,太不像話。是不是這個樣子?有人這麼巷議,我們不知道。是不是他感覺到沒有辦法再(這樣家天下地)傳下去了,還是說他有民主的胸懷?我講過,是不是有史料佐證,不知道。
我個人看歷史相對比較不重視動機。但客觀的事實是因為蔣經國沒有用血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之後臺灣民主發展沒有走上血腥的大混亂局面。雖然還是有林宅血案、陳文成血案,有零星的血的衝突,但比較像個別的擦撞,而不是連環對撞、追撞的車毀人亡。有摩擦,到現在都還在摩擦、擦撞,很多案子還是懸案,轉型正義還沒有處理,但這個還沒發展到對撞相互毀滅。這個也許是人家說臺灣民主轉型基本上是一個和平的民主轉型。這是不是蔣經國晚年一個正面的遺產,不知道,讓未來的史家去討論吧。至於他為什麼這樣做?我們真的希望有更多的史料來佐證。
至於你第二個問題,我的看法是這樣,在一個已經建立起民主政治架構的社會,培育建全的、壯大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恐怕才是最重要的。一個社會最好不要出現國家完全壓著社會的狀況,也不要出現一個完全弱勢的國家,讓像所謂「人民民主」這樣的民粹情緒主導著、壓著,這兩個極端都不是成熟法治社會健全的樣貌。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培育公民社會,公共知識分子在這裡就應該扮演更大的功能。
什麼叫公民社會?我認為 Charles Taylor 的定義簡單明瞭,他大意是說,公民社會是一個不受國家權力控制或監護的自主組合;其次,這個自主組合有公共的關懷,它關注的是公共事務,不是關注養鳥、鬥雞這些無關公共性的個別興趣;最後,可能也是最強意義上的,它能夠集合這些自主力量,進入一個政治過程,來決定或影響可以實現這公共關懷的政策,或者去改變不符合這些公共關懷的政策。這樣的社會就是公民社會。
我們觀察臺灣當今的社會,公民社會確實已經成長起來了。我們可以比較1980年代和今天的社會運動,前者通常跟當時正在興起的政治反對運動結合在一起,但你看像國光石化的抗爭,政治力量基本已經不介入,至少不是主導性的力量了。我感覺臺灣社會這些年來這種基於公共關懷的自主力量、組合,在許多領域都在成長,這是很好的現象。
然而,臺灣今天有一個嚴重的危機,倒不完全是政治的,而是本來應該是公共性的機制,像傳媒,墮落得一榻糊塗。比如我們晚上看電視,每個小時重複一些無聊的個人事務,哪個影星的鼻子整型歪了、哪個明星的婆婆又怎樣了、哪個富豪的什麼人生小孩了,而且一報報好幾天。真是無聊到極點。試問這跟公共議題有何關係?妙的是,這些媒體抬出的大帽子是「觀眾有知的權力」,夠堂皇了吧!這其實是一種公共性倒退的現象,它會無聲無息地腐蝕我們的公民社會。然而我們現在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對這些現象好像都很少講話了,習以為常了。
答:我沒有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經驗,一些狀況的瞭解是靠文獻資料,未必有實感,所以我未必能很確切回答你的問題,但可以把我一些感想提供給你參考。
我想跟印度作對比的話,這條件完全不一樣。印度曾經是一個殖民地,就像日本的民主是麥克阿瑟加在它頭上的,當然它有它文化上的種種使它能怎麼樣跟它接在一起,成長成今天這個樣子;印度也是長期受老牌的民主國家英國的統治,這跟它後來的民主憲政是怎樣的關係,我沒研究不好說。但在中國,有一個很大的幽靈一直纏著中國現代史的發展,那就是專制主義。
已經過世的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先生,他以前是周恩來的英文秘書,老幹部,也是人稱「南王北李」(南王是過世不久的王元化先生)的兩位倡導自由思想的老幹部,他晚年講過一句話,很有意思,他說五四反傳統反得那麼激烈,但是反了半天,有一個傳統不但沒有反掉,而且越來越根深柢固,那就是專制主義。
你去看文革的歷史、回憶,你大概就比較能瞭解李先生為什麼會那麼講。毛澤東主義籠罩在當時中國的天空,支配著每一個人的生活。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專制主義消失了嗎?恐怕沒那麼樂觀,在中國大陸,左的陰影一直沒有真正退潮。像最近四川所謂「打黑唱紅」成為觀摩學習對象,一些新左派大力歌頌這些作為,說這是「重慶模式」,這些現象也許可以說明一點什麼吧!難怪有人要說薄熙來的作為是新毛澤東主義。
然而,從很多跡象看,我覺得大陸公民社會的苗正在出現,雖然以 Charles Taylor 的說法,可能連最起碼的第一層次都還不是很堅實。但你不能不重視像維權運動這樣的發展,它跟臺灣 1960 年代的一些發展有點相似。那時有臺灣記者騎著摩托車到農村做考察,寫出來的報導讓人們看到原來政府講的以外,還別有洞天;你現在去看大陸一些報導,像廣東南方報系的某些報導,你可以感覺到,在中國大陸,不受政府控制、監護的那種力量好像在出現,至少是試圖在掙脫政府的「全權控制」。這個力量能壯大到什麼程度不是很清楚,但我們在這裡看到大陸公民社會成長的生機。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中國大陸的「國家」還是很強有力,擁有近乎絕對的控制力,政治的控治力不講,就看經濟上的國進民退,就可以看到國家的掌控力一直在壯大,社會的力量雖然有在成長,但國家控制的力量更強勢。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愈來愈清楚,國家資本主義的型態是越來越強。這對民主的成長是不利的。
我知道大陸有很多知識分子在反省這個問題。去年,曾當過中共組織部副部長的朱厚澤去逝,聽說他死前跟一些年輕朋友講,你們有責任去搞清楚「中國模式」是怎麼一回事?中國有一些人宣稱中國已走出自己的路,而且走得比西方的模式好,「中國模式」將來會成為新的典範,「北京共識」會取代「華盛頓共識」。
朱厚澤向那些年輕朋友說,1929 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當時很多人認為資本主義不行了,以國家權力主導、計劃的「史達林模式」比較好,很多西歐知識分子也都這樣認為,形成一種時代風潮,認為那樣的模式才是經濟成長比較好的方式,連當時退到臺灣要以宣揚自由主義來反共的《自由中國》都還可以看到這種思潮的殘餘。
朱先生說,到最後,事實證明「史達林模式」造成很大的禍害,是錯的。他跟那些年輕朋友說,你們的責任是好好去弄清楚,去研究什麼叫「中國模式」,好好研究它對中國的利弊。他說他自己感覺,1949 年的路也許是錯的。這是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反省、思考。
這些反省、思考的關鍵,據我看,都集中在對「國家權力」的思考。國家權力不能得到規範,社會的力量不能壯大,民主化恐怕就很難有太大的期待。據我接觸過的一些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並不是很樂觀,認為要真正走上民主化還早。一個原因是,大陸那個強而有力的、帶有深厚專制主義色彩的「國家」(state)還看不到走向「去集權化」(decentralize),且讓「社會」有成長之空間的跡象。所以我對大陸的民主化相對比較悲觀。我認為至少要讓它的社會慢慢建全壯大,民主化恐怕才有機會。目前來看,有一個變數,就是網路會怎麼發展,會對大陸強有力的國家權力產生怎樣的滲透作用。值得觀察,但我不曉得。
(全文完)
杭之,本名陳忠信,臺灣彰化人。在臺中東海大學原習數學,後自修人文﹑社會學術方面之知識。1978 年 8 月出任民主運動刊物《美麗島雜誌》主編職務,同年 12 月 “高雄事件” 後被投獄四年。1983 年底出獄,以自由作家身份從事社會﹑文化﹑政治評論寫作。1988 年初,與十數位青年社會研究工作者創辦民間學術刊物《臺灣社會研究季刊》,任首任總編輯。著有《一葦集》(正﹑續篇兩冊,臺北,允晨)﹑《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上﹑下兩冊,臺北,唐山),《國家政策與批判的公共論述》(臺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一葦集》(北京,三聯)。1990 年起再度投身實際政治運動,先後在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任職,主編民主進步黨《政策白皮書》﹑《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國土規畫》等書,後改任立法委員(兩屆)、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副秘書長等職。 目前為「坐家」,坐在家中,用老真空管聽古典音樂,看看過去想看而時間看的書,想想自己生活過的這個時代的一些荒唐的、悲慘的、令人動容的、肅然的往事。希望能將這些隨想寫下來,以抗拒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