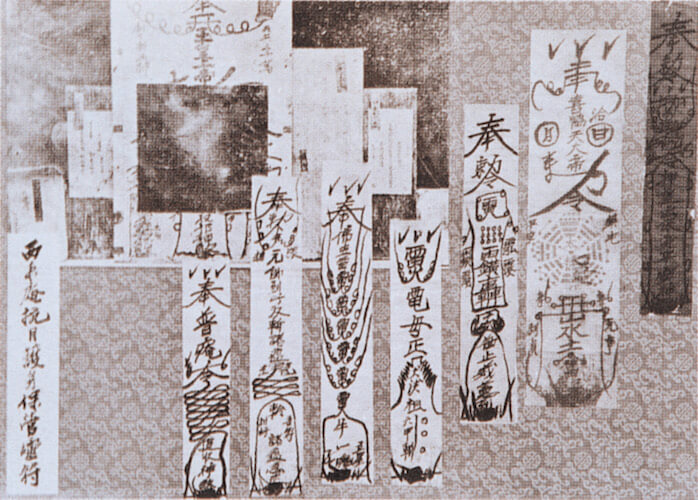1920 年,整個二十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對於臺灣歷史而言,是在一起極富象徵意義、同時在臺灣歷史有著重要地位的大事中揭開序幕──臺灣新民會成立。
為了爭取臺灣人的政治權力並啟迪民智,林獻堂等人發起的這個組織,成為二零年代推動文化抗日與各項社會運動的起點。這似乎就是我們對這一年所知的全部了。
然而,對於當時臺灣社會的大多數人來說,這個「歷史時刻」好像沒有太大的意義。關於這年,甚至是這年夏天,真正重要且影響深遠的,反而是一場沒被記得的暴雨。
溽夏,一如字面上的意思,這年八月的臺灣中南部濕到不行。肆虐的颱風、豪雨使得各地災情慘重,農作物的損失難以估計,一位住在臺中豐原的保正如此感嘆:「自我生五十三年以來未聞有如今年水災之甚者。」
對於住在河邊的人家而言,這場雨已幾乎等同災難,阻斷往來交通還是小事,氾濫的溪流甚至會沖毀身家財產、危及生命安全。據報導,南部的大河曾文溪最高暴漲了一丈餘(差不多是今天的三公尺),附近的低窪地帶轉眼間都成了水鄉澤國。連日的大雨,後來甚至將剛修繕完工的臺北橋沖毀⋯⋯
就在洪水退去,地方人士正忙著重建家園的同時,另一項將對中南部農民與耕植造成劇烈衝擊的事件,已經悄悄展開──
籌建、爭論了好幾年的嘉南大圳,終於要在這年 9 月正式動工。

第一張底片:曾文溪畔,灣里農村的日日夜夜
在嘉南大圳落成以前的臺灣南部,看天田的體質更加強烈。儘管各地建有不少埤、圳一類的水利設施,但降雨季節的集中,使得農業活動受到許多限制,耕田以粗放的旱田為主。當時的總督府技師、後來任臺北帝大教授的土壤專家澀谷紀三郎,在勘查後這麼形容南部的處境:
6 月至 10 月的雨期,所得的灌溉水量尚勉強種植一期水稻;水稻收穫後,土壤乾燥,犁起困難,無法再耕種利用。若降雨量不多,則連一年種植一次的水稻亦全無收穫。
設法獲取灌溉水源,於是成為首要之務。再者,由於一年就只有這麼一次的種植機會,養活全家大小都仰賴這一期的農作,若不幸又遭逢連日乾旱,爭奪珍稀水資源的衝突就會愈演愈烈,甚至經常演變成死亡糾紛。
未來,太遙遠的未來對他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現下的溫飽,以及讓生活好過一點才是重點。這種聽天由命的情緒,對於那些在溪流邊拓墾的農人來說,格外強烈。在堤防不夠穩固、甚至大多仍未構建的年代裡,為人們帶來豐饒田水的溪流,隨時可能化身洪水猛獸,沖毀良田、住宅,甚至滅村。
這幅景象,正是曾文溪沿岸農家年年上演的生死鬥。曾文溪,這條幾百年來因頻繁改流,而被戲稱為「青瞑蛇」的大河,河道最遠北至將軍溪、南達鹽水溪,幾乎橫跨府城到鹽水間這一大段範圍。如此劇烈的變動,使土地的流失與浮覆成為常態,也成為地方居民始終盤桓不去的夢魘。根據總督府在 1924 年的統計顯示,全臺易於遭河川氾濫影響的田地,就有高達一半集中在臺南州(包含今日的臺南、嘉義、雲林[1])。
就算活了下來,要繼續原本的農業活動也很有挑戰性:一方面,大水後的田地歸屬不明,而河道移位更徒增丈量難度;另一方面,滾滾河水帶來的大量泥沙,使耕田變得磽确貧瘠,不適合一般作物生長,收益當然愈發低落。這,即是生活在臺南善化農民們的日常。
善化的舊名是「灣裡」,因位在曾文溪的南邊凸岸而得名。1920 年盛夏的那場水災,毫不意外地也讓善化劇烈毀損,使得這個區域到隔壁鄉鎮官田、六甲一帶,全成了汪洋一片,死傷、損害不計其數。
日本殖民政府難道對臺灣的農業狀況毫無所悉、束手無策嗎?事實上,他們可關心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