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60 年代中期,杭亭頓已經安穩當上了哈佛的教授,平平靜靜在波士頓一帶成了家。1967 年,這樣的生活被詹森當局的一項任務短暫打斷:他被延攬為國務院顧問,準備了一份長達百頁的越戰報告,日後解密被他據以為文,發表在 1968 年 7 月號的《外交》雜誌裡。這篇文章引發巨大的影響。該文贊同政府當局要擊敗北越的目標,但又說明政府想達成那個目標卻完全用錯了方法。
詹森政府聲稱,南越被政府掌控的人口比例(而非受制於越共)已經從 40% 攀升為 60%,但杭亭頓不認同這項聲明的意義。「這項改變,」他寫道,「是人口遷移進入城市,而非政府的掌控擴及鄉村所致」──越共勢力在鄉村地區比以往都還要強。
然而,儘管詹森政府對於「沒有保證的樂觀主義」感到自責,但他肯定地說,批評家們會因「錯置的道德主義」感到內疚。杭亭頓指出,「絕大多數人真正支持的是誰?」這個問題,唯有在如美國這樣一個穩固的憲法民主政體下,而不是處於像越南這樣國家混亂與暴力攀升之中,才會有意義。
此外,贏得大眾對開發鄉間的支持只會一事無成;人民之所以投入越共懷抱,不是因為鄉村貧困,而是因為「欠缺有作為的權力結構」。杭亭頓寫道,哪裡有這樣一個強而有力的權力,「即使那個權力相當階級化又不民主,那裡就幾乎不會有越共染指。」鄉村裡曾遭到越共滲透的三分之一人口,之所以接納越共,是因為和越共一樣,種族和宗教的自治組織往往對歐美價值懷有敵意。
杭亭頓告訴我,語帶不贊同,「即使回到(越南)建國之初,我們也不贊成以宗教與種族忠誠度和越共抗衡,因為我們要的是一個現代化、民主政體、擁有國家軍隊的一個國家。我們處理越南的一個問題就在於,我們懷抱理想主義。」
他認為,這樣的理想主義如今也成為美國干預海外其他地區的特色:「大眾傳播喜歡我們的國家自我吹噓,這種心態假設了我們的價值和政治結構,也是其他國家想要的;而且,就算人家不要,也是人家應該要的。」杭亭頓相信,我們應該以能讓我們從對手那裡得到優勢的方式,在海外宣揚我們的價值才對,而不要勉強自己在人家國內重建社會。
因此,他在 1970 年代晚期,協助布里辛斯基和卡特總統實施了要讓蘇聯難堪的一項人權政策,不過,對於要在毫無西方式民主政治傳統的地方實地打造那樣的政體,他始終不以為然。
杭亭頓對越南的分析,來自於他新近出現的世界觀。1950 至 1960 年代之間,社會科學的大議題就是政治現代化。傳統的學識認為,非洲和其他地區的新興國家,會發展出類似我們的民主政治和法治體系。杭亭頓不認為如此。他對越南的見解(認為當地的政府迥異於我們的)都寫在他的著作《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1968)一書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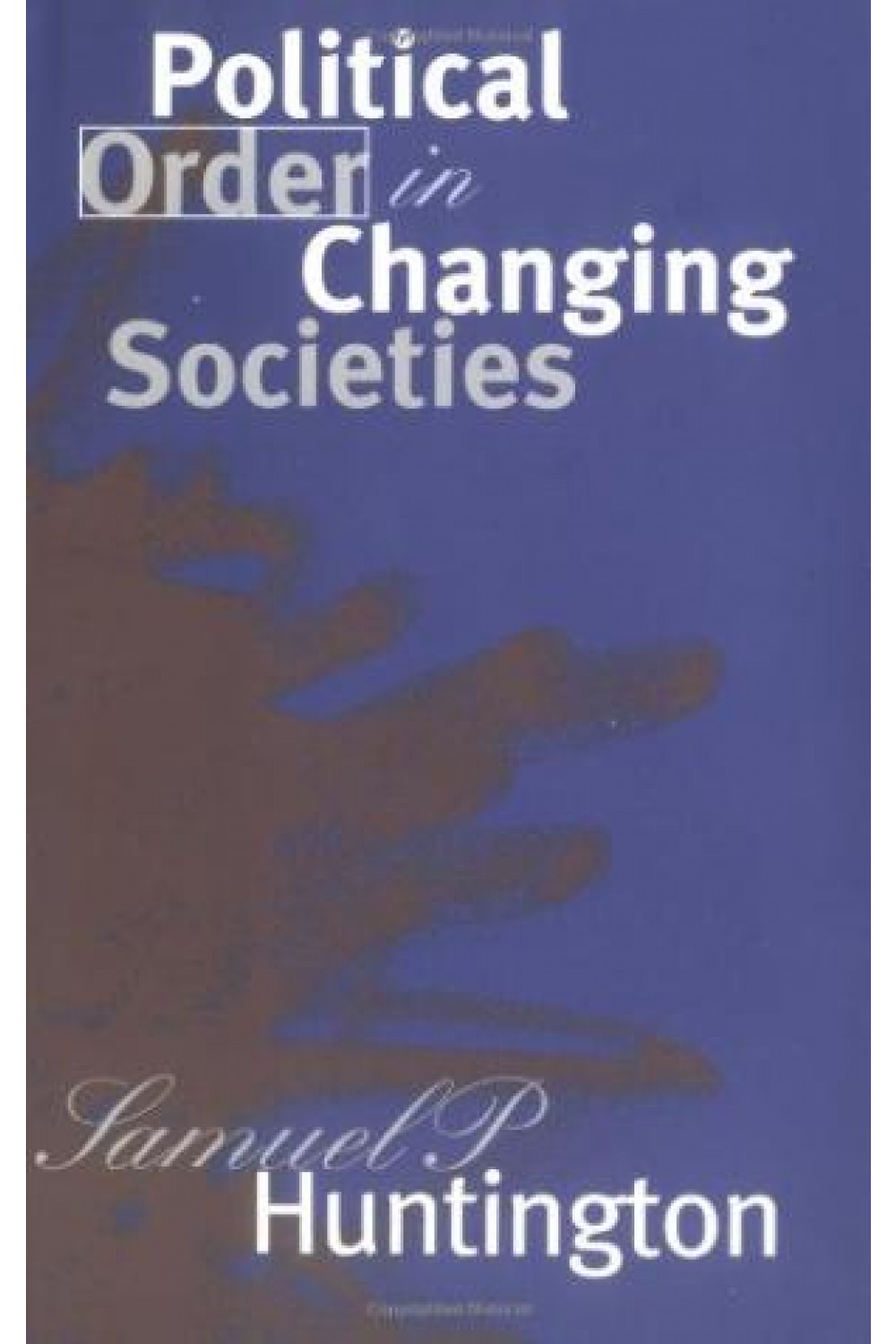
他的答案是,1960 年代是一個「對信條狂熱的時代」;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文化每隔幾個世代就會爆發這股狂熱,而它根源於英國十七世紀的內戰;新大陸在 1740 年代的新教徒大覺醒運動(Great Awakening)時也有過類似經歷。而 1960 年代,縱然充斥毒品和性,但杭亭頓卻認為這個時期的示威遊行人士根本是清教徒,他們之所以充滿憤慨,只是因為覺得學術教育罔顧我們的理想。正是對那些可能永難得以實現的理想懷有希望,而導致美國政治裡的極度痛苦。
一如 1950 至 1960 年代的美國,十七世紀初期英國處於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變遷的劇痛之中,甚至平民和仕紳都對逐漸喪失人情味的政府同感失望。結果就是清教徒起義反對王室,希望創立一個以道德為根基的社會。最後以保守的王政復辟告終。一世紀之後,大覺醒運動也是清教徒再一次的復興運動,因為美國的福音主派,滿懷身先士卒的樂觀主義又不滿現狀,於是遍布新英格蘭為靈魂而戰。
杭亭頓寫道,大覺醒運動「留給美國人民這個信念,那就是他們參與了一次努力確保惡終不敵善的義舉」,其結果是杭亭頓和其他人所謂的「美國信條」(American Creed)應運而生。這項信條成了我們國家身分認同的試金石,因為在我們國家初期區區數十年的歷史裡,幾乎沒有什麼能將我們和我們的英裔表親們做出區隔。
對信條忠貞不二,能讓外來移民一代又一代快速美國化,而同時也保有他們的種族文化元素。和其他的國家信條不同的是,我們的具有普世價值,是民主的、主張平等主義,也是講究個人主義的。1820 至 1830 年代的傑克遜民主時代是個對信條狂熱的時期,而在二十世紀之交的民粹─進步主義思想也是如此。
「反對威權、質疑政府乃最危險的威權具體化,是美國政治思想的中心主題。」杭亭頓寫道。這是真的,不妨看看我們的極端主義團體。歐洲不論左派或右派皆自古以來嚮往富強的國家,但在美國,不論左派右派的激進分子總是要求更多的「主權在民」(popular control)。
確實,這個在 1960 年代必須和外患周旋的機構,備受激進分子嚴厲指責。「威權的傲慢,被道德的傲慢取而代之。」杭亭頓寫道。勞動階級和工人階級認同老左派(Old Left),可是新左派(New Left)卻對「勞動階級避之唯恐不及,對道德主義的壓迫還更甚於思想」。杭亭頓引用民主社會黨學生領袖所說的話來說明新左派,「始於道德價值,奉為毋庸置疑」,儼然處於最純粹形式的清教主義。
信條狂熱所造成的後果是憤世嫉俗漠不關心,繼而導致保守主義;信條狂熱讓政府與社會守住它們達不到的標準。然而,杭亭頓相信,信條狂熱正是美國偉大的精髓所在。讓官員與制度守著不可能達成的標準(沒有其他國家這麼做),美國得以定期透過發展而非革命來改造自己。下一次的信條狂熱期會是何時呢?「權力如今被視同企業。因此下一次信條狂熱爆發時,可能是為了反抗霸權企業的資本主義。」
七
在歐美,1990 年代初期是個樂觀主義,甚至是志得意滿的時代。剛剛贏得了冷戰。新保守派認為民主選舉和市場力量被釋出,將能改善每一個地方的生活。自由主義分子認為,權力政治和巨大的國防預算,是歷史的遺跡。新聞報導預告著聯合國滋長的影響力與效力。新的跨國性掌權人物紛紛崛起,都是些傑出的學者和商界領袖,他們相信這個世界就要開創出一個真正的全球文化。
當時,杭亭頓發表了一篇文章〈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這篇文章刊出在 1993 年號的《外交》雜誌裡,構想來自杭亭頓某一種研討會;在那次研討會裡,因全球化而統一的世界範例,在課堂討論中受到質疑。在少數教育程度極高的掌權人物之外,幾乎找不到證據顯示有任何一種普世文化存在。
比方說,美國與中國事實上可以彼此更輕易地進行溝通,但這個事實並不代表它們就會更願意達成一致的看法。的確,全球的大眾傳媒都把焦點放在一些地方,例如約旦河西岸地區(West Bank)和北愛爾蘭,但這往往讓誤解更加嚴重。杭亭頓之前所持的意見:貪腐有時候是好的;民主政治和獨裁政治的差異,比我們所想的小;1960 年代的激進派分子是清教徒。
若考慮一下,對這些意見不以為然的那些反對者的本質,〈文明的衝突〉一文實在不應該會造成騷動。鑑於後來發生的事,杭亭頓的學位論文似乎再尋常不過,真正的先見之明注定出乎意料。
我的假設是,在這個新興世界裡,衝突根本不是來自於意識型態也非經濟問題。介於人類之間的巨大隔閡,以及主要衝突根源,將會是文化。民族國家仍將是世界事物中最強而有力的角色,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發生在民族與不同文化族群之間……現代世界裡衝突發展的最後一個階段,將會是文化之間的衝突。
可是這些字眼確實攪亂了一池水,瞬間引爆憤怒的回應,以及純粹對杭亭頓所言產生的盎然興趣。〈文明的衝突〉被翻譯成二十六種語言,全球各地召開了許多學術會議來討論這篇文章。「和杭亭頓先前的著作不同的是,」布里辛斯基告訴我,「這篇文章的標題說明了一切。因此大家在沒有閱讀文章本身有趣的見解前,就對吸引人的標題做出了反應。」
在大專院校、豪華旅館和一大堆新興郊區住宅之外,這個正因社會與文化新的緊張關係變得紊亂的世界裡(新的政治衝突高升),杭亭頓的論述對生活見多識廣的掌權菁英構成極度威脅,因為他們被隔絕在杭亭頓所描述的真相之外。尤其對於第三世界的掌權人士,要他們承認杭亭頓指出的真相,無異於要他們承認,他們在各自社會裡備受尊崇的地位岌岌可危。
杭亭頓不僅僅指出世界有些國度是無政府主義狀態,也說出了非洲與亞洲瀰漫著災難,許多分析家願意承認那一點,即使他們拒絕承認它言之有物。杭亭頓也說了,共產主義終結無望,意味著自太古洪荒以來始終屬於強權政治產物的領土爭奪,也永無終結之日。
因此,自由主義想要透過普世價值達成世界一統,注定要胎死腹中。對那些曾以為冷戰終了代表世界危機降低的人來說,這種思維簡直是奇恥大辱。對〈文明的衝突〉所做的許多評論,都只不過是價值判斷,例如「道德上是危險的」、「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lling prophecy),而不是實質的爭論。
不過也有一項攻訐是有實質根據的。這個核心指控是:杭亭頓過分簡化問題。舉例來說,伊斯蘭世界並沒有統一。各自為政的穆斯林國家往往彼此征戰或互相譴責。
杭亭頓稍後在 1993 年號的《外交》雜誌回覆了他的批評者,重申簡化正是重點:「當大家認真思考時,他們會抽象地思考;他們會想像稱之為概念、理論、模式、範例簡化後的真實圖像。威廉.詹姆斯曾說,若無這樣的智力建構過程,就只能獲得『生機蓬勃卻鬧哄哄的迷惑』(blooming buzzing confusion)。」杭亭頓指出,冷戰的範例並不能用來解釋 1945 至 1989 年間的許多紛爭和其他發展;雖然如此,它所累積出的事實也比其他範例好。
處於有如此多的大專院校教師和知識分子懼怕受到其他教師與知識分子攻擊的一個時代裡,大家寧可共同放棄精妙見解以策安全,但杭亭頓卻宣告著,而且捍衛著,學者有義務用嚴峻而概括的字眼說出他真正所思所想。
在由他的文章衍生而成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6)這本書裡,杭亭頓提出了豐富的其他見解。他陳述了,當西方世界歐美引發了意識型態之爭時,東方世界引發了宗教之爭,而他也解釋了宗教如今對國際局勢威脅性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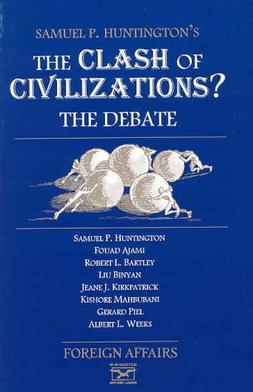
該書研究國家如何形成,堪稱杭亭頓最重要的力作。在十四世紀時,阿拉伯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曾在他的《神學緒論》(Muqaddimah)中描述,沙漠的游牧民族,因為渴望定居生活的舒適,才會活力充沛不斷進行都市化,而這個概念後來被強盛的王朝採用。杭亭頓把這個故事繼續說下去。他描述,都市發展如何帶來新的不穩定模式,包括起起落落和革命動亂,這些又導致要打造更多複合式機構。
《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雖然寫於三十五年前,但至今仍是發展國家再建立穩固、有作為政府,在一個全球化時代裡會面臨什麼問題的清楚準則。
這本書一開始就是一段大膽的聲明:
各個國家當中,最重要的政治差別,不在於他們的政府形式,而在於它們的政府程度。民主政府與獨裁體制的差別,不如那些政治體現了多數人、族群、合法性、組織、有效性和穩固性的諸國,和那些政治欠缺這類特質的國家,差別大。
對那些已經歷過社會動盪,例如在奈及利亞和迦納,縱使它們也有選舉制度,以及經歷過相對開放與公民穩定性的較專制社會,比方說突尼西亞與新加坡,杭亭頓提出的這項認為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差別不如其表面所見的論述,在上述情況中一點也不意外。比起其他大學教授,杭亭頓比較注重實際層面的真相。
綜觀其生涯,他在做研究時是個非典型學者,喜歡引用現場觀察者的說法做注。「近來的事件沒有學術性資料出處可引,」他告訴我,「只有學術意見。」
《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的核心論述是,儘管我們可能在本能上相信,但美國歷史經驗並不適合用來了解發展中國家遭遇的變遷。「美國人相信真善美,」杭亭頓寫道,他們「假設所有好的事物要結合在一起」,包含社會進步、經濟成長、政治穩定等等。
在 1950 年代時,印度擁有的國民平均所得,是阿根廷和委內瑞拉的十分之一,可是它的政局更為穩定。
這是為什麼?
部分原因是一些「壞事」所致,也就是印度的文盲。印度的文盲有助於民主政治穩定,因為鄉村的文盲對政府的要求,少於一個能讀書識字的都市無產階級。文盲或半文盲只要會投票就行;識字的人會搞組織,還會挑戰現存體制。杭亭頓主張,儘管它的貧窮來自於諸多不尋常的因素,例如選民教育程度不足,加上教育程度高的掌權人士多得足以管理現代化政府機構,但印度的民主政體穩定了數十年。如今在印度較低層的中產階級裡出現一群識字者,該國的政局也已經變得比較動盪。
杭亭頓接著說,美國思維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歷史一直都只教導我們如何限制政府,沒有教我們如何憑空打造它;正如同我們的國安,也是承襲自十七世紀的英國,是得利於地理優勢,絕大部分非努力所得。憲政體制是關乎控制威權,綜觀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之前的共產世界,其困難是在建立威權。「問題不在選舉制度,」杭亭頓寫道,「而是在創造組織。」
在政治進步的國家裡,忠誠的對象是機構,不是對族群。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是經過長期都市化與啟蒙運動後的成果,可是這樣的歷程本身可能會導致不穩定。他觀察到,「人民啟蒙得愈快,推翻政府的頻率愈高。」法國與墨西哥革命,並非起於貧困,而是起於支持社會與經濟發展。如今全球各地掌權人士所擁護的經濟成長,在帶來政治進步的社會之前,將會先導致不穩定與動亂。
在國際研討會中,專家經常對貪腐問題束手無策。《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表明了,深獲擁護的極度現代化一開始就會造成貪腐。十八世紀英國曾出現史無前例的貪腐,這可歸咎於工業革命;同樣狀況也出現在十九世紀的美國。
然而在這個發展階段的貪腐,可能是有用的,杭亭頓認為,而且不應該自以為高尚地加以蔑視,因為貪腐提供了方法,將新的族群同化到體制內。舉例來說,出賣議會席次,就是民主政治初期階段典型的貪腐,而且還是對抗議會本身的最佳武器。杭亭頓指出,比起暴力相向,貪腐是較不極端的疏遠手段:「相較於襲擊警察局的人,使體制內警官貪腐的人,比較容易被體制認同。」
在十九世紀晚期的美國,立法機構和市議會在公用設備、鐵道公司和新的產業裡無所不貪,但同一股力量也激勵了經濟成長,幫助美國成為世界強國。在印度,若沒有賄賂,許多經濟活動將會癱瘓。適度的貪腐可以解決反應遲鈍的官僚,促進進步。
同時,杭亭頓解釋道,現代化與貪腐的騷亂會帶來一股清教徒式的反應。卑鄙的交易對成長是必要的,政局穩定會受到狂熱分子聲討,把政治程序變得不合法。《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出版後十年,伊朗就曾發生這樣的事。
杭亭頓說,美國難以了解世界其他地區的革命動盪,因為它從未經歷過真正的革命。它有的只是遭遇了一場獨立戰爭,甚至還不是一場「原住民抵禦外來征服者」的戰爭,像是阿爾及利亞人對抗法國人那樣,而只不過是一場移民者和祖國的對抗之戰。真正的革命與此截然不同,杭亭頓一語道破──糟透了。
但幸虧革命很少見。即使第三世界貧民窟裡的無產階級持續激進,中產階級會逐漸變得保守,也更願意為現存的秩序而戰。在 1960 年代時期所寫的文章裡,杭亭頓就曾描述了二十世紀初期的世界。一旦革命真正爆發,持續的經濟剝削「很可能對革命的成功與否至關重要」。
認為受到經濟制裁而引發食物短缺和其他困境,將會導致如海珊或卡斯楚等革命政權遭到推翻,這種想法根本胡說。物質上做犧牲,雖然在正常情況下難以忍受,但在革命狀況下卻是個意識型態獻身的明證:「革命政府可能會受到生活富足的侵蝕,可是它們永遠不會被貧窮所推翻。」如今在哈瓦那興建旅館的西班牙和加拿大建商,對如何削弱革命政權,應該比起美國政府更拿手。
杭亭頓從世界各地無數例證,來描述革命、君主國家、司法官政體,還有封建制度的問題。他提出了我們的時代裡一團糟、棘手又複雜的全貌,甚至加以有效提煉並提綱挈領。
他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裡用一句話表述了整個二十世紀裡軍人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在寡頭政治裡,士兵是激進分子;在中產階級的世界裡,士兵是參與者和裁決者;隨著大眾社會演變……他會變成保守的衛士,守護著現存的秩序。」土耳其軍隊數十年來的角色轉變,或埃及軍隊的地位變遷,從未有人寫過。誠然,社會愈落後,軍人的角色就可能愈進步,而且歐美應該更小心以對想要用平民政治家來取代軍人一事。
美國很有信心能為它自己從事「民主體制」改革,但這份信心卻放錯地方。杭亭頓寫道:「改革可以是革命的催化劑,而不是革命的替代品……偉大的革命都要歷經許多改革階段,而不是發展停滯和壓制的階段。」無論如何,在經濟不發達的社會進行改革之所以奏效,不是因為透明度和更廣大的公眾參與,而是一如土耳其(第一任共和國總統)凱末爾那樣,因為「迅速且攻其不備─那兩個古代的戰爭原則」。
倘若一個改革方慢慢地被揭露,那麼言論自由就會剖析它,挑毛病反對它。由於社會會有某個區塊支持某個改革但不支持另一個,因此改革者必須祕密進行他的工作,把一些議題從其他的隔離出來,並且往往不要仰賴媒體,而是要利用社會裡所存在的傳播缺口。
然而大眾傳播運作它們自己的魔術,連杭亭頓也在稍後出版,對《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所做的一個很長的結論《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1991)裡,也對此坦承不諱。對杭亭頓嚴厲批評的法國學者皮埃爾.哈斯納(Pierre Hassner)稱該書副書名為「普遍主義者和好戰分子的親民主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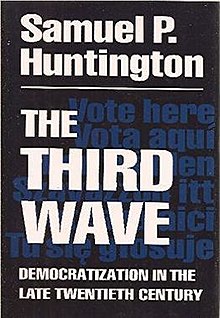
杭亭頓向來都是自由派,可是他是一個拒絕為了得來不易的名聲而撤退到輕鬆老生常談的人。他的著作彰顯著學術生涯應該是但往往不是:由職業安全性所提供的自由,擁有自由去表述那些不流行、有違常理、不受歡迎又大膽的觀點。
六
1960 年代帶給杭亭頓一些嘗試的機會。他被反覆叫囂的遊行示威群眾追逐著,在麻省劍橋公園裡的哈佛園(Harvard Yard)跑來跑去;對方都在《哈佛克里姆森報》(Harvard Crimson)上讀到他和詹森政府的關係。杭亭頓工作的國際事務中心被占據,接著被投擲汽油彈。杭亭頓的小兒子有一天早晨醒來,看到前門被塗寫著「戰犯住在這裡」的字眼。
杭亭頓並未因忌憚威嚇而不再出任公職。如前面所說,他入閣卡特政府,並協助卡特總統制訂外交政策,表述我們的人權理想;這並非是姿態柔軟的假惺惺,而是質疑蘇聯許多政治問題的一項鋒芒畢露的利器。身為國安計畫的協調人(這份差事是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為他量身打造的),杭亭頓同時也負責撰寫「十八號總統指令」(Presidential Directive 18);該文件對美蘇關係做了全面審視,有助於刺激國家安全會議起而與莫斯科進行調解。
在悲觀主義盛行的年頭裡,當蘇聯染指了安哥拉與衣索匹亞後,再加上聯合國掌握在左翼第三世界的多數派手上,杭亭頓因此打造了一支特種部隊,來針對蘇聯人與美國人在製造武器、蒐集情資、經濟研究與其他領域的研究,進行評估。他和他的團隊得出的結論是,蘇聯的優勢難以長久,而歐美終究會獲利了結。他們強烈建議,美國應成立軍隊,在波斯灣部署一支快速應變部隊。在卡特任期的最後兩年,以及在雷根任內的八年之中,那些建議都付諸實現。
唯有在 1981 年時,杭亭頓才出版了一本關於 1960 年代的書《美國政治:不和諧的希望》(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1981)。歷史上絕大多數的世代始終都是組織良好的,喜歡有他人指導,在日常生活中運轉。杭亭頓問道,為什麼有一些世代偏偏不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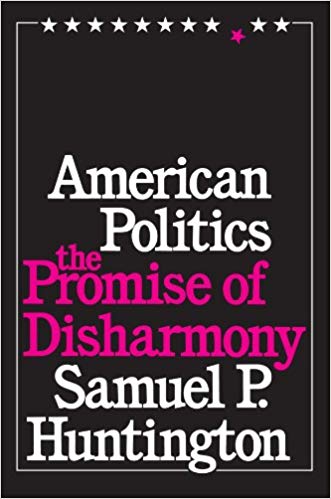
他指出,違反直覺的是,由於共產主義制度是中歐的思想體系,因此蘇聯在哲學思想上比較接近西方,而非接近推翻它的東正教俄國。杭亭頓提醒我們,和歐美與伊斯蘭之間的陳年舊戰相比,冷戰不過是短暫飛逝的一樁事件。在中古時代,穆斯林的軍隊進犯伊比利半島,深入法國之遠,並穿過巴爾幹半島遠赴維也納大門。如今類似的侵犯過程,人口而非軍隊的,正在歐洲發生中。
「未來的危險衝突,」杭亭頓寫道,「很可能會爆發在西方的自大、伊斯蘭的不寬容,以及中國的獨斷之間。」
自從杭亭頓的文章與著作問世以來,數年間北約已經擴張到三個新教──天主教國家裡,同時卻把好幾個東正教國家拒之門外,因此北約的地圖,雖有一些例外,但很類似於中古時代的歐洲基督教世界。在此同時,隨著黎巴嫩、敘利亞和巴勒斯坦領土上伊斯蘭壓迫的幽靈高漲,基督徒持續逃往中東。美國的教會團體,不論自由派和保守派皆然,都一致團結支持基督徒為中國人權而戰,以及起而對抗穆斯林在蘇丹共和國屠殺基督徒。
杭亭頓的著作之所以能引起持續迴響,在於他有能力用一個概括性的理論,對這些和如此之多的其他現象做出解釋。同時,在冷戰期間告訴我們蘇聯體制基本上是穩定的那些研究蘇俄政體的專家們,如今何在? 還有,在 1960 至 1970 年代間曾預測那些飽受戰爭蹂躪的地區將會成長且發展的非洲專家們,又在何處?
將杭亭頓的思想套用到現今因恐怖攻擊紐約與華府所造成的危機又如何呢? 他不願對美國的特定政策應該追求什麼說三道四。但他曾警告過,期待根本不像我們的人很明顯的變得更像我們,毫無意義;這份出於天性的善意,只會造成傷害。
「在這個愈來愈多種族紛爭與文化衝突的世界裡,歐美相信西方文化具有普遍性,會造成三個問題:這是謬誤的,這是不道德的,而且這是危險的。」早期由美國造成的戰爭裡,所給予我們的終極告誡就是,必須要專注在恐怖主義慘無人道的事實上。
他觀察到,賓拉登就他本人而言,顯然希望煽動伊斯蘭與歐美的文化衝突。美國必須防範這件事發生,要以跨越文化界線的方式召集盟邦來對抗恐怖主義。除此之外,美國必須借此機會完成兩件事:首先,鞏固歐美諸國更加團結;其次,努力從現實面上,透過其他民族的觀點更了解這個世界。這個時代,我們面對目標時要抱著不屈不撓的謙遜態度,而且我們要用絕不容寬貸但有分寸的方法。
結尾時他又加上攸關我們生存世界的一段話:「這是個危險的所在,這裡有一大群人怨恨我們的財富、權勢和文化,而且猛力反對我們努力想勸服或強迫他們接受我們對人權、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在這樣的世界裡,美國必須學會辨別誰是會站在我們這邊的真正友邦,我們能與之同甘共苦者;也要辨別誰是投機取巧的同盟國,我們和對方有一些但不是全部利益與共;哪些是戰略夥伴或競爭對手,我們與對方關係複雜;哪些是敵人、是競爭者,但是和我們有協商的可能性;還有哪些是絕不鬆懈、想盡辦法摧毀我們的,除非我們先下手為強。」
八
杭亭頓從未將良善的意圖與分析的清晰性混為一談。他知道,政治科學家工作未必是要改善這個世界,但必須說出他對事情的想法是什麼,並且還要開立行動處方,來為他的政府謀求利益。
在刊登於 1997 年號《外交》雜誌裡的一篇文章〈美國國家利益的腐蝕〉(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裡,他寫道,「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國安威脅加上道德難題,將會需要美國人再次投注巨大資源來捍衛國家利益。」他又說,比起改變對我們國安不重要、不易更動的外交政策事業,這樣的新動員行動,若是從「低的基礎」來執行,會更輕而易舉。因此,相較於深陷於太多地方,不論是為了「特殊主義的」(particularistic)的政治遊說,抑或某些人權宏大概念,來如何整理這個世界。總之,對世界採取克制的處理手法,可以讓我們在緊急狀況時能更敏捷地動員起來。
真正的保守主義不可能追求崇高的信條,因為它的任務是要捍衛現存的一切。保守主義的困境就是,保守派的合法性只能從合乎正義的事件而來,但自由主義人士在每次被證明他們大錯特錯時,總有一堆通則可供依靠。杭亭頓始終都懷抱自由主義理想,但他知道這樣的理想沒有權勢難以存活,而且他也知道權力必須細心呵護。
若美國的政治科學有留下任何永垂不朽的知識分子紀念碑,那麼杭亭頓的著作將是它的一根支柱。在《美國政治》(American Politics)結論有一段文字,我一直認為最能彰顯杭亭頓不朽的判斷力與政治敏感度的精髓:「批評家說美國是個大謊言,因為它的現實遠未達到理想。美國不是謊言,是失望。但它之所以是失望,唯一原因是它同時也是個希望。」

13 世紀時的威尼斯商人馬可孛羅曾走過絲路,他看到的絲路是一條複雜、凶險、混亂、國家與民族界線不明、看似一統卻又充滿分歧的世界,而這恰足以定義當今歐亞大陸的形勢。
本書作者認為新時代的關鍵不是在海上,也不是在解構了的西方,而是在這片廣大古老無邊際的歐亞大陸上,這塊馬可孛羅曾走過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