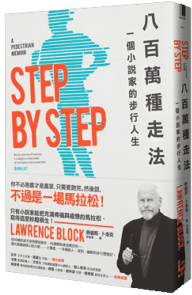我們走過西班牙已經是十六年前的事情了,現在我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部分,不是體能上的嚴酷考驗,也不是我們沿路看到的風景和遇到的人,甚至不是這樣一趟朝聖之旅為靈魂帶來的洗禮──不管是能有什麼洗禮。這一切和我們整個拋下原本的人生、完全孤立地度過三個多月比起來都相形失色。在那段期間,我們的全世界就是眼前的環境,就是聖雅各之路的世界。
在當今這個手機和網咖充斥的世界裡,很難想像我們當時與世隔絕到什麼地步。沒人有辦法聯絡我們,而且我們在出發前就決定好不聯絡任何人,甚至連試都不試。我們在一路上的某些地方或許可以打電話,但打了要幹嘛呢?確定一下被我們拋在腦後的人都還好好活著?

如果出了任何差錯,我們能做的少得可憐。就算家裡有急事要我們立刻打道回府,對置身西班牙某個偏遠地區的一對步行者來說,中斷行程也不是那麼容易。假設家裡一切安好不是容易得多了嗎?
容易得多,但絕非確實可靠。因為我們上一次在西班牙時,就接到美國打來的一通電話,把我們送上了下一班回家的飛機。
暫且讓我們回到安達魯西亞快車,也就是第一次聽說這條朝聖之路並立刻知道我們一定要去的那班列車。對我們而言,在那個當下,我們就已立定志向。但要過了將近三年之後,我們才真的開始奔向理想。
在希洪,我們這一組國際推理作家團煞有介事地做做樣子,參加了一星期的「黑色星期文化節」。那是一個以黑色電影和文學為主題的西班牙節慶,不過純粹的狂歡顯然是真正的目的。琳恩和我玩得很愉快。這一週將近尾聲,我們接獲通知說我媽出了嚴重車禍。(我表哥大衛.納森不知用什麼辦法找到了我們。有鑑於地球上沒有人知道我們在地球上的哪裡,大衛真是非常之高招。)
第二天一早,我們在無從得知她是生是死的情況下飛回家了。她還活著,但奄奄一息,而且在我們抵達後不久,她就陷入昏迷,不省人事地在加護病房待了整整一個月。我們搬進她的公寓住,白天都待在醫院,直到情況變得很清楚,她的狀況已經穩定了,而我們什麼也不能為她做。
我們開車向西,去了俄亥俄州的水牛城,拜訪了在黃泉村的朋友,再開了回來。然後,當她甦醒過來被轉送到另一間病房時,我們就在那裡。
她恢復意識的這件事相當令人困惑,對她自己甚至還比對我們而言更困惑。在某一刻,她無意識地決定要活下去。如今恢復意識之後,她顯然對那個決定並不十分高興。她沒有很想留在這個世界上。
陪在她病床邊的時間裡,我滿腦子都是史蒂芬.金的小說《寵物墳場》。在那本書有名無實的墳場當中,那些被埋葬的死者可以重新活過來,但他們和本來的樣子並不一樣。

有那麼一陣子,我媽感覺就像是從那樣一個地方回來的。她的性格大變,而且不是變好。她對護士大發雷霆,完全就是無法相處的一個人。
我後來明白到,恢復意識不是把電燈開關打開這麼簡單的一件事。那是一個更為循序漸進的過程,事實上,這個過程不只是恢復意識,也是恢復自我。隨著一天天過去,她確實越來越像她自己。她的腦力回來了,她的個性回來了,甚至她的幽默感也回來了。
三年後,當我們在為朝聖之旅做準備時,我很難不想到上次去西班牙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一次,就連像我表哥大衛那麼足智多謀的人,都不可能想出辦法聯絡我們。
我很擔心會出什麼事,而琳恩和我將無能為力。等我們知道的時候,甚至已經來不及採取任何有用的行動了。我母親的健康狀況很好,儘管她永遠無法恢復到和那次車禍之前一樣好。但她將近八十歲了,琳恩的母親也是,還有──我和一個朋友聊了聊,對方問我確切是在怕什麼。
「這個嘛──」我很不願說出我的恐懼。「嗯,啊,怕她們其中一個會死。」
「是有這個可能,但有一件事你必須切記。」對方說。(我不是故意要含糊其辭;我對這次談話有鮮明的記憶,但不記得是和誰談的。)
「哦?」
「如果她們當中有哪個死了,等你們回來的時候,她也還是死的。」
我覺得這個論點的邏輯無懈可擊,並立刻就向琳恩報告,她也像我一樣認同。於是,我們出發前往西班牙,跟我們的日常生活說——唔,就算不是說「掰掰」,那肯定是說「hasta luego」。
這趟徒步之旅最重要的一堂課,或許在於斷絕聯繫,放棄聯絡的需求。我想我們放掉的是控制的錯覺。我們不能控制在我們離開時發生的事,就算我們每天打電話回家五次也一樣。有的人相信保持聯絡能讓他們握有相當程度的控制,就像那些藉由閱讀報紙來掌握國際政治的人一樣。
而當我們在 7 月 23 日抵達目的地之後,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從我們在聖城的旅館打電話回家。我得知家裡沒什麼新鮮事,每個人都好好的。
我們永遠也不會再去一次了。
聖雅各之路還是在那裡,它已經屹立不搖一千多年,而我不認為會再也沒人去走。就算教堂沒了,朝聖者還是會一路來到聖城。(儘管我們碰到的旅人有的是信徒,但絕大多數並不是。許多人來這裡只是為了冒險犯難,還有很多人似乎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走上這條路,但就像我們一樣,只覺得這是一件他們想做的事。)
所以,那條路還是在那裡,朝聖者還是走在那條路上,他們也還是有庇護所可住。你會覺得我們大可再去一次,只要有意願的話。照理說,這件事對我們而言應該更容易才對。我們倆的母親都過世了,女兒們也長大獨立了。我們的手頭比較寬裕,甚至大可空出三個月不做任何能賺取收入的事。
我們比較老了,而且明顯沒那麼活力充沛,但這項不利條件相當程度地被我們各自會做的體能訓練抵銷了。我是競走和參加比賽,琳恩固定上健身房做運動。我們倆都買了比較好的背包,整體而言也裝備得更為齊全。如果一開始的坡路很累人,那麼,接下來一路上我們會越練越強,就像十六年前那樣。
那麼,究竟有何不可呢?
因為我們沒辦法應付那種孤立狀態。
喔,我們是受得了,但我們會忍不住,因為世界已經變得不一樣了。
要把我們的手機丟在家裡並不難。除非要出城,我很少把手機帶來帶去,何況我們的手機在西班牙反正也不能用。當然,那裡一定有賣手機,每一座我們行經的城鎮都會有,但或許我們能充分規範自己不為所動。
但這些城鎮也一定每一座都有網咖,我能忍住多久不去查看我的電子郵件呢?
要到我們從西班牙回來三、四年之後,我才有了第一個電子郵件信箱,如今卻很難相信我曾經可以沒有它還活得好好的。
如果說這個世界變了,好吧,那麼我們也變了。我很習慣和一大票親朋好友多多少少保持聯繫,我很習慣可以要查什麼就查什麼,而且想找到誰就幾乎都能找到──透過Google。
我並不樂於依賴網路世界到無法離開它三個月的地步,但我怕事實可能就是如此。
喔,我想如果非去不可,我們還是辦得到的。但我們事實上就是沒有非去不可的理由,而且我們早在一九九一年就已經去過了。
我很高興我們在有機會時真的去了。

徒步走過迢迢長路──地理上實際的一大片土地──具有某種令人蛻變的效果。看著西班牙的地圖,誰會認為這是一個有可能靠雙腳橫越的國家?
但到了走完全程的那一刻,我們完成的正是這樣一件事。一次一天,一次邁出寶貴的一步。
隨著里程的增加,我們也從中得到很大的力量。有生以來,為了從一個地方抵達另一個地方,我們都要依賴除了自己之外的東西。無論我們的交通工具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無論是搭乘公車、飛機,還是開著買來或租來的車,都是某個並不真正由我們控制的東西載著我們移動。我們沒動,是汽車、公車或飛機在動,我們只是那上面的乘客。
在西班牙,我們是貨真價實靠自己的力量移動。當我們很偶然地停下來想一想時,總會很驚訝自己真的辦得到這件事。十年前,在奧勒岡州,當我決定不要買一輛自行車時,我甚至從沒想過我也可以用走的。我們能想像自己做這種事,但想像和行動是兩碼子事,無論那些心靈勵志大師要你相信什麼,我們從沒想過自己真的會採取行動。
我們不是為了健康或減重而走,但兩者都是這趟朝聖之旅必然的結果。我向琳恩保證過,走路會讓她更強壯,並進而能夠完成這段旅程。就算她不相信我,事實真的就是這樣。抵達聖城時,我們倆都強壯許多、苗條許多,整體的狀況也都比較好。而且,我們由衷信奉起走路這件事,認為它不只本身是一個愉快的活動,也附帶龐大的益處。我們向彼此打包票,這會是我們往後的人生中持續進行的一件事。
於是乎,我們在聖城度過了愉快的幾天,吃得很好,遇見了我們一路上碰到的朝聖者,像是那個我們只有耳聞的聖家庭。我們從聖城搭火車到里斯本,途中中斷旅途,在維戈過了一夜。我們本來安排要在里斯本待一星期,也還滿喜歡那座城市的。但在我們的心目中,這趟旅程在走進聖城那一天就劃下句點了。里斯本所有的教堂、瓷磚工廠和葡萄牙怨曲都不足以抓住我們的注意力。我們撐了四天,接著就改了機票,搭上飛機回紐約。

我們卸下行李,沖了澡,調了時差,做了所有離家很久之後要做的事。我們知道自己遲早會重拾長途步行大業。
有趣的是,這件事從來沒有發生。
我猜事情往往是這樣的。某一件活動格外令人心滿意足,你於是想要堅持下去,讓它成為人生中始終保有的一部分。它是那麼重要,那麼不可或缺,你無法相信它不會繼續下去。
這就是為什麼出國玩的遊客會帶食譜書回家,他們深信自己會想要煮出在孟加拉、多哥或特羅布里恩群島享用到的佳餚。或許有些人真的煮出來了,但我有預感多數人做的事就像我和琳恩一樣,那就是把烹飪書束之高閣,再也沒看它一眼。
畢竟,我們以前就是這麼對待照片的,在我們捨棄徒增重量的相機之前。我們在西非拍了沒完沒了的照片,並把照片沖洗出來,然後它們就原封不動地在一個盒子裡待了幾年。接著,有一天,琳恩突發奇想,買了一本相簿,把所有照片都放了進去。她把相簿放上書架,從那之後,我們倆都還沒看過它。
照片是意圖抓住某個經驗的一種嘗試,彷彿這樣就能將時間凍結在某一刻,永遠擁有它。從第二四二街走回家不也一樣嗎?我們想要抓住某個經驗,不是透過看照片,而是透過繼續去做那件事,但這樣是沒有用的。你可以拍照,你也可以走很遠的路,但無論如何,這段經歷都是一時的事,過去了就是過去了。設法保有它就像在畢業後設法保有在校時期的樂團。
所以,我們回到家,回到我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