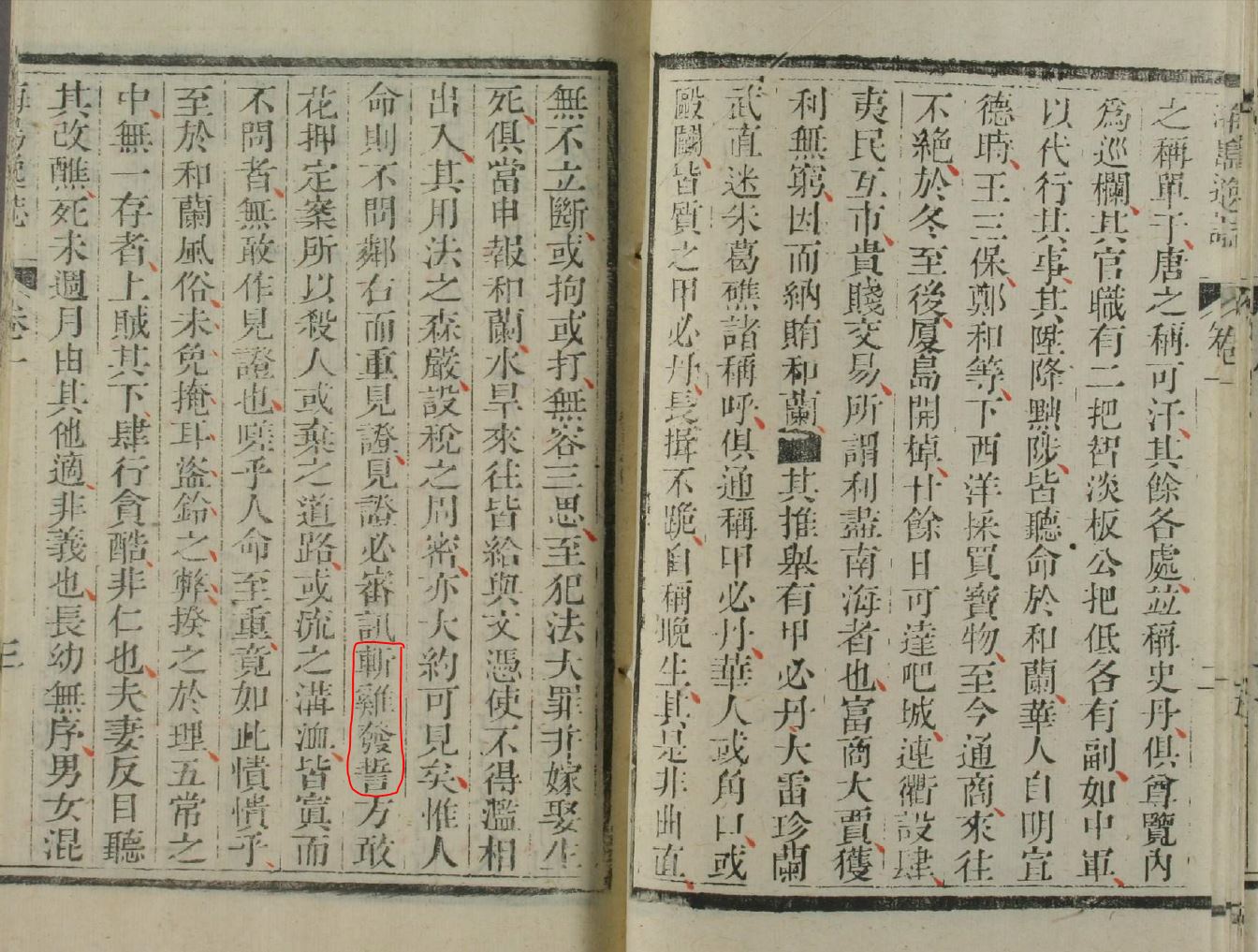2015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1948 年出生於白俄羅斯,明斯克大學新聞學系畢業後,便投身於記者工作,輾轉擔任過地方報社記者與尼曼文學雜誌特派員。但與眾不同的是,她的文體雖具文學性,卻無法被純然劃分,既承繼著俄國口述文學的傳統,又另行創立同時兼有報導文學、散文與呈顯時代真相文獻的「聲音小說」。
所謂「聲音小說」,是指以「人聲拼貼」方式,各階層訪述,一一追索人們成長的生命碎片,最後造就彷彿戰時千人針、佛門百衲衣,血淚交織的動人圖騰。這種眾聲喧嘩的複眼視象,引領讀者走入阿富汗戰爭、二戰、蘇聯解體或車諾比事故等重大事件,揭起那些血腥幕後不曾為人所見的膽戰心驚。
也因如此毫無矯飾的直視真實,戳破了官僚宣揚的謊言神話,以及亟欲掩蓋的諸多殘忍,使得亞歷塞維奇屢屢置身於被審判、控訴、竊聽,作品遭禁,且人身公開露面有所限制的窘境裡。最後經國際避難城市聯盟(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Cities of Asylum)協助,才轉居歐洲各地定居[1]。
亞歷塞維奇自言一生逾 30 年,都致力獻身於撰寫《赤色百科》(「赤色人」與「赤色烏托邦」百科全書)的寫作。此部宏觀百科,實乃關乎一個共產主義式「烏托邦」故事走向崩毀的敘述,共囊括有《車諾比的悲鳴》、《我還是想你,媽媽:101個失去童年的孩子》、《戰爭沒有女人的臉:169 個被掩蓋的女性聲音》、《鋅男孩》與《二手時間》等,企圖以一種寫實如繪的呈顯,去披露社會主義「想創設人間天堂卻反墮入人間煉獄」的哀戚。(以下先就 2016 年 10 月,臺灣已出版的三書介紹如下,後續再另行增補。)

《車諾比的悲鳴》是亞歷塞維奇在臺首部翻譯作,摹寫 1986 年車諾比核災過後的倖存者,人生隨之變形的慘烈。事故發生前後,政府將人民置身無知濃霧,利誘哄騙下,被驅動以強烈的愛國心或因公奉獻的情操,卻反落入死神收割的領土—前往防護措施未見周全的災難現場清理,等同任死神任意操戈。個體一一倒地,最後也導致家國無以復加的縫隙缺漏,傷害於是不可逆。
死者逝去,活者卻也生不如死。無法捨棄母土的戀家情懷,佐附核災傷殘的軀塊,不是使他們更加逼近死亡,便是輾轉逃離內,飽受失根與被排擠的悲傷,連孕育新生的希望都渺茫。日常生活裡,只剩下了絕望。
在各國暢銷的反烏托邦青少年小說裡,最常慣用末日災難敘事,作為青少年女主角,抗爭出逃成就英雄史詩的背景,如朱莉安娜.柏格特(Julianna Baggott)《純淨之子三部曲》(Pure Trilogy),便如詩如繪地呈顯末日核爆過後,英雄英雌的絕地逃生;然而亞歷塞維奇筆下,生命最為艱難的寫實,卻仍是官僚權力持續性的獨大,唯有人民陸續死去。平凡人物的側寫裡,既沒有英雄,也不曾勝利,重複累計的,是人民彷彿螻蟻赴死滅頂的無辜身影,誰也逃不出去。連倖存者控訴悲傷的耳語,都顯得那麼樣的有氣無力,被封閉。亞歷塞維奇耐心傾聽,起起落落鑽鑿那因傷與不幸而緊閉的心,才掘出這些悲傷無以名狀的生命秘密,重見光明。

《我還是想你,媽媽》是尋訪戰時失落童年與愛的人們,傾聽其表述,那些被時光膠囊重重封貼者,約莫二至十五歲之間,那時彼刻的稚眼/稚顏/稚言。烽火連天的征戰裡,他們接連失去父母,中斷學業,尚未成人卻已學會殺人,童年便是戰爭的代名詞,無有無憂無慮的喘息時刻,卻是被迫舉起搶桿,提早面對死亡暗影,還有難掩痛苦的愛恨生別離,最終只能在午夜夢迴,懷想母親,夜半啼鳴。
本書多是失去怙恃的慘劇,出征後等同不存在的父親,只得與母親相依為命,可戰火流離下,又難覓母親蹤影,未及成人,本該接受照料與哺育愛的幼童,卻反轉肩負起大人的責任,趕不及辨識自我,卻須有敵我之別,並在殘酷死亡的洗禮蛻變,家庭失能、過早擔負責任(小大人症候群)、殺人與生存鬥爭等,都將對幼童內心,造就難以彌補的創痛傷害,一輩子延續。
可是這些傷痛,在所謂正統的歷史扉頁上,都顯空白,亞歷塞維奇挑戰的是權威與學科的歷史,另行建構出 history/"his-story" 與權力發聲書寫外,失落的拼圖-—常處於受害者弱者而不被一顧的兒童女人。《戰爭沒有女人的臉》也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二戰期間,彈盡援絕,男人死傷慘重的絕境,近百萬的蘇聯女孩,被徵召上場,她們捨棄了女孩該有的梳妝打扮與甜美純真,婉轉峨眉一朝卻成了戰爭工廠下,重複性運轉的零件──狙擊手、砲兵、坦克兵、通信兵、機槍兵、游擊隊員、司機、空軍飛行員、傘兵、醫生、護士、戰地記者等。戰鬥民族的女子,巾幗不讓鬚眉,也有不輸男兒的熱血氣節與優秀執行力。
這種女為男用,從軍征戰的情節,彷彿中國長篇敘事詩中的花木蘭,更為後世各羅曼史,如廷銀闕《成均館羅曼史》(男裝赴考)與尹梨修《雲畫的月光》(女成太監),經典必備橋段,彷彿可一抒「安能辨我是雌雄」的熱血昂揚,或成為與高富帥熱戀相逢的命運契機。可不同於羅曼史的浪漫順切,《戰爭沒有女人的臉》只有軋實且無窮止盡的痛,如影隨形。
一腔熱血趕赴戰場的熱切,竟反使她們後續的生命墮入深淵,所有該擁有的全都失去,包含作為一個女人或戰士的聲音──「因為女人無法成為英雄」。戰場上,生生死死,陰陽相滅,不過一瞬之間,即便倖存回國,卻還有更多的殘酷在等待。不僅肉體殘缺與心靈斷裂,還被惡意標籤以淫亂不潔,人生最後僅餘孤獨終老的寂寞與戰事陰影的盤旋。書中記載,戰後女兵不是撕碎獎章褒狀,不欲人知,只怕為此受人歧視,否則就都孤身終老,屈住寂寞裡。歷經這諸多種種,要使她們回返社會已屬困難,又何況是社會隨勢反轉的無情?關係鍵結的斷裂,再也回不去。
關於二戰前後,戰事情勢的改觀,而予士兵有受欺遭騙的無所適從,在百田尚樹《永遠的零》或皆川博子《倒立塔殺人事件》等也可得見。百田尚樹《永遠的零》摹繪了強調赴死的愛國氛圍,不過是官僚體系自我中心與盲目政策的錯決,使得無辜士兵,命如螻蟻,枉送性命,僥倖存活者,也在戰後因親美政策而遭人摒棄,倍絕錯愕。完全不似宮崎駿《風起》,作為《永遠的零》反面,不見戰事的慘烈,只有追逐昇天夢想的堀越二郎,飛機性能研究的發明進展,充滿個人理想得遇實現的樂觀浪漫,卻不見成功的代價,有可能是千萬人的性命!
皆川博子《倒立塔殺人事件》教會學校權威者,也不過是隨風草偃的牆頭草而已。或許小至個人私事,大至家國戰爭,都俱有「一個真相,各自表述」的可能,然而亞歷塞維奇替讀者揭開的,是被蓄意掩蓋,且正統歷史長久失落的缺塊。並由此省思,「人活著,究竟為何,人存在的價值,又在何處得見」的生命議題。
戰爭中,不分敵我的一塊麵包分享,是人性的溫情,還是愚鈍?違背天性,被迫舉起槍桿,所執行的殺戮,是不是罪?愛國熾烈,由此背負傷亡血腥,歸國過後,社會卻只留下惡意排擠,這算不算背叛?在埃及來世文化中,曾有鷹頭神何魯斯(Horus)執行秤心儀式的傳說,由此明辨亡靈生前所為,各國死後審判,亦有所略同。那麼,這些受苦受難的煎熬心靈,又該被怎麼劃分,難道短短歸諸於「時代悲劇」便劃下句點?
耙梳世界經典名作,深思人存在的經典,如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的《變形記》與安部公房《沙丘之女》,人形卻困獸籠中般地,毀滅於如蟲如獸的反覆絕望,但這仍僅限於男人面向,機械工作與生命價值的思索;戰時因猶太身份受迫的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的《安妮日記》則突出了兒童至青少年,甚至作為一名女性,對生命居間的各項困惑質疑,人的存在與歷史想像,再不囿限於男人與成人,也不僅是官方檯面上的公佈,至亞歷塞維奇的系列著作,生命的秘密,人存在的價值,更完善地於受害弱者或兒童女人,盡數增補完全。
亞歷塞維奇記錄書寫的同時,也提醒著我們,世界的苦難仍在延續,距離二戰已逾 70 載,然而世界各地卻仍發生著不幸與戰爭。2016 年 8 月 17 日,敘利亞空襲過後,被抱上救護車的倖存男孩翁蘭.戴克尼許(Omran Daqneesh)呆若木雞,渾身灰燼血跡,可在前一年土耳其的沙灘上,才正傾覆著亞藍.庫爾迪(Aylan Kurdi)的屍體,二戰以來的難民危機,不曾稍息,越演越烈,然而許多戰事仍在進行。
在日本漫畫《犬夜叉》中,有一種妖怪「無女,是戰爭或飢荒裡,失去孩子的母親,怨念的集合,可她身為妖怪,卻仍懷抱有母親愛子的慈悲心。」妖怪形象的摹繪,是一種「沒有臉部的女人」,由此可幻化為他人母親,作為迷惑之用。這彷彿是《我還是想你,媽媽》,集合戰爭所有失去母親孩子們想望的反相,沒有臉孔,可隨意替換的身形,也像是《戰爭沒有女人的臉》,被抹去痕跡,無能發聲的女人們。

每部著作,亞歷塞維奇都耗時多年,訪錄千百人才剪裁而成,1917 至今,但這不僅是對國家戰事的個人訪談或證言的陳述記錄而已,她以一個朋友的身份靠近,讓人吐露生命的秘密,彷彿從中追尋人生命的原型與奧義。
從蘇維埃的國體悲劇,映射到人類全體的苦難悲傷,正統歷史書所沒有寫的,靈魂的、情感的歷史,由此得到補足充滿,無可避逃的悲劇或戰爭,往往非一人之罪,亦非親身經歷難以言喻,所以亞歷塞維奇,才如此關切個人發聲,行文卻又形諸於和聲,只因「為了理解,所以把話語權交給所有人」。從這樣叨叨絮絮的講述裡,見證殘酷真實,望見最鏤骨蝕心的人性[2]。
[1] 「千人針」據說源於日俄戰爭時,將出征的女性軍眷,持白色布匹與針線,請過路行人或街坊於布上,每人一針,概念頗似如今的集點,集滿百千之數的作品,對出征戰士有祝福護佑,甚至避彈的作用,等同護身符。然而實際上,千人針可能情感心靈撫慰的層面居多,配戴此物在舉槍投彈,死傷百萬的戰事裡,作用不大。百衲衣則是袈裟的原型,取眾人碎棄的雜布為一衣,作為修行之用。有時命格體弱的幼童,也有吃「千家飯,穿百衲衣」,用以祛病消災的風俗。亞歷塞維奇所創「人聲拼貼」文體,蒐集百千人物生命故事而成書,為被掩沒的歷史發聲, 某種程度上的形式,也若合符節。
[2] 亞歷塞維奇訪談,可另行參考 2016 年,由貓頭鷹出版社負責聯繫翻譯,獨立評論@天下以信件對她的獨家訪談。網址https://goo.gl/sSR5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