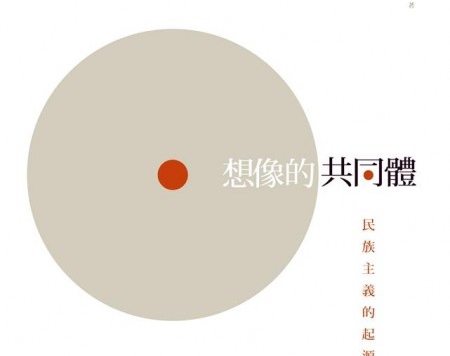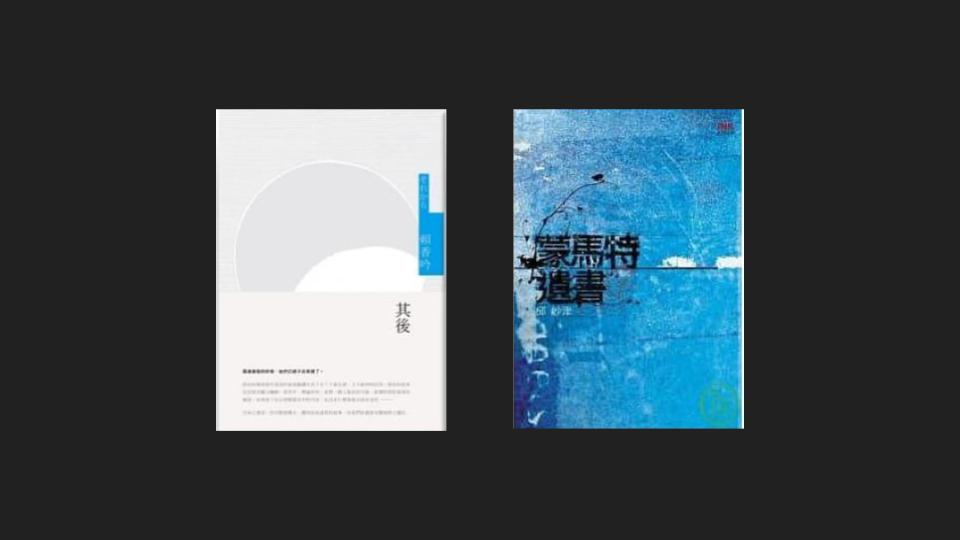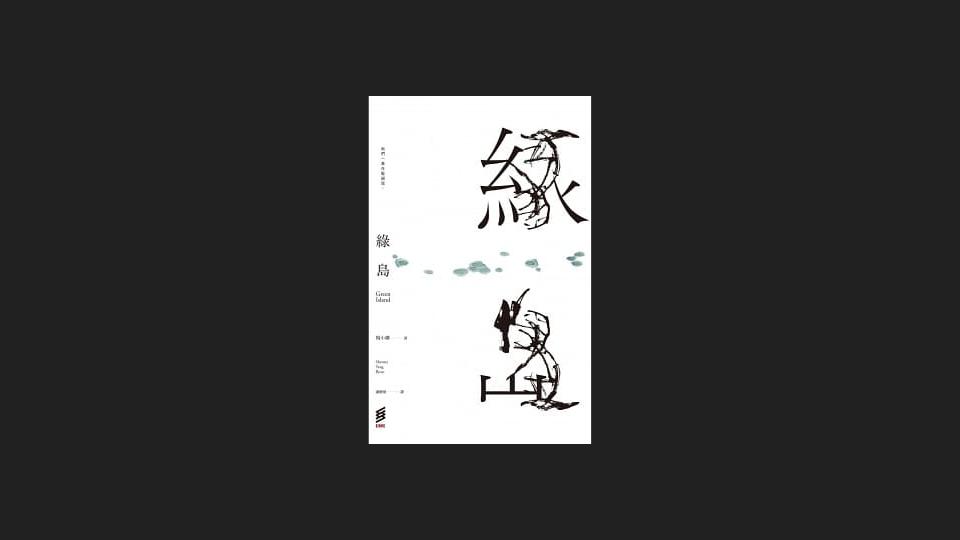如果不是因為臺灣的政治處境,Ben 在臺灣不會這麼受到關注;如果不是因為叡人的翻譯,《想像的共同體》也不會擁有這麼多讀者。
讀《想像的共同體》既是享受,也是挑戰。他的核心論題不難懂,但他帶領讀者進入的世界,有一大片陌生異境。深具原創性的安德森不媚俗,在自由左翼學界對民族主義一片撻伐聲中,他獨排眾議指出現代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起源是:弱小社群對抗帝國的「弱者武器」。光是這一點,就值得臺灣讀者好好思索本書的深意。
認識 Ben 在 2003 年底,那年協助舉辦一場研討會,主題是「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與他通信,邀請他擔任主題演講者,但 Ben 出發前護照遺失,只得錄影講話。
那次研討會有一場圓桌論壇,我擔任引言,為 Ben 特別準備了英文稿,談臺灣認同變遷與兩岸關係。發言稿以提問開場:「一個民主、進步、安全而繁榮的臺灣發展願景,是否能夠排除『中國因素』而獨自發展出來?」因為 Ben 沒來,就把講稿寄給他,並說:「你在錄影演講中提到,當時機成熟時,倫敦知識分子挺身支持愛爾蘭獨立。開展與中國公民社會交往的思維,也隱含這條思路。」
Ben 很快回信:「……兩件事特別震動我。第一,臺灣人認同在十年之間急遽變動(按:1990 — 1998 年,從 18% 到 55%,根據聯合報民意調查)……這過程完全是常態的,只是速度讓人震驚。從民族意識興起的比較研究中,我總是被民族意識似可在一代人之間浮現的現象所震撼,因此我有時候會開玩笑,把民族意識的成長,與青少年早期突然萌發的性自覺做類比。第二,我確信你所主張的『社會交往』是正確的。中國社會大於共產黨與國家機器,而中國社會終將決定後者(之命運或面貌)。無論如何,我猜想,中國政府對臺灣的焦慮並非臺灣本身,而是臺灣在西藏人、香港人、維吾爾人眼中的榜樣作用。」
接著,Ben 評論道:「臺灣的『受害者』心態有個危險性存在,可能會讓人忽略了其他國家人民也可能是臺灣人的受害者。我假定兩岸間通婚主要是臺灣男人娶大陸女性──果若如此,這種不平衡現象很讓人擔憂,尤其是加上許多人知道的,臺灣生意人有時候在大陸再婚;還有,臺灣生意人在大陸助長娼妓行為、剝削中國女性。恐怕臺灣生意人在東南亞和其他地區的形象也不好──人們經常讀到關於他們剝削勞工、規避反汙染法令、性騷擾女性工人、逃稅、行賄等新聞。此外,臺灣應該更努力與非華人社會交往,讓這些地方的人知道臺灣的正面故事;對這些社會,臺灣人除了商機之外也應該多關注其他方面的事務。很高興知道埃及藝術展的事,這是個絕佳的例子,可以幫助臺灣人逃脫乏味無聊的美日中三角關係。」
Ben 對臺灣人、臺灣生意人的直率批評與忠告,至今仍然有效。臺灣深陷「美中日三角」的糾纏,而影響我們對世界其他地區的認識,這個觀點尤其發人深省。
隔年冬天,叡人再度安排 Ben 來訪,清大社會所趁便邀他演講。當天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兩岸政治關係變化的見解,聽眾中不少人對中國的進逼憂心忡忡,Ben 舉重若輕地回應:「我們並沒有列席中共政治局的會議,怎麼知道中南海這些傢伙在想什麼?說不定哪一天,因為某些讓我們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們決定讓臺灣走了算了。」確實,中共歷史上,對於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立場並非一成不變,而總是審時度勢做出調整。畢竟,毛澤東在延安年代,也曾遵從第三國際的路線主張臺灣獨立。
2008 年秋,到康乃爾大學開會,Ben 開車載我上山找餐廳,黃昏的綺色佳寧靜優美。這次相處我發現他身體和眼睛可能都不好,走路緩慢,但依然精神奕奕,幽默風趣。
2010 年,《想像的共同體》中文譯本推出新版,Ben 再度來訪。主辦單位在信義誠品舉行座談會,書迷塞爆,會後要他簽書者大排長龍,我們在樓上咖啡廳等他半小時才盼到他會合。他腳傷未癒,行動不便,但當他看到 Peter(黃文雄)身影從遠方出現,竟雀躍起身,以輕快舞姿迎接 Peter,逗得眾人大笑。當天,有人略帶挑釁地問他:新版的書封設計像不像日本國旗?Ben 一聽莞爾,拿起來端詳一番便說:「看起來像是一塊 CD。」
2012 年初,寫信問 Ben 有關愛爾蘭社會運動與英國知識界的歷史關係,他介紹一本討論無政府主義與工團主義的書,其中有愛爾蘭專章。[1] Ben 說:不要買,這本書貴得離譜,讓 Cynical Institute 買,他們有的是錢。[2]
當時臺灣剛舉辦總統選舉,馬英九第二次當選,公民團體氣氛低迷。記得幾位長輩朋友甚至擔心 2016 年是否還有總統可選。投票後數日,我在《蘋果日報》一篇評論上說:「中國對臺策略,從武嚇轉換到經濟收買,國民黨扮演了掮客角色。馬政府為了勝選,已經把自己套牢在自己參與製造的危機之中。臺灣社會所顯現的堅韌民主能量,很快將檢驗馬總統發下的宏願:『我會用生命來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臺灣的安全和臺灣人民的尊嚴。』」我與 Ben 提到臺灣政治氛圍,Ben 仍一派樂觀:「的確,馬是個相當荒謬的人物,但我很確定,他不想讓自己在歷史上成為臺灣最後一位總統。振奮起來吧!」
彷彿是為 Ben 的樂觀主義背書,2012 年開始,公民運動對馬政府親中政策的抵制、對中國因素的反抗,改變了臺灣內部的政治結構,預示了國民黨的挫敗。人的能動性,不斷在改變世界。Ben 的思想若說與臺灣社會的抵抗行動有契合之處,最重要的大概是對結構主義式命定論的批判了。
2015 年 7 月底,收到一封 Ben 從馬尼拉寄來的信,他的錢包及證件都遺失了,沒錢付旅館費,旅館經理不讓他們離開,而 Ben 又趕著搭機回家,因此急需一千二百美元。不用說,一看就是詐騙郵件。
當下想,是否應該警告 Ben 他信箱被盜,但手邊沒他在綺色佳的電話(夏天他應該都是待在綺色佳吧),一念之間便作罷。之後,心裡一直掛念要寫信問候他,卻沒有動筆。豈料不過幾個月,這樣親近臺灣的愛爾蘭人,走了。
我們最後的通信,一封詐騙郵件,如此的玩笑,聽說他在爪哇睡夢中悄悄離去,倒也符合 Ben 詼諧的輕快風格。別了,這樣深刻而平易可親的愛爾蘭人。
(本文作者為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1] Steven Hirsch and Lucien Van Der Walt eds., Anarchism and Syndicalism in the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World, 1870-1940: the Praxi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International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 Leiden: Brill, 2010.
[2] Cynical Institute 是雙關語,中央研究院的英文是 Academia Sinica.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紀念會
時間:2016 年 1 月 6 日 19:00 地點:誠品信義店三樓 Forum主持:莊瑞琳 與談:吳叡人、吳豪人、吳介民
特別來賓: 陳正雄以及所有《想像的共同體》的讀者
主辦:衛城出版、時報出版、誠品書店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64978467030367/
活動說明:1983 年《想像的共同體》英文版出版後,這本書三十一種語言的翻譯過程,彷彿變成一則人類民族主義發展的見證,還使得安德森不得不在 2006 年寫下〈旅行與交通〉一文,解讀這則由翻譯版本時間形成的民族主義隱喻。這篇文章也種下衛城編輯得以在時報出版任職時推出新版的緣分,並且有機會與這位幽默又睿智的 Uncle Ben 於2010 年在臺灣相見。而五年前的我們並不知道,2015 年的結束與 2016 年的開始,我們將在紀念 Ben 當中度過……
附錄
吳介民:從神性時間到世俗時間的推論躍進
我這幾天閱讀這個新發行版本中,你寫的〈旅行與交通:論《想像的共同體》的地理傳記〉。裡頭浮現的作者,給人的印象是:心情豁達,開朗,舉重若輕。這很有趣,與這本書在世界各地所歷經的複雜捲摺、彎彎翹翹、或沉重或輕巧的生命歷程,形成強烈的對比。一位年過七旬的學者,他即將成為傳世之作的書,不斷在世界上被翻譯,裁剪,詮釋,襲奪,盜版。是的,「盜版」是你認可的民族主義以不同形式在全球快速擴張的最佳隱喻;於是,「《想像的共同體》已經不再是我的書了。」這令人眼花撩亂的翻譯百獸奇觀 (menagerie of transliterations),竟然就發生在這位學者仍然健在的當下──因此,我對於這位作者的豁達與幽默,感到既尊敬又好奇。一位把一切看開的老學者,我們大可期待,他會以直率而毋須討好任何人的態度,來回應任何關於他作品的問題。因此,趁這個難得與作者重逢,同時又面對文藝公眾的機會,我想要問他一個問題。
我個人認為,《想像的共同體》這本書最具原創性的觀點在於:你在本書第二章,尤其是「對時間的理解」那一節,借用奧爾巴哈(Erich Auerbach)對中世紀神性時間(或「彌賽亞時間」)的詮釋,對比出發源於歐洲的小說與報紙的現代時間──或者可以說是「世俗時間」;並進而發展出你的想像共同體的認識論基礎。這兩種對時間性質的神聖性程度的對照,也就是兩種對「同時性」(simultaneity)的認識和體會,使你可以做出推論上的大躍進。
關於神性時間的基督宗教生活氛圍,絕大部分的學者能夠引用的例子,如同你所使用的,都是通過上帝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秩序是超越經驗世界因果的垂直性的同時性,裡頭的人物總是基督、亞伯拉罕、以撒等等人物。對反的,在現代時間的範疇中,你做了一個引導讀者想像的大躍進:你的主角是字母,是A、B、C、D……,他們是凡夫俗子,他們之間以雙人配對的關係出現,他們有婚姻關係卻又背叛,他們在一起或分別做這些看起來瑣瑣碎碎的事情:吵架,做愛,做夢,打電話,打撞球,購物,吃飯,流連酒吧還喝醉了──他們的生活是依照時鐘與日曆而運行。現在,你告訴我們,這群可能存在實際交往關係的人們,他們更可能是終其一生未曾發生真正的接觸。他們的關係,容許我打個比方,頂多是通過「匿名的連鎖傳染」而產生。現代的民族主義,就是誕生在這樣的現代時空結構當中,而且竟然變成了「被設想成在歷史之中穩定地向下(或向上)運動的堅實的共同體」(《想像的共同體》中文版,頁 63)。
這是一個極端抽象的概念,一方面很難被精確翻譯(由於各式各樣的原因,其中一個很可能是,在諸多並不存在超越性的一神論的文化中,這兩種同時性的對比很難被掌握住。因此,在翻譯上也容易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但是,另一方面,弔詭的,這個概念因為其抽象程度,也很難被任意竄改。我個人認為,這個對於現代時間與民族主義的關聯,是你對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最大貢獻之處。我相信,這個理解已經不斷被你的研究者所指出,雖然我沒有花精神去搜尋浩瀚的文獻。
從時間的同時性這個概念,容許我自由聯想而提出我的問題。誠品書店是臺灣的一個觀光景點。隨著來自中國大陸的觀光客愈來愈多,這個景點已經成為中國具有小資情調的中產階級必遊之地。因此我相信,今天在這個現場聆聽你的演講的人群當中,很有可能有中國籍人士,他們有可能無意中進入這個想像共同體的現場,也有可能是仰慕你的大名而在這個空間駐留。所以,在這裡,至少有兩群對於臺灣這個社會/國家/生活共同體,有天南地北迥異想像的聽眾,這些聽眾對於臺灣的想像,甚至是某種敵對性的想像。他們此時此刻共聚一堂。對於這一幅呈現在你面前的影像,其實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翻譯百獸奇觀的俗世版,你心中的直覺感受是什麼?你有什麼話,想對這樣異質性的聽眾說嗎?
按:附錄為「《想像的共同體》的地理傳記:一本書的旅行與政治」座談會與談大綱。(2010 年 5 月 9 日,誠品書店,時報出版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