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台籍青年陳武雄終於在基隆上岸,自南洋活著回來。二十一年後,作為詩人的他,以仍帶有一些日本味的異質中文,慢慢寫下第一篇小說〈輸送船〉。在書桌前,隨著波浪的搖晃,與引擎的爆音,再次回到戰火中的南洋。這一段記憶,彷若一個遲遲無法結束的夢境。十七年間,他陸續寫下十多篇角色、精神相通的戰爭系列小說。集結成冊時,他已是六十二歲的老人了。為什麼非得透過小說,回到南洋不可呢?他在〈輸送船〉的序詩〈信鴿〉寫道,他把死埋設在南洋。但直到戰爭結束、回到故鄉,他才想起,忘記把自己的死帶回來。
他活著回來了,卻成為只有一半的人。
只有一半的人
他的語言只有一半。離開故鄉前,他接受的是日本教育,甚至通過日語口試,轉入以日本學生為主的小學校。早慧的他,也曾以「陳千武」為筆名,發表六十餘首日文詩作在報刊雜誌上,受到《台灣新民報》文藝欄主編黃得時、文壇領袖張文環的讚譽。然而南洋一去四年,「光復」後的故鄉,已成為使用陌生語言的冷酷異境。他有詩人的靈魂,卻找不到語言的形體。只能如孤魂般,暫且棲身於另一種「國語」,笨拙地以宛若義肢的舌頭自我表述,有時也必須委請嫻熟中文的年輕詩人替他改稿。南洋的砲火不曾傷害他。但作為一位詩人,回到故鄉後,卻遭遇了難治的傷殘。
他的記憶只配擁有一半。國民政府統治下的戰後初期,各種剷除「日本奴化象徵」的措施陸續展開:日本紀年的石碑事略塗改為民國紀年;朝日末廣大正的街町名稱由中華中正中山取代;神社轉型忠烈祠、刨去銅馬腹部的菊紋、覆上國徽或是黨徽。當然,他是不贊同日本帝國主義的。即便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叛逆的陳武雄也決心不改姓名。但國民政府此舉,毋寧是宣告從前的記憶都是奴化,都不能算數。他赴南洋參戰的事,當然也不能夠提起。

他的存在,也只有一半。平安歸來這麼多年,他卻不時感覺自己仍在戰爭狀態:「睡時感到自己還活著,醒時感到自己沒有死去,這種深刻的感覺,一直到今天,有時會再無端地回想起,我也覺得它仍存在我底世界裡。」他的生,是介於「還活著」與「沒有死去」之間的微妙存在,因為他只帶回來半個自己。他的死,仍徘徊在南洋的密林裡沒有回來。失去了死的他的生,自然不能算是完整的活。
一九六三年,他寫下詩作〈鼓手之歌〉,談自己的寫作與人生。他說:時間遴選他做一名鼓手。他於是將自己的皮張成鼓面,拚命敲打自己痛愛的生命,以發出聲響、產生共鳴。如此的生命之歌,成為「詩人陳千武」的象徵。然而悲哀的是,其鼓聲的響亮,並非源於生命的豐饒、或生花的妙筆,而毋寧是高度緊繃的人生張力,以及內在的巨大空洞所致。
他們這一代人,是憑藉著殘缺與不足來寫作的。
南洋歸來後,只以一半的狀態存在的他,努力要活成完整的人。
為此,他做了三件事。
跨越,建構,寫作
首先是語言的跨越。一九四七年,他藉由手抄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中譯本,開始自修中文。儘管在此之前,他已有兩部日文詩集《徬徨の草笛》與《花の詩集》出版,但此刻他必須把自己歸零,不能再惦念過去。然而語言的轉換不是一蹴可幾的。要到一九五八年,他以新筆名「桓夫」發表第一首中文詩〈外景〉於《公論報》「藍星週刊」,才終於以「跨語詩人」之姿重返文壇。不過他認為,一九六一年刊登於《台大青年》的〈雨中行〉,才是他真正寫詩的開始。這首詩以蜘蛛絲比喻垂直落下的驟雨。這座透明的檻柵,也象徵生命的困局。「被摔於地上的無數蜘蛛/都來一個翻筋斗,表示一次反抗的姿勢/而以悲哀的斑紋,印上我的衣服和臉/我已沾染苦鬪的痕跡於一身」。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他與幾位同樣歷經語言苦鬪的詩人林亨泰、詹冰、錦連等,決議共同籌組「笠」詩社,從過往的單打獨鬥,往集團活動跨出重要一步。也許他們終其一生,還是很難將陌生的「國語」內化成為自己的語言,但即便如此,他們仍要設法突圍,不能辜負詩人的靈魂,與文友們的勉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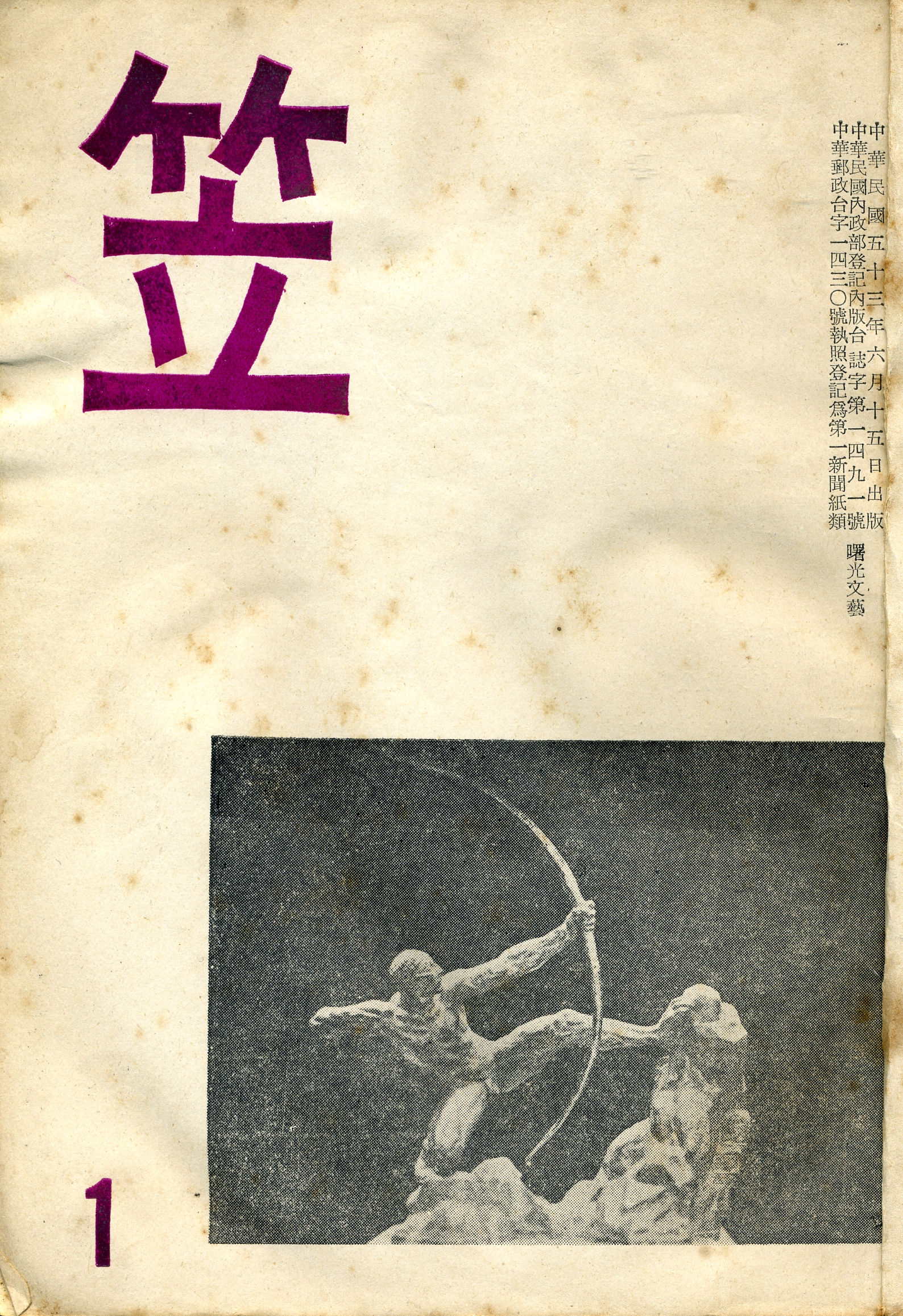
第二件事,是文學史的建構。他借用植物地下根莖的象徵,提出極具創意的「兩個球根論」,設法將被系統性抹除的日本時代台灣文學水脈,在文學史上延續下來。他說:「紀弦認為他帶來台灣新詩的火種那個時候,台灣並無所謂什麼詩壇,也談不到什麼文藝界的。而由於他帶來的火種,一手建立了這個詩壇。」但他認為,促成戰後台灣現代詩開花的,並非只有中國來台詩人的刺激。得到日本養分而在戰前台灣留下的近代新詩精神,也由林亨泰等跨語詩人所承繼,而與紀弦帶來的中國現代派融合,共同構成戰後台灣現代詩雙重構造、多音交響的獨特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七○年代末,日本時代的新文學史料陸續出土之際,他也與同屬跨語世代的小說家鍾肇政等,擔負起分量極重的翻譯工作,企圖溝通、縫補這段被腰斬的文學史,讓日本時代的台灣球根,能以中文型態與戰後的讀者見面。
最後一件事:他花了十七年的時間,完成人生中唯一的一部小說集《獵女犯: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這部作品,不少人將之與現實混同,視為台灣人南洋參戰的歷史見證;但我想,他不得不寫的理由也許是:長年以一半的狀態活在戰後台灣的他,終於下定決心,要用自己的餘生,重新尋回被忘在南洋的死;或者說,失落在密林中另一半的自己。
一九四三年九月三十日,甫完成訓練的新兵陳武雄抵達高雄港,乘上滿載「台灣陸軍特別志願兵」的三千噸輸送船,往南洋出發。此後幾年,他輾轉於赤道線南北的昭南、爪哇島、溫魯斯島、帝汶島之間參加作戰,也曾經做過俘虜。關於死,他曾經寫過,部隊出發前,士兵們要剪下指甲裝進信封,再填上部隊編號、軍階、姓名,交給人事官。萬一戰死無法收屍,就當作骨灰交還給遺族。指甲宛若替身。他活下來幾次,指甲便替他死了幾次。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他終於離開南洋,活著回來,卻留下半個自己,在異鄉南洋的密林裡。無人知曉,生死不明,沒有國籍,成為埋藏在陳武雄心底沉甸甸的心事。這些年來,一直沒有人來領他回去。說不定他不知道戰爭早已結束。

一九六七年,在出版兩冊中文詩集之後,他開始著手撰寫短篇小說。他虛構了一個角色林逸平兵長,與之共用一份兵歷表。大概所有的讀者都知道,林兵長的原型就是陳武雄,但為何他不以自傳或回憶錄的方式撰寫?在充滿禁忌的戒嚴時期,透過小說的虛構,也許能稍稍迴避自身經歷的直接指涉。但我想,這一段經歷對他而言,並非什麼值得拿來說嘴的事,而是創傷。每一次想起,也許就會讓他感到混亂,焦慮,喘不過氣。所以他將半個自己忘在南洋,不願輕易提起。
小說中穿著軍裝的林兵長,並非英雄般的存在,而是帶著生而為「人」的軟弱、恐懼、良善、悲傷、醜惡、慾望、殘虐、認同的混亂與矛盾、無奈、愛、柔軟、苦痛,輾轉於島與島之間,潛伏在南洋的密林裡。他寫下林兵長這個角色時,也許也反覆地想著:我也是這樣的人嗎?我有沒有比他更正直,更良善?所以他需要漫長的時間,以及更多迴旋的餘裕,稍稍離開自己,也更加客觀地面對自己,從個人的傷口、台灣人集體精神的裂縫,重新探視這段艱難的過去。在各種層面上,他都必須很勉強自己。無論在語言上,或是在精神上。
因為唯有重新接回被忘卻在南洋的自己,他才能夠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回到自己的故鄉,用餘生完整地活著,再完整地死去。

絕無僅有的台灣人被志願成為日本兵的第一手故事,
是被殖民者成為殖民者的武力再去殖民他人的懺情錄。
◎在《獵女犯》之外陳千武也發表數篇以二戰時期為背景的小說,可視為《獵女犯》主題的相關創作。本書附錄收入這幾篇作品,讓讀者可以同時閱讀陳千武先生關於這主題的所有小說創作。
你不是福佬人,你是日本鬼。
如果你真的是福佬人,那為什麼要當他們的兵?
能不能救我,放我回家?
一九四二年,二十歲的陳千武「被志願」入伍受訓,成為日軍侵略東南亞的部隊。
《獵女犯: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是陳千武親身經歷南洋戰場後所寫下來的故事。本書以多篇小說架構,從主角台灣青年林逸平「被志願」入伍成為日本陸軍,被派往東南亞參戰寫起,各篇的主題述及了日籍士兵與台灣志願兵的不平等待遇、面對美澳聯軍空襲、南洋當地人被多次殖民的處境、軍隊裡同性互相撫慰的狀況、被派去為日軍運送與「狩獵」慰安婦、為日軍管理與徵收當地部落的農糧生產,直到戰爭結束日軍投降於英荷聯軍,但又同時暗中幫助蘇卡諾領導的印尼獨立軍。台灣士兵們爭取脫離日軍變成自主的同鄉會,等到隔年的一九四六年七月才得以返回台灣。
同名的獲獎作〈獵女犯〉描述了主角林逸平兵長受命押送一群被日軍強徵的當地女子到慰安所受訓,途中聽到女子群中一人講了福佬話,便與之交談,知道她是福建移民後代。該女子賴莎琳對會講相同語言的同胞卻成為日軍感到不解與不滿。女子們受訓完後,慰安所正式運作,日軍要求士兵都要去光顧。林逸平去找了賴莎琳,賴莎琳指責他跟其他人一樣是來「狩獵」的。但他表明因軍令不得不來,但只是來看看她而已,並無非分之想。故事最後反倒是賴莎琳要求林逸平「狩獵」她,讓他陷入迷惘。
文學價值之外,《獵女犯》也具有時代意義,更是難得一見的有關台灣人到南洋當兵的第一手書寫。當年被強徵從軍的人到了戰後都變成失語世代,語言轉換困難,更別說寫作,很多事情都難以記錄下來。陳千武以其毅力,在戰後努力學習華文,建立自己特有的語言風格,創作眾多詩作與小說,《獵女犯》終於以獨特的靈思和語言呈現在大家面前。
以往我們總覺得台灣人長年沒辦法當家作主,命運是悲哀的,但陳千武的作為與作品卻展現了,即使在殖民時代台灣人也有其主體思考的一面。《獵女犯》充滿了對時代的評價與對人性的信念,文學的心靈面對政治力量的壓迫與戰事的衝擊,從中生長出穿透國界的人道關懷與自我省思。
除了《獵女犯》的序文和十六篇小說(包括代後記)之外,陳千武也曾發表多篇以二戰時期為背景的小說,可視為《獵女犯》主題的相關創作。本書於附錄收入這幾篇作品,讓讀者可以在《獵女犯》這本經典之外,也一覽陳千武關於這主題的所有小說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