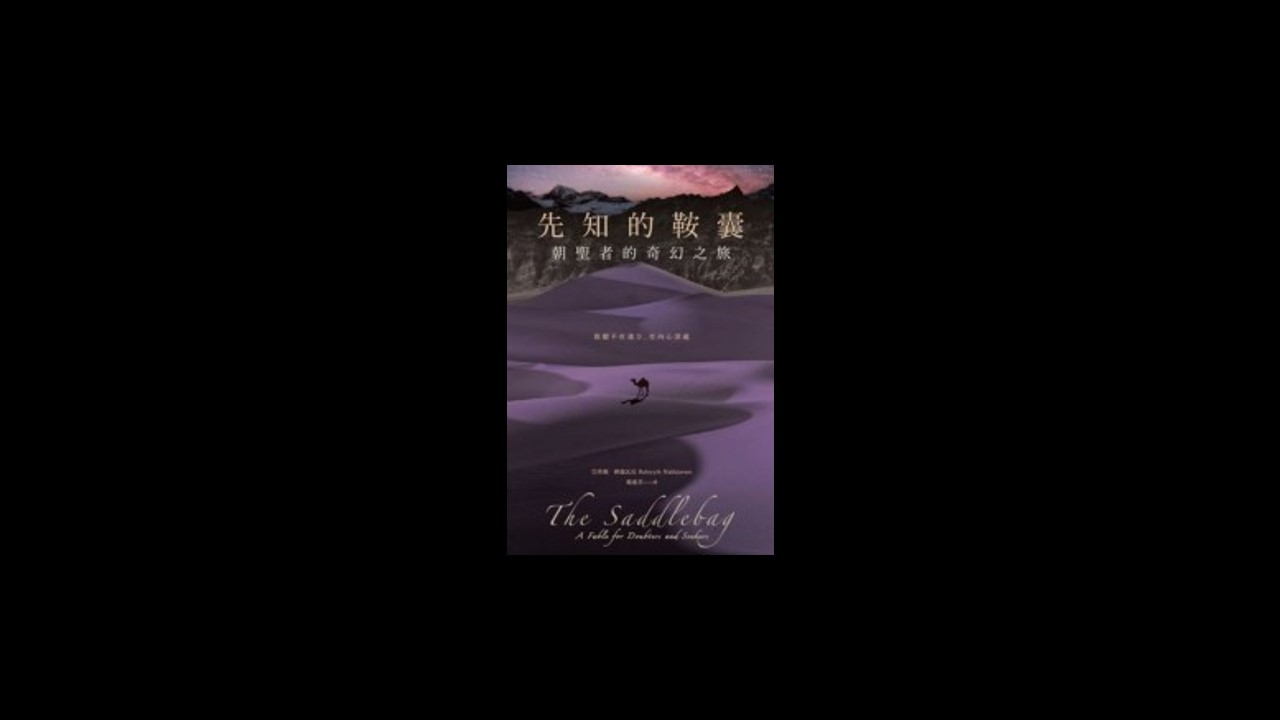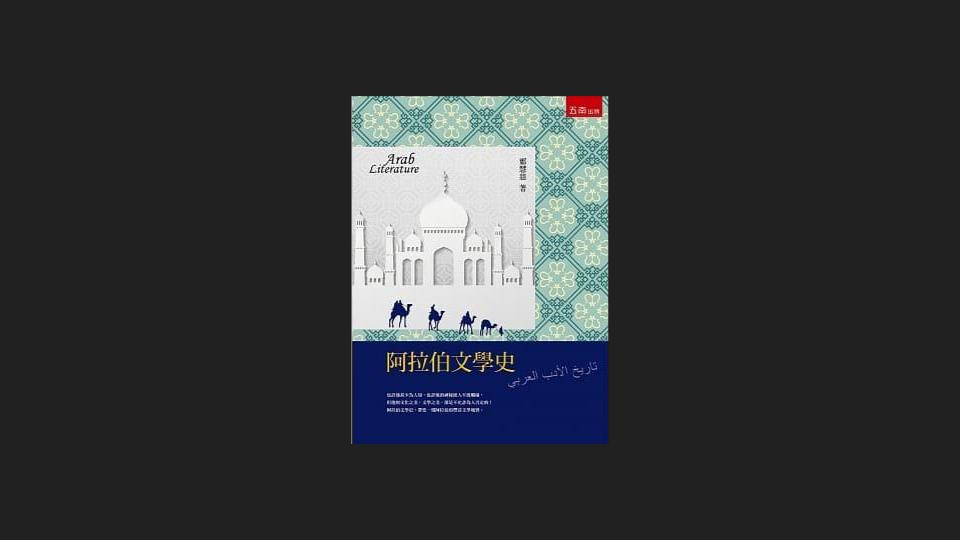異教徒,除了星星、月亮、太陽和自由,從不侍奉任何人。
從前有一個小偷,專門在麥加和麥地那之間的路上竊取朝聖者的財物。
他是貝都因人,在沙丘之間出生,從小就沒有父親。他對教士也一無所知,不在乎先知或他的律法。他由好幾個母親扶養,在他學會扒竊之前,她們就全都過世了,因此他幾乎沒有被人疼愛過,也沒讀過書。但他一直很自由。
對這個貝都因人來說,自由就是他呼吸的沙漠空氣。
是介於瞭解和否認之間的那個不置可否的開放空間,是夾雜在明顯事實之間的那個保留期望的無人地帶。他一生來就繼承了這種空虛;這是免費留給他的遺產。他從小就知道它的價值,但他仍然必須為自己找出這種自由的定義。
他發現住在城市的人不信任這種自由:他們用人的意志和壁壘束縛它數之不盡的意義。到了擁擠的城鎮和污穢的村莊,只有在長滿香甜果樹的祕密花園裡,他才能找到這種自由的遺跡。在水池邊的庭院裡,就像記憶中的橙花,舉目望去,仍是一片蠻荒;儘管空間狹窄,自由的種籽就算在這裡也會生長。但是對貝都因人來說,這是不夠的。他渴望無垠的浩瀚。
因此沙漠給了他特權。
在這裡,猜想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利,而且既然無從舉證,足以證明他的猜測是不朽的真理。這些起伏的沙子容許無限的詮釋;這些山丘和山谷提供無數揣測的機會。而且儘管從小孤苦伶仃,他在沙漠從來不感覺孤獨,因為他的腦子裡總是迴響著沙漠種種不同的聲音。一直以來,沙漠就像他的母親和父親、老師、愛人和嚮導。
儘管不認識字,沙漠也教給他淵博的學識。他發現了整篇整篇隱藏在沙塵暴裡的論文;他讀過刻在大地上的一千首詩。日出時分,在他的靈魂潔白無暇時,他聽得懂沙子的語言。到了二十歲,他知道龜裂懸崖上的祕密小徑,能解讀流動沙丘裡的謎語。他根據時辰來分析每一片塵雲,解讀月球在每個季節發出的訊息,也能聽出每一顆恆星的聲音。風是他的宗教,金星是他愛人,他在岩石和沙漠的谷地發現了它們殘留的旨意。
最重要的是,他知道如何利用從吉達到兩座聖城路上的溝壑躲藏、逃跑、消失得無影無蹤。因為這個原因,他認識了一群盜賊,當上他們的嚮導。
從扒竊到為盜賊效勞,似乎很順理成章。這個貝都因人從小就會監視那些在路邊聖堂駐足的人,偷聽他們在村莊水井邊的談話。他知道他們的目的,評估他們的弱點,然後在朝聖的途中伏擊他們。有時他甚至會擔任他們的特別嚮導。
不過讓他收穫最豐富的未必是荷包。
小時候遇過一個伏在沙子上禱告,但習慣從頭到尾都不停默默挖鼻孔的人,讓他看得津津有味。他鬍子都還沒長齊的時候,就遇見另一個朝聖者在咖啡廳和他搭訕,而且給他的酬勞比他開的價碼還高。他少年時代第三次當嚮導時,有個朝聖者虛偽的程度令人瞠目結舌,結果他一毛錢也沒拿就跑了。
事實上,這些朝聖者賜給他的不是生計,而是讓他從他們身上學到某種能力,辨別何謂社交式的虔誠,何謂真誠的信仰。
在他多年的竊盜生涯裡,還沒見過幾個把信仰看得比金錢價值更重的人。大多數的朝聖者活像在跟一個阿拉伯數字說話,他怎麼看也不像是那個讓他在流沙邊際激動得全身顫抖,或是在懸崖邊緣嚇得直打哆嗦的唯一真神。他們的宗教對外在的姿態有諸多要求,卻沒有造成什麼恐懼,在他眼中,後者才能證明神的存在。既然斷定朝聖者祭拜的並不是他的神,偷竊他們的財物,自然不會良心不安。
但孤獨的小偷生活艱難,有幾次身無分文,他也很想裝出虔誠的模樣討施捨。多虧了那幫盜賊,他才不必出賣自己。他們看到他在前往麥加的路上行乞,妄用神的名字來辱罵他,但他卻不覺得褻瀆。他們還保護他的安全,因為沙漠裡的人比流沙更危險。
為了請他幫忙帶路,這批盜賊答應保護貝都因人不受野蠻的部落欺侮。他們的首領需要這個沙漠蜥蜴老手指點,好比對手早一步知道哪裡有比較有錢的商隊,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他也需要這批人。
雙方談好條件,他幫他們做事,以免於遭受他們欺凌;他放棄自己的自由,是因為他年紀還輕,相信自己是自由的。由於雙方締了約,至今他一直懷抱著自己寶貴的夢想。因為他希望,將來有一天,能和王子一樣富有。
這樣的夢想,一旦說出去,其他土匪就會知道這個小偷非但不夠狡猾,還是個既天真又古怪的傢伙。
不過從他的長相卻看不出來。他的眼睛屬於細長型,像鷹眼一樣銳利,眼珠的顏色讓人看了惶惶不安:猶如藍天一般,空無一物,只映照出地平線盡頭的景物,凝視人的臉孔時,眼珠頓時成了綠色。有時會呈現一種奇特的黃色色調,人們事後想起,不免心裡發毛。他的鼻子也像鷹嘴,皮膚被太陽曬得黝黑,整個人黑不溜丟的。他的頭髮算是少年白,胡亂糾結成一束一束,用一條原本是靛青色的帶子綁在後腦杓。他的腳程快如閃電,而且幾乎不會留下腳印,因為他沒有高大或壯碩的身材,體型矮小、靈活、瘦削、敏銳。
但儘管長了令人不安的眼睛和一副鷹勾鼻,雖然有著野蠻而殘酷的外表。他喜歡做夢,這個貝都因人。他生性浪漫。他在暴風和飛沙裡聽見自己的自由發出的聲音;在任何時候都能聽見。其他的盜賊說他是懦夫,因為他不願意挺身與人打鬥:他寧願轉身逃跑。他們不明白這是因為他全心全意熱愛自己的自由。因為他腦子裡的聲音告訴他,絕對不要和任何人妥協,只要侍奉星星、月亮和太陽。
不過他也會聽男人的聲音,好把那幫土匪伺候得更好。雖然他對清真寺裡的聲音充耳不聞,對市場裡的聲音卻機靈得很。當朝聖者放下他們的祈禱書,開始用自己的聲音說話時,他會從頭到尾聽得仔仔細細。因為這些聲音反映出他們在世俗方面的煩惱,可以趁機摸清楚他們的憂慮。在他們互相爭執,討價還價,埋怨叫屈的時候,他分辨出他們是富是貧,他們會損失多少,他又能賺到多少。他的耳朵變得很尖,可以從男人的嘴巴一路聽到他們的口袋。
服侍那幫土匪幾年之後,有一天晚上,小偷在路邊的客棧聽到傳聞,說有個富商和他的商隊會在接下來的幾天經過這裡。據說他車上的珍珠和珠寶多得不得了,閃爍的光芒會讓太陽西沉,而且忘記還要再升起來。
這個商隊的騾子和駱駝馱的貨物重到必須在岩石小徑上開一條純金的軌道。商隊中白銀的光比月亮還耀眼,他們喃喃地說,幾個鞍囊裡裝了整個東方的財寶。有婚喪喜慶都用得著的糖果和香料。有人說這個商人來自希哈,準備去麥加朝聖;另外也有人說他來自布什爾,此行是去大馬士革做買賣。雖然對他的來處各說各話,也說不準他究竟要去哪裡,不過大家都相信他有大批財富,而且值得動手偷竊。

當然,這些年來,像這樣的傳言多得很,後來也有人攔路打劫。每次的收穫總不如先前預想的那麼豐碩。但小偷覺得這一次的傳言和其他的不一樣。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次的財寶似乎更令人垂涎,這個商人聽起來好像更有錢,他的商隊可能帶來的財富,多到這幫土匪連做夢都沒想過。他們越想越陶醉,小偷也陪他們一起喝酒。

那天晚上,他們在營火邊計畫埋伏行動,首領把這個貝都因人叫到身邊。他老早就喜歡他這個身材結實、雙腿纖細的嚮導。其實他還稱不上是男人,但氣宇軒昂,不同於其他的鼠竊狗偷之輩。他當著其他人的面擁抱他,然後把自己的酒遞給他喝。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榮譽。
按照慣例,他們會把偷來的贓物平分,但這一次,貝都因人以為他會拿到最大的一份。所謂最大的一份,當然是在首領拿走他應得的大多數戰利品之後,才輪到他們。這個跡象代表他,小偷,貝都因人,即將成為他們的一分子。
土匪歡欣鼓舞,然後偷偷往腳邊的沙子啐了一口;他們大聲歡呼,同時用懷疑的目光斜眼互望。他們繞著營火換位子,拍手臂,嫉妒這股溫情。他們不喜歡首領給他這麼大的面子。
據說被首領親一下,就能得到一筆財富,也可能損失慘重。
他的擁抱比鑲了珠寶的匕首更值錢,而且和匕首一樣危險。在過去,貝都因人一直渴望首領像這樣對他另眼相看和疼惜。曾經有一段時間,這種信任會讓他志得意滿,就像逃離這幫土匪一樣高興。但現在不同了。他在苦惱什麼?他遇上了什麼麻煩?
他腦子裡的聲音很不安。低聲細訴著土匪腳邊的流沙,以及首領的親吻所包含的毒藥。
這些聲音喃喃說著孤獨的沙丘,因為對於他委曲求全的一生,它們已經很不耐煩。它們慫恿他離開這幫人,一個人獨吞這批贓物。他們提醒他別忘了有個祕密的地方可以存放他得手的錢幣,他們所有人都找不到。他要的不是分到最大的一份;而是一分錢也不分給別人!想到要等別人分配給他,他就一肚子火。「逃跑吧,」他腦子裡的聲音說,「趁現在還有機會跑走。」
他坐在首領身邊,看他啃著羔羊的骨頭,然後一塊又一塊地丟出去,越過營火,墜入黑暗。這個人今晚會有三個女人在帳棚裡任他挑,他們搶來的最美的女人也歸他。小偷看著他舔去嘴唇的油脂,剔去卡在牙縫的肉屑,然後想起這完全不是他熱愛的事。「有更多熱情在光禿的月亮下等著你,」他腦子裡的聲音低聲地說,「而不是首領的夢裡。」
他也仔細端詳圍坐在他身邊的這群土匪,知道他們的靈魂已經被控制,完全不由自主。在閃耀的星光下,他望著他們悶悶不樂的表情,聽著他們活像貓頭鷹鳴叫的悲涼笑聲,感覺到他們在充滿火花、忽明忽滅的黑暗中貪心不足的嫉妒。「他們慣於嫉妒他們永遠得不到的東西,」他腦子裡的聲音咕噥著,「而且他們會恨你一輩子,因為你不嫉妒他們。」
新月升到沙丘上空,顯得更加澄澈明亮,一陣冷冽的微風拉扯他雜亂糾結的頭髮。月亮傳遞了一個訊息;刺骨的微風也傳遞了一個。月亮擁護他;微風控訴他。新月見證雙方的契約改變了,時間到了。微風悄聲地說,時間早就到了,契約的條件已經過期。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沙漠裡全是她們的聲音。
「好一個懦夫。」微風嚴厲地嘯嘯響起。「你比任何朝聖者都虛偽,比任何海市蜃樓更會欺騙!」土匪放肆狂飲,圍著營火吵吵鬧鬧,狂風把火焰颳到他們臉上。
「但以前的情況不一樣。」月亮低聲呢喃,而且她的論點鏗鏘有力,連首領都抬頭看了她一眼。「以前他是個小男孩,現在他是個男人了,」她接著說,但首領似乎不相信月亮的這套邏輯,因為聽到一名土匪說了個低俗的笑話,他就立刻轉過頭去。
「如果他的感受和行為是兩碼事。」微風冷笑著說,「那他跟他壓根就瞧不起的那些人有什麼不同?」聽見這個控訴,貝都因人打了個冷顫,在暗處把他的連帽長袍拉得更緊一點。風越吹越大。「如果他比那些朝聖者更糟糕,又憑什麼搶他們的錢財?」她譏笑著說。
「他原本談好的條件是犧牲自由來換取保護,」月亮低聲回答,「但現在他寧願不計代價討回自由。」月亮甩掉附著在身上的最後一朵雲,然後意味深長地航向毫無人跡的黑暗沙丘,來證明這一點。
小偷聽見微風出賣他,但那幫盜賊似乎沒聽見。他聽見月亮為他辯護,但首領彷彿沒聽見。即使當星星拿出一個又一個證據,從距離遙遠的太陽引述案例,從消逝的季節提出證明,除了貝都因人,誰也沒察覺到現在已經不是當年那個時候,契約的條件已經不同,而且永遠無法恢復。
但小偷至今還沒拋棄這幫盜賊是有原因的。
他擔心遭到報復。他的恐懼活像沼澤水坑裡的蒼蠅,在他的腦子裡嗡嗡作響;就像頭頂上的禿鷹,發出尖銳的叫聲。首領的報復欲永不滿足,對叛徒又毫不手軟。貝都因人知道如果他逃跑的話,首領一定會找到他,要他的命;他不敢亂來。他知道不管他躲在哪裡,這幫土匪遲早會找到他,在他背上捅一刀,一刀劃開他的喉嚨,割下他的舌頭和命根子,然後把手伸進他的肝和心臟。他們這群人既嗜血又冷酷。每次想逃跑,他腦子裡的聲音就會噓他,說這樣必死無疑。
他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買回自由,同時保住性命,意思是如果他有錢的話。
這種想法充分顯示出他的天真。其實這比較像是一種信仰,而非想法,而且發出的聲音強烈、簡單。充滿了日光的希望,聚集在他的心底深處,清新如朝露,讓他確信可以脫離現在的困境。這個聲音告訴他,如果那批贓物的誘惑夠大,如果他一個人就能偷到更多的財寶,如果他能賄賂土匪還他自由,以後就不必替別人賣命;他可得到自己渴望的絕對自由。
現在機會似乎就在眼前。既然他已經得到首領的信任,而且特別得寵,這幫土匪應該沒有理由懷疑他有背叛的可能。如果商隊真的像大伙兒說的那樣,裝滿了金銀財寶,他或許有機會偷到足夠的籌碼來和他們談條件。
想到這個可能性,貝都因人陶醉得很,把腦子裡那些不安的聲音奉若神明。
那天晚上,在為這幫土匪忠心效勞了好幾年,在終於得到他們的接納,受到首領的破格垂青之後,小偷悄悄離開他的主人們,消失在沙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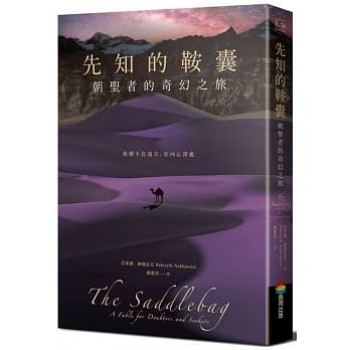
一只鞍囊讓他們命運交錯。
在不同文化、不同世界觀的眼光之下,
鞍囊反映出每個人的所想所望,
自由、財富、名聲、權力……,
然而,靈魂的救贖究竟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