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優先 vs. 各國的反抗
截至二○一八年底,川普的對外政策,正如他的選舉口號:「美國優先。」
在競選期間,經濟上,川普大力批評九○年代美國參與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揚言退出歐巴馬政府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誠如前文所述,川普認為這些過往的全球化觀念與自由貿易協定,只會嚴重地傷害美國人的工作權益與貿易利潤;安全上,川普批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過時,各會員國都只願意享用美國提供的公共財,不願意負擔更多責任,形同讓美國人民負擔更多的經濟成本。
而川普,矢言要改變這個狀態,找回屬於美國人民的利益。
因此,川普在競選期間便宣示,他將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果不其然,在當選之後他隨即宣布退出該協定、在 G20 峰會上首次提出各國可以用適當方式保護國內產業,在二○一八年推出新版的《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取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BBC,2018)。
此外,在北約領袖峰會上,他更當面、直言批評各國在軍事領域上投入過低。川普大動作地批評、試圖修正美國自冷戰結束後歷任總統的外交政策,這將會對美國的霸權產生如何影響?以下,讓我們依序從安全與經濟兩個面向來探討這個問題。

什麼是霸權?
「霸權」(Hegemony)的基本定義是:「政治、軍事、經濟上遠超過其他國家的單一國家。」冷戰期間,經濟上,美國憑藉其市場、資金、技術,東接歐洲、西連日本,串起了市場經濟的貿易格局。此外,美元在金本位制度以及石油以美元計價的影響下,更成為全世界的流通貨幣,加強了美國在世界經濟上的影響力。
在國際安全上,美國成了民主世界的守護者;歐亞大陸東側有美日同盟,西側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歐亞大陸兩側建立起最強的軍事同盟,並由此確立美國在自由世界軍事上的超強、領導的地位。
雖然美國的國力在七○年代末期有所起伏,然而冷戰結束初期,蘇聯的崩潰與美國的再次復甦,更確立了其原本就在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獨強地位。各國在經濟與安全上,皆依賴美國建立的市場與安全體系,且在各項實力上皆遜於美國。
學理上將單一超強國家建立、維護的穩定國際體系,稱之為「霸權穩定論」(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由查理斯.金德博格(Charles Kindleberger)於一九七三年提出。然而,經歷一九七○年美國國力起伏、國際關係中對於制度與實力的辯論,學界開始將制度補充於霸權穩定論之中,使得霸權的定義開始出現在國際制度層面和文化與制度層面的軟實力(宋學文,二○○四)。
更全面地來說,國際霸權在現今的討論中至少會包含幾個基本面向的定義:在安全上,它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經濟上,它掌握原物料、市場、資本;產品具備高度競爭力;提供一定程度的國際公共財;意識形態上,則能夠為其他國家接受。
冷戰結束後,柯林頓政府決定繼續維持冷戰期間的軍事聯盟並填補蘇聯崩潰後的權力空間。軍事聯盟非但沒有取消,反而透過擴大成員與軍事行動範圍來強化既有安全制度。美國在後冷戰時代,對於維護權力的企圖心無庸置疑。
 柯林頓(Bill Clinton)(Source: LBJ Library)
柯林頓(Bill Clinton)(Source: LBJ Library)安全領域上,來自德國的反抗
在川普治下,他指責北約會員國的軍事預算並不到其 GDP 的 2%,並要求各國提高其軍費支出,這作法動搖了美國在歐洲長期作為安全公共財提供者的角色。若從冷戰結束後來論,歐洲的確長期荒廢於軍事投資,使得美國負擔沉重。然而,川普的指責、試圖削減美國在公共財上的支出,不僅無助於夥伴關係、更削減美國領導世界的合法性。
甚而在學界中,已開始出現美國是否會從民主世界的保護者變成掠奪者的討論。自由世界領導人的反對,最明顯的例證,便是歐盟重要領導人德國總理梅克爾提出歐盟軍事上必須自立的言論。
二○一七年十一月,歐盟反而先行簽訂《永久架構協定》(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由歐盟內部要求提高各國國防預算、展開歐盟軍備項目並參與聯合演習等,讓歐盟軍事一體化邁開重要一步。社會科學的限制在於,研究者無法知道在另一個時空中,假如希拉蕊上臺,美國是否會一樣遭逢歐洲各國對美國領導的不滿意。可以確定的是,川普的非傳統外交模式勢必引來盟友對於美國領導合法性的質疑。
更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原先美國在國際制度中提供的好處開始刪減,使得各國開始思考是否接受或拒絕霸權提供的國際公共財。在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的理論中,國家會因為國際制度對其有利而選擇加入,亦即國際制度是基於現實、工具性考量。能因為利益而加入,自然也能因為利益消失而退出(Keohane, 1988)。
當然,基於歐盟的安全考量與歐盟的軍事能力,歐盟無法在短時間內離開北約自立,然而川普非傳統的外交模式,逐漸讓原本美國作為歐洲安全保證的唯一提供者的狀態產生裂縫。這結果,自然與美國嘗試繼續擔任霸權有所牴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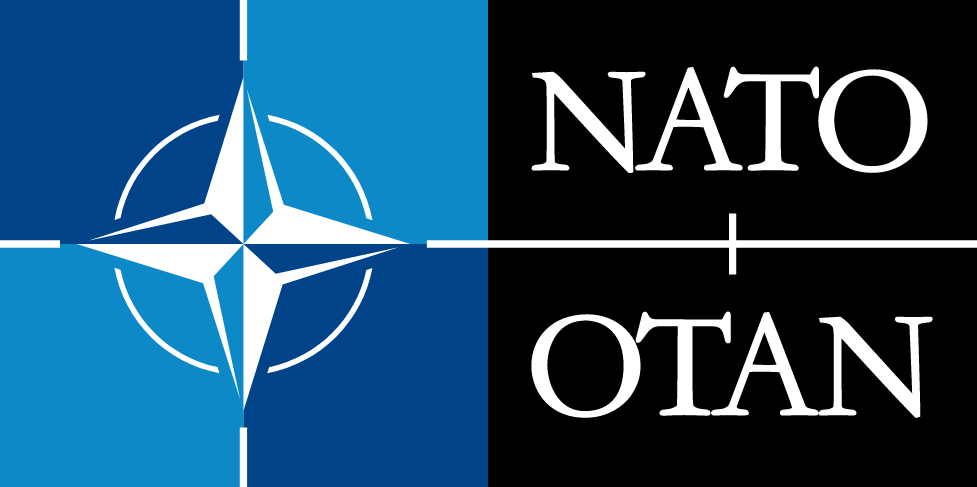
經濟領域上,來自中國的反抗
從貿易的歷史上來說,二戰結束之後,西方世界基本上信仰的是避免「以鄰為壑」(beggar-thy-neighbour)的貿易心態,因為「以鄰為壑」正是造成二戰前夕各國貿易大戰與經濟大蕭條的原因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國內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為了保護國內市場,共和黨里德.斯姆特(Reed;Smoot)參議員與威利斯.霍利(Willis Hawley)眾議員倡議提高進口關稅。
一九三○年美國胡佛總統在一千餘位經濟學家的強力反對之下,依舊簽署該法案,是為《斯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而在美國通過提高關稅來保護國內市場後,各國便先後採取報復性關稅來抵制美國,以及保護國內市場,這使得國際貿易進入黑暗期,各國經濟因此快速、大幅衰退。部分經濟史學家更認為,正是該法案的通過造成美國經濟大蕭條。而終結該法案的是二戰結束之後由美國主導所成立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該協定正式在一九九四年改名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換句話說,在過往七十年裡,人們不可以忘記的是,世界各國經濟穩定發展的基礎,實際上是從 GATT 到 WTO 的低關稅以及避免以鄰為壑的心態的功勞。
目前,我們尚且無法蓋棺定論川普的國際經濟政策,然而川普式的保守主義和非傳統外交方式所帶來的風險,正在撼動美國全球貿易領頭羊的地位,而結果仍未可知。
二○一七年的 G20 峰會首次出現的貿易保護言論,已先為美國政府留下未來貿易保護的後門。美國已經退出了泛太平洋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並且提出了新版的美、墨、加三國貿易協定。為了讓美國可以在中國與美國貿易中獲得公平的待遇,川普透過提高對中國的關稅發動「自損四百、傷敵一千」的貿易戰,威逼中國讓步。
正如同在安全領域上,川普要求歐洲各國提高軍費支出後,遭到來自德國的阻力,中國果不其然也以提高關稅作為回應。兩國之間的矛盾已經達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美國副總統彭斯更在二○一八年發表新一輪的中國政策,矢言要在新的大國對抗中取得最後的勝利。即便美國在占優勢的情況下,有極高的可能在貿易戰中獲勝,然而這樣的純然權力鬥爭,是否會對美國在全球經濟合作倡議上產生不良影響?這樣的連鎖效應,不就是令人擔憂的「以鄰為壑」嗎?
然而,川普政府在經濟上矢言為美國人民討利益的政策,真的會如他預期般的有效嗎?
川普式的保守主義與反全球化,真的可以解決美國產業轉型帶來的貧富差距與城鄉差距嗎?川普與中國的貿易戰中,的確可以增加美國許多夕陽產業與製造業的利潤,但夕陽產業的問題在於它不是未來,它終究要轉型。那轉型中對於二度就業的調適策略在哪?而製造業面臨的更大問題是人工智慧與智慧製造的浪潮(Ross,2016)。
從技術發展的角度,美國政府難以要求資本家們放棄更省成本的方式生產,轉而僱用更多傳統人力。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對於川普而言,美國利益的損失必須被導正,然而,美國經濟、甚至是整個國際合作的未來在哪裡?單純的大國對抗,是否是國家經濟發展的解方?猶未可知。整個國際合作的未來,如今猶如蒙上了一層迷霧,沒人能夠看得穿。
川普年代的全球化啟示
美國弱勢群眾對全球化的反撲,自然是此次川普崛起中對美國政治菁英最重要的教訓。然而,身處臺灣的我們,能夠在川普的崛起中看到世界什麼樣的發展趨勢與啟發?
首先,我們可以留意的是全球化造成的經濟利益分配問題日趨嚴重。全球貿易在過去數十年,已經幫助開發中國家的幾十億人口脫離貧窮,然而對於已開發國家來說,經濟利益的分配問題卻沒有獲得相應的解決。已開發國家的大公司,透過全球化提供的市場、人才、技術賺進大量利潤,然而底層、沒有技術、不具備國際移動能力的民眾卻無法翻身。財富分配不均導致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已經變成已開發國家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底層民眾的在職進修、再教育,以及協助產業轉型,已經是刻不容緩的問題。
其次,全球化的速率如果在國內無法取得共識恐萬難前進。在此次川普的選舉中,鐵鏽帶群眾的反撲就是美國對全球化產生疑慮的重要案例。然而,除此之外,我們也在二○一七年看到英國脫歐公投成功、法國出現極右派總統候選人勒龐並在兩輪制投票中獲得一千萬張選票,換言之,反移民、反全球化、反區域整合並非美國所獨有,而上述這些國家都是當初區域整合、全球合作的重要國家。
這說明,若國家無法成功整合國內反對聲音,全球化極有可能在政治上形成全球化退潮,並因此為全球經濟、政治帶來高度風險。全球化的發展,必須呼應地方政治發展的需求才能順利前進。
最後,鬆動的國際制度高度可能為原本就風雲莫測的國際政治投入更多不確定。川普的不確定、不可預測性,為國際制度投下了許多不確定性。若我們站在一個更高的視野來觀察國際關係,短期內美國霸權地位依舊不可動搖,各國依舊會試圖與美國合作來獲取更多利益,然而當美國過於我行我素、甚至開始恣意修改國際制度時,美國霸權的合法性,將一再受到挑戰。這對於霸權國與扈從的國家來說,都是嚴峻的挑戰。自然也更有可能產生安全上的衝突,美中貿易戰自然是最佳例證,而雙方安全衝突的可能性自然也因為敵意螺旋而快速上升。
川普式的保守主義與非傳統外交的表現,是反對過去觀點的全球化、反對美國利益受損,積極地施展權力手段以逼迫各國服從,這是這關鍵年代最重要的特色。對於全球發展來說,思考如何穩健地持續發展才應該最符合人類的利益。
然而這部分,首先出現了一個難題,面對美國積極地維護其利益,究竟是世界各國共同維護美國霸權符合人類的利益?還是,世界有其他的選擇?
川普的崛起固然是個驚奇,但也許他的出現更凸顯出在這個關鍵年代中,一個從未為人重視的幽暗陰影。美國霸權的未來將何去何從?世界,又會因此而變成什麼樣貌?
.png)
一本透過歷史了解世界局勢的書,12件關鍵年代的關鍵事件。
在這個紛亂吵擾、光怪陸離的時代,新聞幾乎以分秒為單位更新,電視頻道似乎就快要不夠看,網路又闢出多重戰場,世界在每個人的點指間鋪展,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動態成百成千從我們眼前溜過,每個瞬間都在創造歷史,而歷史,是連結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