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一般常引用的數字,1850 年到 1864 年間的太平天國戰爭,導致了兩至三千萬人喪生。據此,它被稱為人類史上最慘烈的內戰。近來幾篇研究對此時期流失多少人口莫衷一是,這顯示要回頭去做精確(甚或是粗略的)死亡人數統計是不可能的。
當時的記載顯示發生過規模驚人的屠殺和破壞,戰後所編纂的回憶錄及方志都以駭人聽聞的頻率,屢屢提及人口的巨大折損(長江下游市鎮喪失將近 50% 的人口,甚或更多),以及人們遭受了難以言說的痛苦。但無論這些數字精確與否,死亡人數顯然遠大於同時期的美國內戰(或稱「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約有六十二萬名士兵及五萬名平民死於該內戰。
可是,姑且不論這場戰爭的毀滅性有多強,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太平天國戰爭與那些照理說涉及範圍與影響都較小的事件相比,仍相對地罕為人知。即使是在中國研究領域內,關於太平天國的記述也驚人地缺乏血肉:我們只關注抽象的意識型態,而非戰爭所造成的傷害。關注十九世紀晚期上海如何崛起的學者們,常常會提及移民從繁榮、風雅的江南地區來到上海,卻從未敘述那場驅使他們背井離鄉的毀滅性戰亂。
在講授太平天國這段歷史時,海外中國研究學者的典型做法是,點出「它是史上最慘烈的內戰」這個事實,或是引用那個「兩到三千萬」的駭人數據;但接下來,我們(包括我自己)就會轉去講述耶穌的兄弟洪秀全和他的古怪願景──這常讓學生聽得津津有味。是時候重新思考太平天國諸方面孰輕孰重的問題了。

我在十年之前,曾寫過《清初揚州文化》(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這本書,講述揚州如何在 1645 年滿人征服後建構名勝。我在完稿前意識到,儘管自己已經看過清代幾乎所有版本的《揚州府志》,但獨漏 1874 年那份。所幸離我住所只有幾個街區的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就有這本府志。我走去圖書館,打算花上一兩個小時看完它,以確保自己不會錯過揚州府所有方志中任何有關清朝的記載。但那天,我在那份材料中的發現,卻改變了我對自己研究項目的理解。它讓我重寫了該書結尾,同時也開啟了一連串全新的問題意識,指引我走向現在這項研究。
我吃驚地發現,我在《清初揚州文化》 中提到(以及許多沒提到)的所有名勝幾乎都毀於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戰爭。更讓我震撼的是,我發現 1874 年版的《揚州府志》刻意用樣板化的方式,記載了太平軍佔領揚州時眾多百姓自殺或被殺的捨身成仁過程。我當時已有十多年的清史研究經驗,讀過一些關於太平天國的論著,也曾在課堂上講過太平天國史。可我從未真正思考過,這場戰爭對於地方上那些失去了生命、生計與所愛之人的幾百萬人而言,意謂著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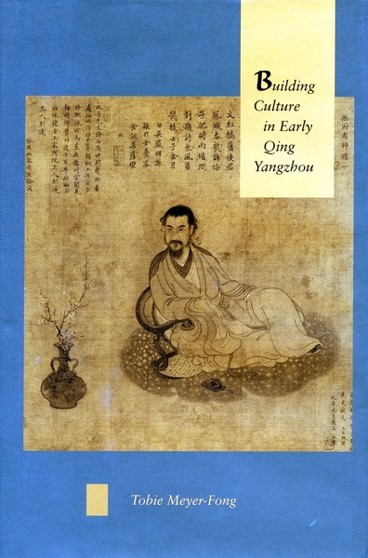
接下來的幾天內,我讀了數以百計描述忠義死節的記載,儘管這些故事和我當時努力要完成的作品沒有什麼直接關係。所謂「方志」,是將一個地方各方面材料按主題組織、編纂的匯總,在官員指導的名義下,由地方精英纂輯而成,對材料取捨有自己一套固定的原則。儘管此前的清代方志通常都記載了道德模範人物的傳記,包括列女、忠義、篤行、節孝、名宦和文苑,但這本方志卻著重聚焦於忠義死節者。
我後來才瞭解到,太平天國之後,江南地區的方志常常強調忠義,而且它們採用的編纂形式也頗為典型。這些有關死節者的故事被高度樣板化,除了死者姓名、社會地位、死亡地點與原因,並不提供其他訊息。例如,1874 年版的《揚州府志》記載的眾多人物中有這麼兩例:
「(咸豐八年)趙嘉琳,揚城再陷被擄。至三汊河時,賊以火藥實寶塔中。琳祕藏火種,擲入塔。是夜塔崩,賊死數千人,琳亦死。」
這本方志描繪了因為回嘴而遭剮、刺、劈、燒、或砍的死節者,以及自沉、上吊、自焚、絕食或服毒的死節者。每個故事皆以死亡發生的那一刻為中心,捕捉與太平軍對抗的關鍵舉動。每個被這樣記載的人,都因此從活生生的人被「轉譯」成道德的楷模,或是忠於朝廷的化身。
在這個「轉譯」過程中,每個人都被簡化,簡化到只剩下單一政治與道德意涵。他們的個人特質或經驗只留下能將他們塑造為忠義之士的部分,其他部分則不復存在。他們的義舉讓他們喪了命,卻也定義、定位、決定了一切,彷彿那英勇的一瞬間就證明了他們的紀念價值。
但我想要知道的是,死者們的屍骸下落如何?戰時如何安排葬禮?戰爭剛結束的時候,倖存者有多麼看重朝廷賜予的殊榮?對倖存者而言,喪失之痛會帶來怎樣的情感衝擊?朝廷賜予的殊榮似乎很自然地主導了紀念方式,但我們是否能在這些方式中,發現情感回應的蛛絲馬跡?
在官方的紀念中,死者是在一個極為特定的政治語境與話語中獲得意義的。透過道德化的語言,平凡的男女被塑造成烈士,而他們轟轟烈烈的死亡則充滿政治意涵與道德重量。地方精英們創作有關死節的道德故事,並將其上呈府、省、禮部的官員,希望能獲得承認。這些精英建立了符合清代價值觀及制度的祠祀,以供奉戰爭死難者。然而,也不過幾十年光景,這些看似為王朝殉死之人的故事就被刻意遺忘,被國家的新需求淹沒了。
在十九世紀末中國的大眾記憶裡,地方劫難的終極象徵不是太平天國戰爭,反而是年代更古早的 1645 年清廷對江南的暴力征服。這是因為人們解釋事件的方式改變了。在 1879 與 1880 年代的方志記載裡,十七世紀那種為明朝集體效死盡忠的行為,成了太平天國戰爭時期為清朝效死盡忠的先聲。將盡忠視為最至高無上的價值,是這種驚人的類比所試圖鼓吹的價值。
再到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滿清征服中原的故事又有了全新的意涵:不再是盡忠的象徵,而成了(漢)民族的恥辱。清朝已名聲狼藉,所以儘管太平天國戰爭發生的時間點較近,時人為大清殉難的行為已無法引起任何共鳴。人們於是替這場十九世紀中葉的戰爭樹立了一批全新的英雄,並賦予它一套全新的意義。
當公眾只聚焦於死節者的忠義與英雄主義,便抹煞了戰時破壞與殘酷的記憶;而有系統地排除太平天國製造的文本,則讓其他說法相對缺乏──至少短時間內如此。1911 年辛亥革命後,新的一批革命烈士取代了被前朝旌表的那些人。原本被用來紀念太平天國戰爭死難者的祠祀,也都改弦更張,轉而紀念為建立中華民國而死的人。有關太平軍及其對手清朝的文本與故事,凡是不符合新說法與時俱進的,都被曲解或忽視。肯定太平軍英雄行徑的材料,則在海外的圖書館裡被重新發掘,或是憑空捏造出來。
十九世紀中葉那些貌似為了清王朝而捐軀之人,在二十世紀時顯得既不革命也不進步,因而在現代中國史的主流論述中變得無足輕重──這些主流論述對戰爭、王朝、太平軍,甚至對於死者的評判,都做了一百八十度逆轉。從民族大義出發的新願景想像,掩蓋了無意義的暴力,掩蓋了情感,掩蓋了失去。原先那些紀念死者的方式,如今已不再有意義。與當初方志編纂者的用意背道而馳,對戰爭死難者的記憶消失了。
叛亂、革命、戰爭
十九世紀中國的這場內戰,常常被寫成一部傳記,講述一位夢想家如何掀起第一場革命運動的故事。1837 年,來自中國南方腹地廣東省的失意考生洪秀全陷入幻覺,恍惚中見到了令他不安的幻景。六年後,他從幾年前由傳教士手中得到的一部基督教小冊子裡,為這些幻景尋得了解釋。他聲稱自己是天父的次子,也就是耶穌的弟弟。他在家鄉廣收信徒,並從 1844 年開始,在廣西山區發展出一個融合基督宗教和民間慣例的體系,替他日後挑戰強大的王朝秩序奠定了基礎。

1851 年一月,在對官兵贏得了一場決定性的戰役後,洪秀全自封為「太平天國」的「天王」,這一舉動相當於宣告一個獨立政權成立。太平軍由廣西向北殺出一條血路,佔領沿途的戰略城池要地。謠言四起,沿長江而下傳到了三角洲乃至更廣的地方,引起焦慮與不安。1853 年,太平軍佔領並定都於明初舊都南京,並將之更名為「天京」。他們推行新的貨幣和曆法,宣揚自己的宗教,並構想了從未徹底實施的全新政府制度與地權制度。他們還把民眾組織成生產與戰鬥單位,並依性別來隔離劃分。
太平天國操弄著一種初生的漢民族主義:他們在宣傳上將清朝直接妖魔化,用「妖」字開頭來稱呼清廷,藉以挑戰滿人、朝廷官員及機構的合法性;他們還刻意屠殺滿人駐防地的平民。在建都後的十一年間,儘管內鬥幾乎摧毀了太平軍,但他們還是同清軍、地方團練、地方駐防與外國傭兵對抗,爭奪領土與稅收。由於地方頻繁反覆易主,平民及其賴以為生的基礎設施受到嚴重的連帶傷害。在十四年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清帝國二十四個省份當中,有十六、七省深受其害,其中又以長江沿岸遭受蹂躪最甚。
1860 年南京左近清軍江南大營崩潰後[1],太平天國在土地肥沃、商業化程度高的長江三角洲成功佔領了不少主要城市。從 1860 年到 1864 年湘軍攻陷天京的幾年間,連天烽火給此處的物、人都帶來災難性後果。清廷及其盟友也刻意將敵人非人化。湘軍的創立者曾國藩便在試圖剷除太平天國時,將他們形容為儒家文明之敵。

長江三角洲的城市難民們逃往鄉村,抑或奔向上海租界避難──上海此時得益於外國勢力的保護,而這些新來的難民日後將會改變這座城市。軍隊因起用俘虜和徵募新兵而逐漸壯大,也加劇了日益嚴重的暴力行為。交戰雙方為了餵飽膨脹的軍隊及團練,不得不四處打劫;同時,由於百姓也能被徵募為兵或是供給敵方物資,雙方都對平民百姓施以暴力。
隨著戰事延續,戰鬥也變得愈來愈弱肉強食、難以預料、混亂無比。隨著雙方都開始以徹底殲滅敵人為目的,這場戰爭也變得更加險惡。盟約薄弱且不可靠,財產也毫無保障。在一些案例中,兄弟和鄰居分屬不同勢力而互相作戰,很多社群也對該支持哪一方以自保而意見分歧。
1881 年,《無錫金匱縣志》的編纂者提到,戰爭摧毀了清朝幾百年來在人民心中建立起的和平願景,也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雖卒憑藉黃靈湔除腥慝,而數百年之保聚蹂躪無遺。其虔劉焚掠之慘,亦前此所未有也。
事情何以走到這樣糟糕的境地?無錫這份縣志的編者們將地方事件的災難性發展歸咎於官員無能與部分地方精英的收賄行為。他們指出,應付太平軍襲擊所做的準備既薄弱,又不徹底,主事者有部分責任。他們還指出,更糟的是,那些在春天收取租、稅的人們不但沒能守住縣城,還把他們徵收的錢物主動獻給了太平軍。被徵召來對抗太平軍的地方團練常常對農民和商人施以恐怖暴行。糧食短缺的軍隊是很難控制、很難維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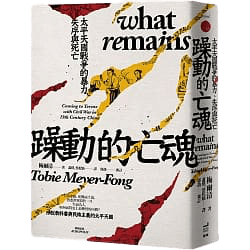
生而為人,如何面對史上最慘烈內戰?
掙脫教科書與民族主義的太平天國
躁動的亡魂,反映出躁動的人心。太平天國戰爭讓成千上萬人成為亡魂,並在無數生者心中烙下刻痕。
本書透過方志、傳記、詩集、外交文獻與傳教士報告,帶領讀者看見這些刻痕,看見當時人們最切身的經歷:失親之痛、對官府失能的憤怒,以及摻雜腐臭氣息與夢魘畫面的可怖回憶。
[1]編註:該年二到五月,太平軍再一次擊敗圍困南京城的清軍江南大營。江南大營由直轄於清朝皇帝的綠營軍組成,其遭太平軍擊敗一事標誌著清朝只得更加仰賴湘軍等地方團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