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七月,在票決七年後夏季奧運的主辦地在倫敦還是巴黎前夕,當時的法國總統賈克.席哈克(Jacques Chirac)似乎說了:「英國料理是繼芬蘭之後,歐洲中最難吃的,吃這難吃料理的人是不可信賴的。」我打心底想贊同席哈克,因為我在英國有過好幾次這種經驗,但或許「好吃、不好吃」都只是主觀上的判斷。
那麼,英國料理真的很難吃嗎?若真是如此,其中有什麼原因呢?當然其中也有氣候風土不適合栽種豐富農作物的自然環境差,但這些問題應該可以透過技術革新或世界性農作物流通來解決。
英國中世紀的王侯貴族之間有種習慣是,認為吃得多就是好。征服者威廉的食慾被傳說化了,而亨利八世那龐大軀體的肖像畫,也讓人們想像他是大胃王。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期的喬治四世與愛德華七世也一樣,後者的時代裡,上流階級中關於食量大的傳統到達了顛峰,人們都在競相較量腰圍的粗細。

上流家庭總是舉辦著沒完沒了的宴席,整個中世紀都是如此。喬治四世似乎說過:
我們的國民是由啤酒跟肉做成的。
與此相對,女王的飲食則似乎很樸素,例如伊莉莎白一世的晚餐,一直都是兩種套餐,雖每種套餐中有許多種肉類,但女王都只有吃一點點。她喜歡啤酒,很少喝葡萄酒。維多利亞女王對吃東西也沒什麼興趣,早餐只吃水煮蛋,用金色的蛋架和金湯匙來食用。
即便如此,奢華的宴席還是能在餐桌上反映出帝國的光明,所以英國花大錢雇用了法國主廚 M.Menage 來擔任總廚師長,旗下配置四、五人的廚師、廚房相關人員,其中最多的是法國人,負責提供給王族與客人豪華又豐富的套餐料理。
就像這樣,一直到近代為止,雖有大胃王國王,但在紳士以及中產階級中,作為近世以後的整體趨勢,節制飲食成為一種趨勢,並廣泛地傳播了開來。
英國料理很難吃?味覺破壞教育
在這方面最重要的契機是宗教改革。不列顛內戰的領袖奧立佛.克倫威爾甚至在聖誕節斷然實行斷食,受到人們仿效。十七世紀清教徒的牧師理察.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 )說過:「吃飯時間有十五分鐘就足夠了,要花一小時簡直是無聊。」他也說過:
美味的食物是惡魔的陷阱,不應該去看,吃窮人的粗食,就能免於墜落地獄。

若總是聽到這樣的說教,應該就會對飲食毫不在乎吧。宗教改革後,在英國紳士們間,為對抗法國人的英國國王以及對以其宮廷為主的飲食執迷與墮落,有人建議:「水煮或燒烤羊、牛、鹿等肉(尤其是腳、腿肉很紮實比較好)再沾醬料吃就好」。
紳士階級的子弟有大半成長期都在公學度過,公學於是成了粗食主義訓練場。哈羅
德.阿克通(Harold Acton)大臣回想起在朗伍德學校學生宿舍曾出現過的飲食:「我偷偷將又髒又油的人造奶油、帶有毛的豬肉、小牛的頭、腿肉凍、醃豬肉、粗糙的燕麥粥包在手帕中,丟到廁所。」
即便是在近年,似乎也有很多紳士只吃麵包、加了豆類與馬鈴薯的蔬菜湯,還有便宜的燻鱈魚或燻青魚就夠了,一個禮拜吃一至兩次便宜的雞肉或香腸就滿足了。
農民或勞動階級吃的飲食更為粗糙。他們的飲食很少肉類,主食是中世紀以來的燉蔬菜湯以及在奶製品中加入黑麥麵包或大麥麵包,但自十八世紀前半起,一般是吃米布丁,後半則是馬鈴薯。自 1860 年代以後,已經能大量供應代表勞工階級飲食的食材──馬鈴薯與魚類,形成了可作為現代英國料理代表的「炸魚薯條」而廣為普及。

可是,決定現在英國料理「難吃」的,似乎是維多利亞時期的中產階級。他們對於表現出快樂會感到緊張,所以主動避免這麼做。他們乘著工業發展的浪潮,賺了錢,住在打造得稍微好一點的房子裡,家中備置了漂亮的家具,但一旁卻聚集有心懷不滿的窮人。因此至少飲食要吃得粗糙些,藉由對食物無感,以消除那份罪惡感。
他們認為,在飲食上吃得快樂是步上身敗名裂與社會墮落之路,他們也嚴格禁止孩子們吃得很美味或是吃得像餓死鬼投胎那樣。總之,他們每天都很努力消除食物的吸引力,讓孩子對飲食沒興趣。
育兒書中也寫道:「離乳食應該要單調且難吃,為了靈魂好,須給孩子身體所討厭的食物。」難吃又乏味的食物是最好的。馬鈴薯泥、米布丁、燕麥粥、煮或烤的羊肉、葉菜類蔬菜……全都是乏味的食材。英國人終其一生都灌輸給孩子一個觀念──對食物不用有太高的期待。
如此一來,自十七世紀以後,尤其是在十九世紀時,除了庶民,連貴族都減少了飲食量,同時他們也不在意「好吃」這件事。對英國人來說,飲食無關乎文化,不過是為了活下去的燃料補給品而已。
或許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在十九世紀建立起了大英帝國。因為英國人不論去到哪裡,都不介意吃什麼食物,只是把食物當成「燃料」,只要迅速將食物放入口中、腹中即可,若沒了這些剛強的男性,或許就無法經營起殖民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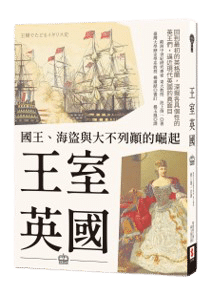
邁入二十世紀後,因大憲章的緣故,使皇室權力大減,歐洲王室陸續被廢止或形式化,但英國卻只有兩成名眾想廢除王室制度,改為選用共和制。追溯以英王為主的政治史、制度史流變,才能理解現代英國為何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