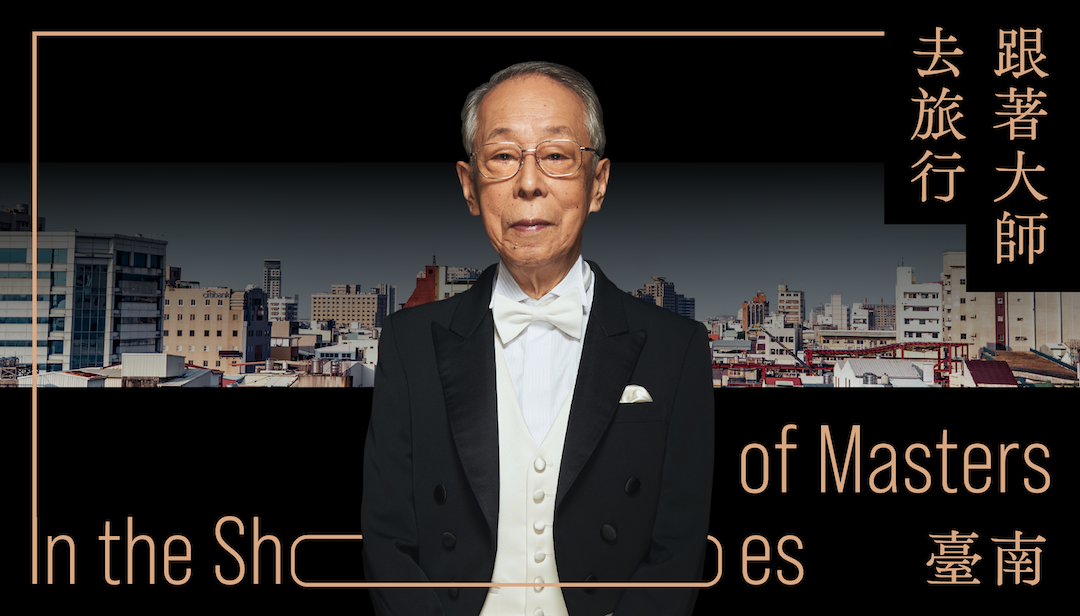斯波義信生於 1930 年的東京,1950 年進入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科,1953 年進入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碩士班,直到 1962 年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後,陸續在熊本大學、大阪大學文學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任教。自 2001 年起擔任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理事長迄今,同時也是日本學士院會[2]的一員,並於 2018 年獲頒唐獎第三屆「漢學獎」,其學術成就,不言而喻。

從經濟史研究出發,斯波義信的學術生涯
斯波義信很早就對都市史感興趣,特別擅長以社會經濟的角度切入討論。根據他個人的描述,在他讀高校的時候,就受西洋史教師松田智雄(1911-1995)的影響,特別喜愛德國中近世的商業史和經濟史。因此到東京大學求學時,他一方面選擇主修東洋史,另一方面則延續他對社會經濟史的志趣,成為周藤吉之(1907-1990)的高足,亦繼承周藤吉之的老師──當時甫過世的加藤繁(1880-1946)──的學術課題,在宋代市場、城市發展、商業組織、資本活動等議題上,發表了精彩的研究成果。最終,這些成就也讓斯波義信成為 1960 年代迄今,東京大學宋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代表學者。
不過,斯波義信對日本東洋史研究的貢獻,不單是在宋史領域與其個人的發表,更重要的是他能夠跨出日本,與國外學界分享、交流學問。斯波義信還是研究生時,就開始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會議,關注外國的中國史研究,也注意跨學科的研究方法。1960 至 70 年代正值美國的中國研究熱潮期,以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為首,聚集了一群社會學、地理學、人類學和歷史學者[3],共同探討中國的市場體系、社會組織、城市與移民的現象,以及其深層的歷史文化結構問題。
斯波義信取得博士學位後,仍時刻關注國際研究的動向,並持續與學界先驅對話。1966 年斯波義信在《東洋學報》中,就引介了施堅雅的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中國農村的市場與社會結構)[4]。 不僅如此,1970 年 斯波義信的博士論文《宋代商業史研究》刊行兩年後,即由伊懋可(Mark Elvin)翻譯成英文,並由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5]。
接著,斯波義信赴美參與了中國研究討論會,在這個由施堅雅等北美學者組成的跨學科地域史研究群體中,斯波義信提出以長江下游杭州灣南岸的寧波、紹興、杭州地區為具體個案,並運用施堅雅的都市分析方法操作都市與地域史的研究。 會後,斯波義信將相關的研習成果發表於施堅雅主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1977)以及個人專著《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1988)中,道出前人所未見過的中國研究觀點。
1960 至 70 年代斯波義信在學界的活躍表現,讓他成為溝通日本與美國漢學界最重要的橋樑,不僅消化了美國學界有關帝制晚期中國史(late imperial China)研究最新的課題與方法,也將日本學界中的東洋史研究成果推廣出去,例如「唐宋變革假說」就深深影響了施堅雅、伊懋可等人對中國歷史發展的看法。
融合東、西方學術觀點,開展中國都市史研究
回到斯波義信在中國都市史研究中的成就,他能繼承且融合來自日本及西歐的學術脈絡,並結合兩者的觀點進行討論。如此可貴的研究角度,起因於他的學術背景與環境。早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日本就透過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及東亞同文會,先後對臺灣及中國的慣習、法制、產業與社會組織進行全面的實地調查,且蒐集地方志及地方文獻,因而累積了豐富的中國都市資料。例如仁井田陞對北京行會的調查、今堀誠二在內蒙古及華北的城市調查,以及加藤繁擔任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囑託、參與《清國行政法》的編纂修訂工作。
這些戰前日本學者在中國及臺灣的調查活動,是日本中國都市史研究的先驅,他們蒐集與研究的成果,亦成為戰後東洋史研究的基礎。因此,斯波義信能充分運用戰前調查資料及地方志、地圖、碑刻、商業文書等地方材料進行研究,可說是得益於東洋史學界紮實的學術背景與積累。
另一方面,斯波義信個人對歐洲中近世史的興趣,對他發展中國都市史的研究有莫大影響。歐洲中近世都市研究尤其關注工商業活動、市場、同業團體(Guild)、中產階級、城鄉關係等課題,這種社會經濟史的分析視角由德國的歷史社會學者韋伯(Max Weber,1864-1920)集大成[6]。
韋伯曾以西歐中世紀城市為理念型(ideal type,比較的原型),對不同文明的都市進行比較與觀察,為西方的中國研究開創了新的典範,這種比較的視野貫串了斯波義信的宋史與都市史的研究。
1950 年代以後的中國研究者一方面受韋伯的啟發,另一方面也試圖利用更多的個案研究與實證資料,修正韋伯相對薄弱的中國論述[7]。施堅雅等學者則開始將人文地理學中的環境生態、空間型態、中地市場理論、都市等級與都市化等概念帶入歷史上的中國城市,同時關注城市內的社會如何組織運作,從而影響了斯波義信對於都市史的研究觀點。
從斯波義信 1988 年出版的專著《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中就可以看到,他一方面借鑒了施堅雅所提倡的區域史及整體史觀的研究取徑,另一方面,以宏觀的角度呼應施堅雅及章生道的都市型態理論。
2002 年,在《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出版十四年後,斯波義信完成了他另一本代表性著作——《中國都市史》,通論性地介紹施堅雅等人當年對中國都市研究提出的觀點,並展望未來的研究方向。
斯波義信在此書中提到,只用農村社會來理解中國是不夠的,中國的都市在歷史長河中也佔有一席之地,應該被學界重視。他希望透過這本書,結合都市行政史與聚落史(從地理學來說,都市就是一種聚落),說明中國都市和西方都市的共通之處外,也展現出中國獨有的特質,以及都市對鄉村所造成的影響。
除了整體性的介紹外,書中更以專章介紹幾個具體的城市個案,包括長江下游的寧波與上海、臺灣的臺南、臺北與新竹,以及廣東的佛山。這些案例或多或少以形成時間和空間環境的差異,各自回應了不同的都市史課題。
這邊值得一提的是,臺灣作為中國都市研究案例的意義。對 20 世紀以降的國外學者而言,比起因為文革影響,難以入境深入了解的中國,臺灣是相對便利的田野研究地點,因此,也成為學者研究中國社會的重要基地(如臺南的境、會、郊等,在 20 世紀的臺灣還有豐富的文獻資料與現況可以觀察。)
從中國研究的立場出發,當時的研究成果可以幫助學者去詮釋什麼是中國社會。如果從臺灣研究的立場出發,則更能協助我們把臺灣複雜多元的資料與現象加以理論化、結構化。
而在斯波義信眼中,臺灣的都市更被賦予了邊地、帝國前線城市的特殊意義。
以帝國邊陲城市的角度,觀看臺南的獨特性
在斯波義信的中國都市論中,臺灣被理解為「從中華帝國末期開始開拓,遠離首都政治中心,且與帝國本土相隔大海的邊疆領土」。臺灣城市的誕生、發展,甚至「中國化」的過程,在斯波義信看來,都是帝國邊陲城市的重要例證。尤其臺南作為臺灣最早形成的都市,經歷荷蘭東印度公司到清朝兩百多年的歷史,恰恰是說明「邊區城市生命史」的絕佳事例,臺南也保留了相對豐富的社會資料,非常適合用來展現和印證城市商業機構及移民的多元信仰等課題。在中國都市史的臺灣研究中,斯波義信先是從「聚落史」的角度來考察 17 世紀以來臺灣的歷史發展,主要參考的資料,為邵式柏(John R. Shepherd)的《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而他對臺南的細部認識,則是根據 1979 年臺灣省文獻會出版的《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
從外在條件出發,斯波義信先透過地文、外形、區劃描述臺南。透過這些資料,他注意到清朝文教機構、軍隊用地、商業活動中心等不同功能、人群活動的空間分布特色,也觀察到臺南的城牆建設時間甚至比諸羅、鳳山縣更晚的問題。他另一篇談論清代臺南府城的文章〈清代臺南府城の「会」、「境」と「郊」--旧中国都市における民間の公共組織〉,則從「都市化」的角度切入,以鄭氏政權的都市行政區域劃分,如何讓臺南進一步中國化開始談起,接著描述城內的官民寺廟、街路、官廳與商店的空間分布[8]。
從兩篇斯波義信的臺南研究中可以發現,他對臺南最核心的關懷,總歸是討論城市內外不同功能、形式、名稱的社會組織與其運作秩序。包括「會」、「街」、「境」與「郊」這些基層社會組織[9]。

除了近鄰與同業關係之外,還有同鄉、同姓組織,所有的組織往往以寺廟或神明連結、統合更廣泛的人群。因此城市的居民在不同名稱與功能的社區組織之間,常有多重歸屬的複雜關係。斯波義信對臺南城內傳統的空間概念賦予了社會學上的意義,使清代的臺南歷史研究能進一步理論化,更深刻地詮釋了傳統中國城市共同體的樣貌。
臺南歷史,不僅只是臺灣的歷史
前述斯波義信的都市研究,乃是建立在 1970 年代以施堅雅為首的中國都市模型上,將寧波、臺南、佛山等地視為中國城市的某些典型,從城市體系、空間型態、外來人口、社會團體等面向描述中國城市是什麼樣子。關於臺南,他以 1979 年出版的《臺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為素材,分別填進不同的城市分析課題,描繪出具結構意義的「歷史上的臺南」。不過,斯波義信將臺南都市歷史結構化,此舉反而將清代臺南定型、固結在一個型態,忽略清朝在臺灣兩百年間,無論政府體制和地方社會均有不同程度的變化。換句話說,斯波義信所描繪的臺南,是把不同時期形成的結構合併在一起,成就那一代學者對於帝制中國晚期封建城市的典型論述,而不一定忠實呈現當時的臺南樣貌。
儘管如此,斯波義信對臺南史研究的貢獻仍不容忽視,他將原本零碎片斷的臺南史蹟和歷史考證,透過施堅雅建立的中國都市史研究架構賦予學術上的意義。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掌握社會科學的問題意識、培養綜合地理生態環境條件的視野,將有助地方歷史與當代都市變遷之間的對話。
這樣的研究正告訴我們,臺南的歷史不只能說明臺灣自己的歷史,也能回應韋伯等城市史家提出的問題,從城市居民、社區或社會的角度出發,發掘城市自我發展的原動力。
(本文作者為臺灣大學歷史系專任助理教授)
附錄:20 世紀中國研究大師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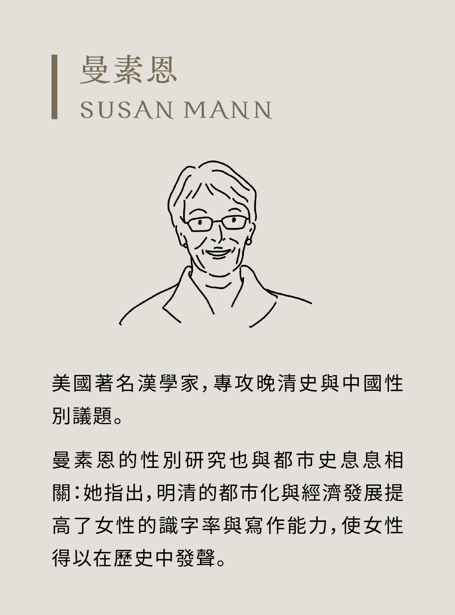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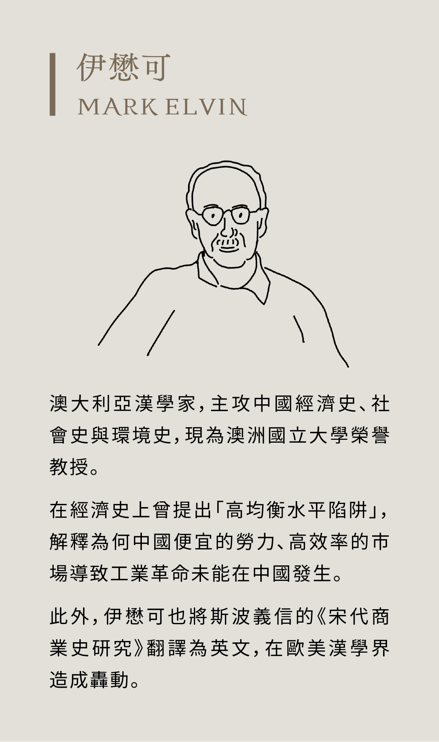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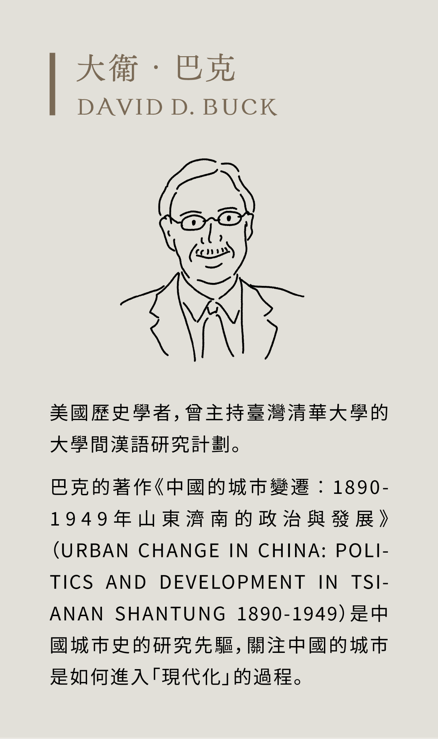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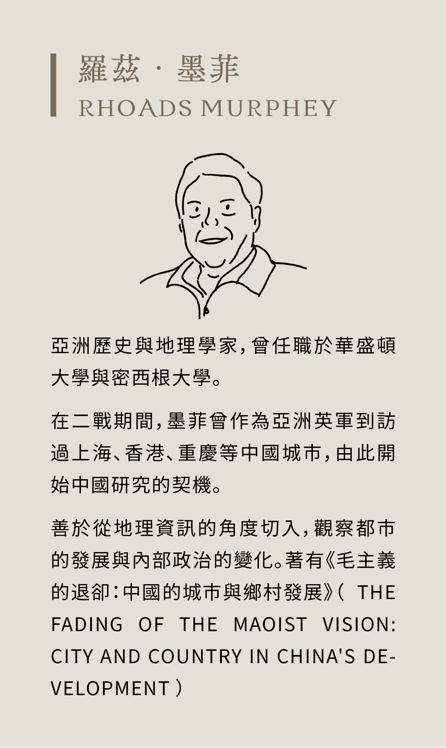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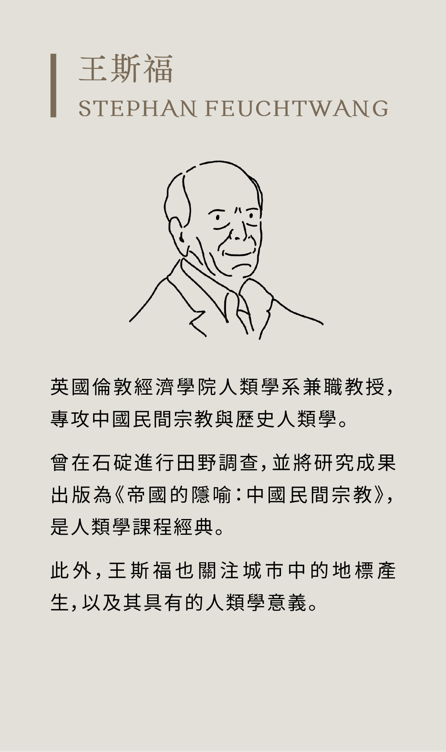
- Skinner, G. William.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葉光庭中譯,《中华帝囯晚期的城市》,北京市:中华书局,2000。)
- 斯波義信,〈G.ウイリアム・スキナー著『中国農村社会における市場・社会構造』 : 批評と紹介〉,《東洋学報》第49巻2号(1966)抜刷。
- 洪敏麟編,《台南市市區史蹟調查報告書》,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
- 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風間書房,1989年。Shiba Yoshinobu; translated by Mark Elvin.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 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0
- 斯波義信,〈宋代明州の都市化と地域開發〉,《待兼山論叢》第3号(1969-12), 127-148。
- 斯波義信,〈コメント 中国都市史研究より〉,《社会経済史学》53 巻 3 号(1987-8),421-424。
- 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経済史の研究》,汲古書院,1988。
- 斯波義信,《中国都市史》,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
- 斯波義信,〈清代台南府城の「会」、「境」と「郊」--旧中国都市における民間の公共組織〉, Asian cultural studies special issue (11), 39-52, 2002.
[1]唐獎,由臺灣企業家尹衍樑捐助成立,為鼓勵世人重新省思永續發展的中庸之道,設置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及法治四大獎項,不分種族、國籍、性別及宗教,自 2014 年開始以每兩年為一屆,遴選出對世界具有創新實質貢獻及影響力的成就者。
[2]「日本學士院」是日本對於在學術研究上,具有卓越貢獻人士,給予最高優遇的榮譽機構。其前身為 1879 年正式成立的東京學士會院。
[3]如伊懋可(Mark Elvin)、Rhoads Murphey、曼素恩(Susan Mann)、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David Buck、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藍厚理(Harry J. Lamly)、施舟人(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等學界先驅,皆是當時的中國研究大家。
[4]斯波義信,〈G.ウイリアム‧スキナー著『中国農村社会における市場‧社会構造』 : 批評と紹介〉,《東洋学報》第49巻2号(1966)抜刷。
[5]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風間書房,1989年。Shiba Yoshinobu; translated by Mark Elvin.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 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0.
[6]在韋伯的論述中,以西歐中世紀城市共同體為基準,比較不同城市的防禦工事、市場、法律、城市法庭、功能與組織等元素,認為包括中國、印度、中東在內的亞洲城市,皆缺乏西歐那種由市民階層共同參與、決策管理的城市制度體系,也沒有形成自己的城市和社區認同。換句話說,市民組織和認同意識因此成為東、西方城市最關鍵的差異。
[7]20 世紀以降的學者,希望能了解中國民間社會團體的形成與運作辦法。他們在明代的廣東找到「宗族」,在宋代找到「社」,在清代臺南不只找到「境」,也找到「會」(神明會)與「郊」;在臺北與新竹,則是透過清末的築城活動,看到民間社會團體的運作與能動性,進而突破韋伯的學說(見註六)。
[8]斯波義信,〈清代台南府城の「会」、「境」と「郊」--旧中国都市における民間の公共組織〉, Asian cultural studies special issue (11), 39-52, 2002.
[9]在一眾名詞當中,「境」也許是讀者最不熟悉的現象。其實「境」與會、行、郊、街等相同,是臺灣、福建等地普遍的基層社會單位。這些地方的民間社會通常以廟為人群活動核心,有些甚至以特定的空間基礎發展出社群網絡,承擔各種不同社會功能。斯波義信在臺南之所以關注「境」,是因為它時至今日仍在民間社會活躍。不過,「境」組織在中國、臺灣等地(如嘉義市區)都有分布,並非臺南獨有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