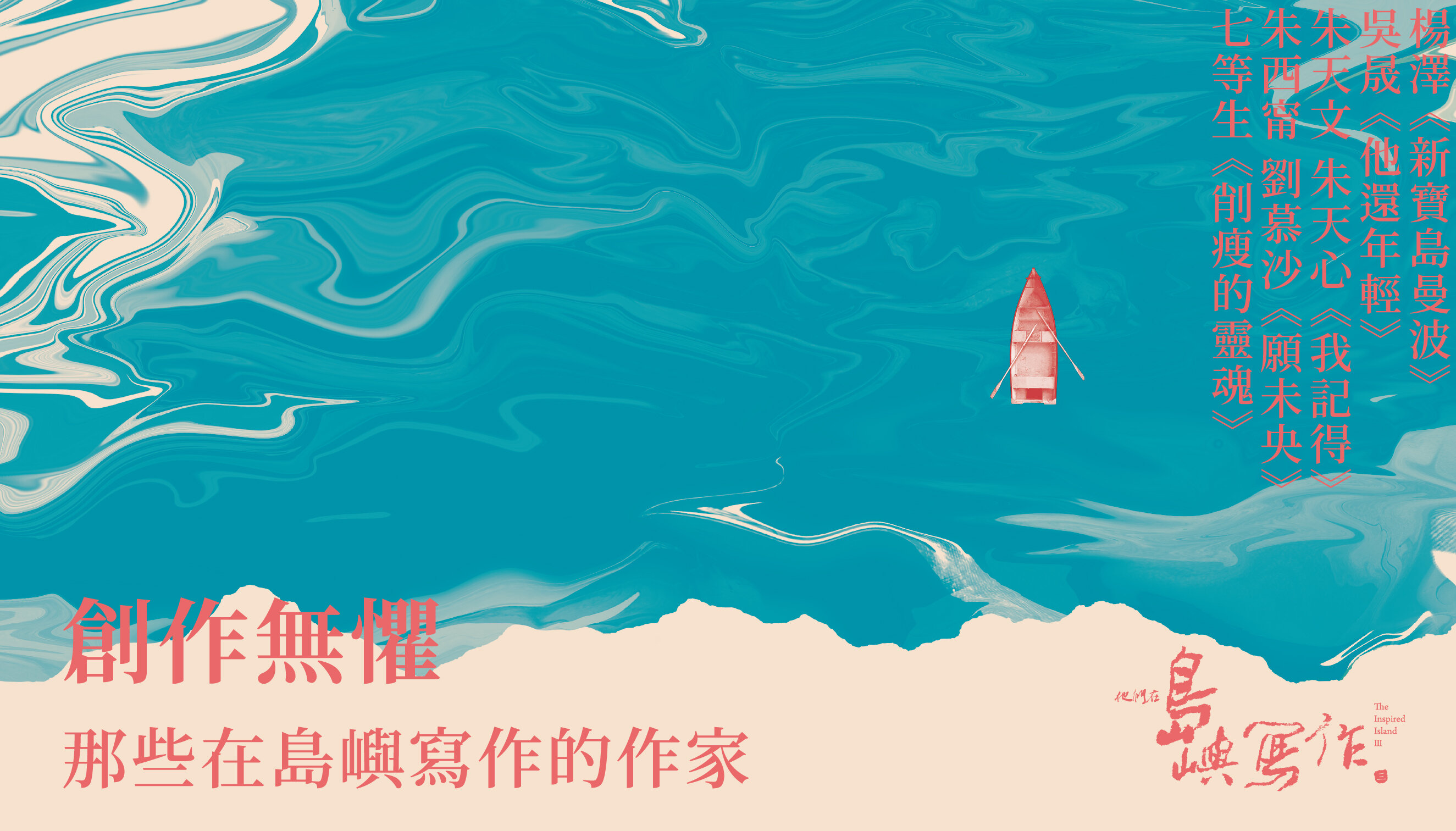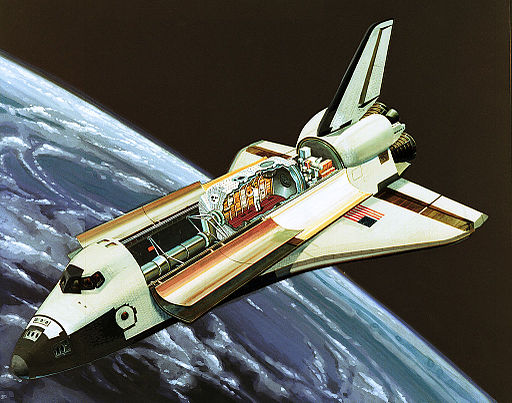大雨滂沱,黑濁的雨水大量滲進列車窗口,滋滋水泡不斷作響。列車的軌道向往何處?車上的大兵擔心驚惶,他們的目的地或許是左營。若真是左營,金門、馬祖就不遠了;距離死亡,其實也正是這樣一道海峽的寬度而已。
這是朱西甯《八二三注》的開場,場景就在陰鬱氣氛與等待心情、兵士的調侃與罵聲中揭開序幕──探頭的上等兵望向前方,隱約幽微的黑暗裡,列車、雨聲的盡頭,他看見了港口⋯⋯
書寫戰爭,卻非僅止於戰爭
該如何書寫一場只見砲彈、不見敵人的詭譎之役?擁有多年軍旅經驗的朱西甯,面對由軍人交織而成的「混亂的社會結構」,選擇延續先前的書寫風格──不鋪張氣勢之壯麗,不強調特定人物之英勇。戰爭的煙硝氣、血腥味於焉退居後位,浮出檯面的,則是再平凡不過的小人物生活。
這樣的安排,或許令讀者聯想到《狼》與《鐵漿》二本短篇小說集。它們承載著朱西甯的原鄉記憶,中國北方土壤氣息、無知而犯著「小奸小惡」的角色,以及難以排解的悲劇色彩,構成朱西甯此一時期的創作風景。而《八二三注》這本長篇巨構,令人矚目之處或許也正是它書寫「戰爭」,卻非僅止於戰爭本身,而是負載於歷史事件下方的密麻小「注」,軍人、原鄉與戰場的疊光重影。
這一行行注腳,不僅彰顯戰場上軍人的所思所想,亦呈顯戰爭與家鄉的辯證張力──何處是家鄉?何處是戰場?面臨這些問題的齟齬可想而知。在兩岸形勢已定,美國持續介入調停的歷史背景下,彷彿總有些問題,不能回應,只能超越,或者無視。「時間」,於是成為一再延擱結果的修辭:
他珍惜的摩搓著指間的細沙,另隻手摩挲著原先扎了刺的地方。現在是光光滑滑了。雖很鬆暢,然而有些不習慣。不過一個月而已,卻會這樣子了⋯⋯可笑!—《八二三注》(頁 537)
三個月零十天,鋪衍六十萬字長篇小說,時間的調度既是敘事技術所在,亦是故事核心關懷。《八二三注》從景色陰鬱的高雄港口一路寫到情節中段,才真正發生一場「惡戰」(此前只有砲擊),並擄回一名疑似被下蠱的俘虜。可即便如此,主角黃炎「還像是做了場夢一樣,繼續恍惚著。」他繼續思想、遊蕩,徘徊在人道關懷與婦人之仁的掙扎。
故事中,黃炎的漫遊甚至行進至更遠的位置,以致他即將觸及周遭詭譎戰爭的內在意義:「這獵物將可活下去,由野獵而家畜,而和我們一樣的被信任著,成為這個戰鬥體的一員,那麼我的惻隱,不忍,甚而自我鄙夷,將從何而生?可以無中生有嗎?他追索著,追索下去⋯⋯」就在此時,黃炎無意間將下巴那顆生長已久的「刺」摳了出來。於是讀者未獲結論,再度跟隨主人翁跳入時間漩渦中──解答被延擱了,成為永無止境的謎。
事實上,若從同樣的角度看「八二三砲戰」本身,何嘗不是一場延宕二十一年的戰爭?雖然砲擊頻繁僅止於戰事前三個月;然而直到 197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停止炮擊大、小金門等島嶼的聲明〉一文發佈,炮戰才正式劃下句點。與此同時,曾經歷八二三炮戰的兵士發現,時代的滾輪果然繼續前進著不等人,島嶼臺灣即便一腳踏入新的政治生態,解答仍在遠方,家國故土、戰爭情懷遺留在歷史的荒原上,待人作注。
是年,朱西甯《八二三注》於「三三書坊」出版。

眷村,是否能成為家的代名詞?
曾幾何時,朱家少女仍意欲著離開眷村、影響世界。「三三」,三民主義、三位一體的融合接洽,正是此一時期下迸現的閃亮星辰。
不過說到「三三書坊」,不得不先提這群少女們的母親──劉慕沙。當時省籍對立尚可稱做劍拔弩張,本省籍的劉慕沙與外省籍的朱西甯相戀,這位苗栗女子不顧家中反對,毅然決然與窮士兵攜手終生。這對相愛卻礙於家世背景而陷入苦戀的夫婦,活成了眷村裡的部分縮影,以此為「家」的所在,落地生根,並替時光見證了外省與本省藩籬的消失。
朱天文曾如此寫道:「這兩種文化構成,自然且當然,已成為我寫作的意識底層。我從它們來,也從它們源源生出作品,它們是我書寫的核心。」
劉慕沙同樣鍾情創作,小說多以自身的生活經驗為背景,能使人窺見數十年前的在地生命軌跡,感受那個質樸、醇厚的年代。除了出版短篇小說集《春心》之為外,劉慕沙也持續在翻譯日本文學的路上耕耘,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大江健三郎等日本名家,她都曾有譯作,並將翻譯文學融入自我創作中,形成獨特的行文風格。
浸淫在如此文學環境中,朱家三姊妹也開始呢喃獨屬於她們眷村私語。
叛逆的眷村男孩畢楚嘉如何從淡水海岸離開,拋下一切過往,成為空軍;或許,也還有些許印象,親眼見過那些漫遊在城市裡的外省青年。這些夢寐記憶,在族群與國家認同逐漸轉型的島嶼,彷彿蒙上一層傳說般的翳影,瀰漫在三三的書寫世界中,為讀者留下了一則又一則、綿延不止的典故。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我只是向中華民族的江山華年私語。他才是我千古懷想不盡的戀人。—《淡江記》
三三書坊出版的一系列作品,不僅勾勒出 70、80 年代臺灣文學史的側影,同時也是定位朱天文、朱天心兩人早期書寫的標誌。在此一時期的書寫實踐中,文學少女受胡蘭成影響,筆下無盡的抒情姿態與張揚的中華傳統敘事密不可分,神州大陸的想像與光復河山的衝勁緊緊綰合。此時的眷村,還充滿著青春生氣;或許,甚至可以說,在朱天文和朱天心兩人的筆下,它仍然透顯著一種專一而天真的想像。
然而,從什麼時候開始,眷村的實體漸漸不再存在,而成為記憶中迷茫的幻影?

眷村內外的難題,外省本省的糾結
詹宏志曾在 1989 年出版的《我記得⋯》一書序言中說道:「讀單篇小說時,我依稀感覺到朱天心『變』了,但究竟轉向何方,變成什麼樣的異型,卻沒有什麼概念。等到讀若干篇小說時,一個創作家同時期的關心,某一階段的思想與人格,就給我們一個圖像了。」在這本短篇小說集子與接下來出版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讀者可見這種轉變之劇烈──朱天心的筆鋒銳利起來,開始質疑政治理想的真實性,包括〈新黨十九日〉、〈佛滅〉,也轉而將自己帶入所謂「畸零族群」的認同裡。
「逐漸消逝在人群中的眷村兄弟」,被朱天心辨認為畸零族群的一種。在初版《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封底,一一說明了集子收錄的六個畸零族群,並接續說道:「它們隱密、破碎、不為人知、不易辨識,更不為政治和大眾傳播媒體所同情支援。」不難發現,朱天心此時的創作已經面臨艱難的認同危機。她反覆在故事裡藉敘事者口吻定義眷村子弟的性格,並且在最幽微處,發現了外省人在島嶼的處境:「清明節的時候,他們並無墳可上。」
離開眷村的少女朱天心,也許並沒有如她所想改變世界;反而令她難以迴避與拒絕的,正是眷村的消亡本身。因此,在出走與回首的辯證之中,讀者看見一個不斷揣度與思量的身影,一則關於眷村的典故:
至於那些為數不少、嫁了本省男子、而又在生活中屢感不順遂⋯⋯因而會偶覺寂寞的想念昔日那些眷村男孩都哪兒去了的女孩兒們,我在深感理解同情之餘,還是不得不提醒妳們,不要忘了妳曾經多麼想離開這個小村子,這塊土地,無論以哪一種方式。—《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頁89)
世紀末的華麗,還在繼續
從三三時期鏡頭走出的另一人,是朱家大姐──朱天文。她早期的創作〈小畢的故事〉,後經電影改編,成為臺灣新電影重要的代表作品。在此之後,《世紀末的華麗》與《荒人手記》等書,則一步步將重心從眷村生活移往都會,從黃金的三角結構踏入張揚的情色描寫,而寫作風格亦從原先胡蘭成式的抒情宇宙,轉往張愛玲的蒼涼廢墟邁進。

90 年代,臺灣悠悠然邁入世紀的最後十年,朱天文筆下記載的「新人類」蜂擁攢動,如織錦棉絮漫天飛舞。然而,在這華麗的血肉賁張的現場,也正如詹宏志所指出,「卻透露了腐爛錢、衰敗前的有機分解。」《世紀末的華麗》書寫的,是不斷繁殖叢生的記憶碎片,以及近未來卻同時瀰漫著上古斷簡殘篇的預/寓言。
然而突然來的厭世情緒又將它席捲,天啊慾望臨陣起義,又背叛了他。他眼見身體那座亙古聳立的金字塔霎時已潰塌在前。他沃沃心田頃刻間荒蕪了下來,完全荒蕪。—《世紀末的華麗.肉身菩薩》(頁53)
朱天文和朱天心的後期作品,有肉身菩薩在三溫暖裡無盡徘徊,有老靈魂在古都裡踏著漫遊步伐。新時代將臨,終究伴隨著舊世代的殞滅。廢墟與神殿同時矗立,重層疊影,衍生出「老」與「新」、「記憶」與「遺忘」的矛盾修辭。而時間作為拉扯兩端的主要張力,好像要麼緊繃,要麼完全碎裂。
讀者從這些文字裡,依稀可見那徘徊在本省、外省間的認同危機,或者甚至完全不要,歷史沈積的意義一併讓渡給全球化資本主義,連最後一點身世都蕩入大洋裡頭,扯出夢幻泡影。
走向世紀末,是否正如一級級向下階梯,越走,越發現光在後頭,而前方完全暗了?至於歷史,果真朝熵增的混沌狀態邁進,驀然回首,少女發現世界已不再是天地之始、禮樂的城邦,但她們的書寫還在繼續。
文學,是歷史的證言
文學,同時也和歷史、政治緊密連結。作家或許難逃一再被解讀的命運,然而解讀有時意味著一種記憶、銘印在心。銘印那些已被遺忘的過去,那些曾經存在後來消亡的掌故。
朱家的文學,已然成為一個時代的縮影,閱讀這些作品的同時,也是翻閱著過去的時光和記憶,提醒著我們──不要遺忘。
《願未央》、《我記得》
平凡的桂花樹下人家,塵封著父親小說家朱西甯與母親翻譯家劉慕沙的書信,他們的情書非情書,還題下「唯有文學,不能平凡」的鴻鵠大志,一個隨國軍來台的軍人,與本省籍的醫生千金,在歷史交會點寫下深刻愛戀。
《願未央》由長女朱天文首執導演筒,偕同侯孝賢領銜的劇組班底,拍攝團隊遠赴中國探親、走訪台灣舊居,並透過珍貴的家族照片與難得的豐富史料,呈現出這個絕無僅有的文學家族開枝散葉的歷程。他們將生活過得簡樸,但對於文學終其一生不能平凡的大願,依然在第二代女兒的紙筆中虔誠地追逐著。
《我記得》──文壇傳奇姊妹,姝途刻畫人生
稿紙糊成的文學朱家,孕育出嗜字如命的傳奇姊妹——朱天文、朱天心。這對姊妹雖同根共生,但各憑本事在稿紙格線攻城占地,建立起風格殊異的強大文學國度。
《我記得》由小說家林俊頴執導,以長年友人的貼身視角,紀錄朱家姊妹的成長軌跡,從桂花樹下的家作為記憶的場景出發,在此雙姝少年師承胡蘭成、廣交才俊創立《三三集刊》。鏡頭隨著她們的腳步移動,走訪鳳山眷村故居,渡海祭拜東京胡墓,談笑間分享對彼此作品的見解,也錄下她們穿梭街頭巷尾照顧流浪貓的身影。姊妹倆在片中毫無保留地坦露內心,展現文學成就背後,如同常人一般隨性親和、溫暖立體的生活光景。
▲《願未央》正式預告:https://reurl.cc/oemAXM
▲《我記得》正式預告:https://reurl.cc/
▲電影預售票:https://reurl.cc/Qj2DQb
- 王德威,〈老靈魂前身今世──朱天心的小說〉,收錄於《古都》,頁9-32。
- 王德威,〈戰爭敘事與敘事戰爭:延安,金門,及其以外〉,《中國現代文學》(2005年,27期),頁1-25。
- 朱天心,《古都》,麥田出版,1997年。
- 朱天心,《我記得⋯⋯》,遠流出版,1989年。
-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麥田出版,1992年。
- 朱天心,《漫遊者》,聯合文學,2000年。
- 朱天文,《小畢的故事》,三三書坊,1981年。
- 朱天文,《世紀末的華麗》,遠流出版,1990年。
- 朱天文,《淡江記》,三三書坊,1989年。
- 朱西甯,《八二三注》,印刻,2003年。
- 朱西甯,《狼》,遠流出版,1994年。
- 朱西甯,《鐵漿》,三三書坊,1989年。
- 吳忻怡,〈成為認同參照的「他者」:朱天心及其相關研究的社會學考察〉,《臺灣社會學刊》(2008年,41期),頁1-58。
- 邱貴芬,〈想我(自我)放逐的兄弟(姊妹)們:閱讀第二代「外省」(女)作家朱天心〉,《中外文學》(1993年,22卷3期),頁94-110。
- 柯慶明,〈論朱西甯的「鐵漿」〉,收錄於《鐵漿》,頁245-291。
- 張大春,〈一則老靈魂──朱天心小說裡的時間角力〉,收錄於《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頁5-22。
- 張瑞芬,〈明月前身幽蘭谷──胡蘭成、朱天文與「三三」〉,《臺灣文學學報》,(2003年,4期),頁141-201。
- 黃錦樹,〈從大觀園到咖啡館──閱讀書寫朱天心〉,收錄於《古都》,頁235-282。
- 詹宏志,〈一種老去的聲音──讀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收錄於《世紀末的華麗》,頁7-14。
- 詹宏志,〈時不移事不往──讀朱天心的新書《我記得⋯⋯》,收錄於《我記得》,頁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