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曾經在地理課本上學習過:「臺灣四面環海」。但我們和「海」的關係其實相當陌生。如果一個人能夠忠實地活在大海之中,活在自己的文化之中,那會帶來什麼樣的視野?2024 年 4 月 25 日,第 23 屆國家文藝獎頒獎典禮前一天。臺灣知名的海洋文學家、小說家夏曼.藍波安的眼中有一絲趕場的疲倦,但更多的,仍然是樸實不羈的神情。
對這位大半輩子都與海洋共同生活的達悟族作家而言,國家文藝獎意味著什麼?「對我來說,這是莫大的榮耀,但同時也有壓力。因為接下來無論是身分轉換、作品轉型,都會成為我的挑戰。」夏曼.藍波安如此說道。不過,在接受這份榮耀以前,那首先是出自一種有意識的拒絕,以及抵抗——
改名的身分證,有意識的拒絕與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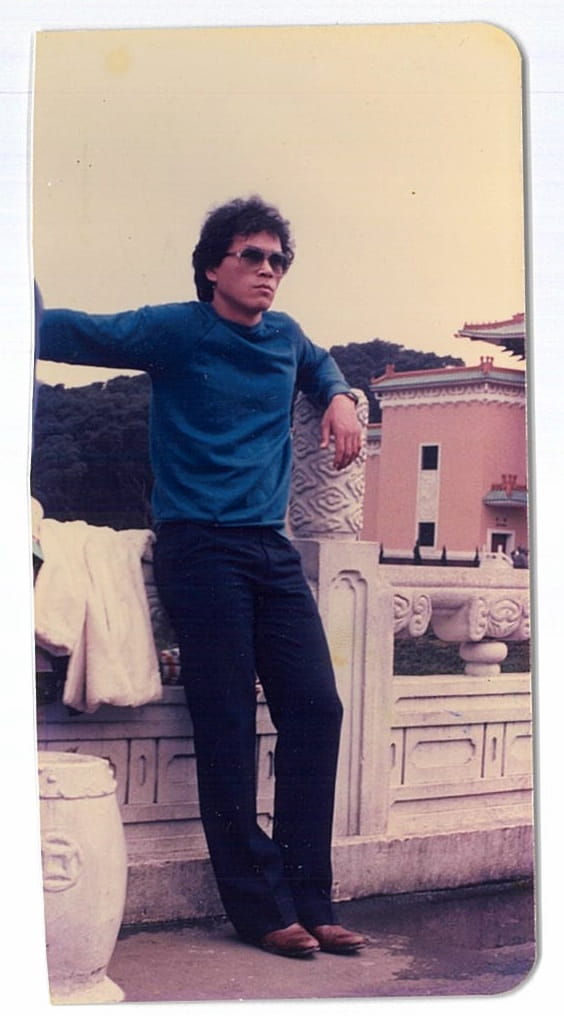
夏曼.藍波安回顧自己將近三十年來的寫作態度與書寫初衷,「我從來都拒絕去模仿漢人作家的樣子,也拒絕模仿國外的小說。」不只是教科書上必定會收錄的代表作《冷海情深》,以及《航海家的臉》、《天空的眼睛》、《大海之眼》等作品,再到近年出版的,獻給 Sira Do Zawang(河谷家族)的長篇小說《沒有信箱的男人》。無論寫魚,寫神話,寫家族史,身為作家的夏曼.藍波安,每一本書的創作命題都是從達悟族文化中萌芽。種種敘事,也與海洋有著密切關聯,「我寫海洋,因為這就是我們的民族文學,和陸地思維是完全不一樣的。」夏曼.藍波安表示。
不只是寫作,他很早就已經選擇去抵抗某些事了。在錄取率不高的聯考時代,夏曼.藍波安拒絕保送入學,靠自己考了四次才終於考上大學;拒絕使用漢名,1990 年代初就已經前往戶政事務所,將自己正名為「夏曼.藍波安」之外——他也曾經站出來拒絕過更龐大的事情,例如國家政策。
正好是整整半個世紀以前。1974 年,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展開「蘭嶼計劃」,核廢場地點選設在蘭嶼,數年後蘭嶼貯存場第一期完工。1988 年,有一批達悟族人站在核廢料貯存場前面,發起「220 驅逐蘭嶼惡靈」反核廢料運動。第一波只有一百多人參與,第二波幾乎全島的達悟族人都來了。
⬆自 1988 年第一波「驅逐蘭嶼惡靈」反核廢料運動開始,至今已持續超過 30 多年。影片為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製作的專題《惡靈退散》,其中記錄了 2011 年夏曼・藍波安等達悟族人到總統府前抗議之畫面。
作為曾經的發起人,夏曼.藍波安淡淡地回憶:「那幾年,大概 1984 年左右吧,我們有幾個人就已經去行政院抗議了,也有去寫一些請願書、上街頭。」這些 1980 年代風風火火的原住民族運動不是「別人」的故事,更不是二手資料,全是他(們)共同的見證:1987 年東埔布農族挖墳事件、湯英伸案、1988 年吳鳳銅像破壞事件、還我土地運動——彼時還是一個原住民族大學生的他,當然也在場。「我在臺北,街頭運動我們已經做了好幾次了。」夏曼.藍波安說。
當警察來到島嶼,「國家」意味著什麼?

那也是臺灣才剛開始解嚴的頭幾年,「我並沒有被國民黨馴化,也沒有被中華民國馴化,這些蘭嶼的自決運動和民主運動,都是我們自己去開創出來的。」夏曼.藍波安說。在 2018 年出版的小說《大海之眼》中他描寫臺東縣警察局蘭嶼分駐所,以及外來者試圖灌輸「國家」軍訓思想給蘭嶼人的過程。註解寫道:國家是新的詞彙,對我民族而言。
所以,國家究竟是什麼?當年日本警察來到蘭嶼,「我爸爸他們就已經認知到了,日本是一個國家。」這些殖民者並沒有在蘭嶼殺戮,最殘忍的行為也就「只是」拘留人民。夏曼.藍波安補充:「更多口述故事,也有收錄在去年國史館出版的《雅美族紅頭部落歷史研究》裡面。」現代國家的形成,時常是建立在對原住民族「野蠻」的排斥,甚至清洗之中建構的。非得要透過人的敘述、書寫,才能把故事重新揀拾回來。
夏曼.藍波安也有意識地抵抗漢化。他說:「就我自己而言,國家比較屬於政治面的認同,也就是說我們非漢族的原住民、海洋民族,接受了被統治的體制,但不一定有文化上的認同。」國族與我族之間,其實有著相當明確的分野——作為一個非漢民族的華語文學作家,夏曼.藍波安認為,自己是向漢人「借貸」漢字,用來描寫達悟民族的星球。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星球

而我們其實住在不同的星球上——在這廣袤的世界中,由於語言、民族的不同,自然也會形成不同的文化和宇宙觀,這樣的差異,夏曼.藍波安稱之為「星球」。相當有趣的是,這種星球想像,也不若「地球」的框架那麼唯一,反而更像是共生共榮的星群。夏曼.藍波安說:「當我說我們住在不同的星球上,其實意思指的就是多元生物,多樣民族。」
達悟族有一個極為美麗的,描述靈魂與星星的故事:「我們達悟族人的靈魂在宇宙裡都有自己的星星,很亮的就是呼吸很長,不太亮的就是呼吸很短。」夏曼.藍波安的族名,即為織女星(Nuzayin),海天一線。
這些是我父親(Yama)說給我聽的。不過這是我父親講的,夏曼.藍波安笑了笑:「我母親(Ina)是說,你把你右肩的靈魂放到星星上。現在苦了我,因為我的靈魂一直在那顆星星裡面流浪,我沒辦法把它帶回來,那就讓它在天上流浪吧。」這是神話,親情,也是生命。
最終,它們都成為了珍貴的文學養分,得以發出獨特的聲音。不需要仰賴其他文學典範或前輩大師,作為海洋作家的夏曼.藍波安,所見所聞的全都是家族中經年累月、傳承而來的神話口述故事,以及自己親身實踐過的經驗。在《冷海情深》的序言裡他就已經說盡一切:「達悟男人們的思維、每句話都有海洋的影子。」
遊牧的身體,深邃的眼睛

在這樣的口傳基礎中,夏曼.藍波安的文學,也大多以「我」第一人稱開啟,「漢人有句話叫『船過水無痕』,但我是身體過了,記憶會留下。」夏曼.藍波安一語道破現代性的終極矛盾:「會船過水無痕,其實是因為這艘船不是你做的。」如果你沒有去真實地經歷過、感受過,那麼你自然就會流失它。
「當然,我一個來自小島的原住民作家,與臺灣漢人作家,寫的東西必然是不同的,我們有各自的思維和價值觀。」夏曼.藍波安的語氣中帶著一絲不以為然:「我也不喜歡劇情很複雜,轉來轉去的。因為我不想要寫那樣的東西——如果只是一直坐在房間裡構思情節,但你的生命都沒有在太陽底下走來走去,那文學要怎麼發展?」小說家那長年被曬得黝黑的面孔,露出不解的困惑。文學,是要用全副身體兌換來的。

夏曼.藍波安拋出了第二個尖銳的辯證:「而且,為什麼很少有臺灣作家願意去關心更多島嶼以外的議題?」他強調,當他選擇以「達悟族」的身分開創臺灣的海洋文學視野,把自己的想像與身體帶到國外去,不是為了要獲得讚美或是國際掌聲,而是希望讓臺灣文學的廣度與深度都有更豐沛的層次,同時,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傳遞出這樣的信念。
只有行動者不留遺憾。作為有意識去傳承這一切的原住民作家,夏曼.藍波安說:「而我的夢想是什麼呢?靠自己考上大學,我實現了。靠自己考上研究所,我實現了。靠自己的身體去流浪,造船前往大西洋、南太平洋,這些事情我也都去實現了。」夏曼.藍波安說得坦白:「不過這種遊牧的身體狀態,沒有經歷過的人很難體會,是無法去想像的。」
乘著拼板船,一次又一次地划槳

那些拼板舟(達悟語為 tatala)都是一塊一塊拼出來的。不需要用上任何一根鐵釘。倚賴的是對大自然的敬重,情感軌跡的傳承,以及嚴謹細密的木頭工法。當別人搭乘著快艇、機動船、豪華郵輪的時候,他一次又一次地親手划槳。航行在海洋裡,也航行在文字裡。
2007 年,夏曼.藍波安與叔父合力建造一艘雙人四槳的拼板船。彼時,叔父已經是八十二歲的老人了。傳統的達悟族人以什麼樣的方式活著,夏曼.藍波安也以那樣的方式活。他與父輩共同造船,如今也帶著兒子造舟。於是,夏曼.藍波安大概也是全臺灣(甚至全世界)最有資格說出這句話的人了:「哪個作家,他能夠有能力去潛水、抓魚、造船,並且以這樣的方式養活家人?」
海洋小說家以非常達悟族的語言,如此描述:「我還在浪花裡打滾。年輕的時候,整片海洋都是我的世界。不過年紀大了,現在只能在浪花最脆弱的地方打滾。」他頓了頓,「也就是說,當我的體能衰退,思想也應該要逐漸成熟結實。」提起浪花,夏曼.藍波安的表情變得炯炯有神。浪花不死,海洋仍然繼續帶著他到處流浪,「例如去跳島啊,我還有很多想寫的。之前也有作家紀錄片,拍攝我和我兒子上山伐木、造舟的畫面,也有預計要出一本詩集和散文集給子女。」
一次划槳,是十片魚鱗的紫色螢光在閃爍。活在那顆他心有所愛的星球上,夏曼.藍波安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划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