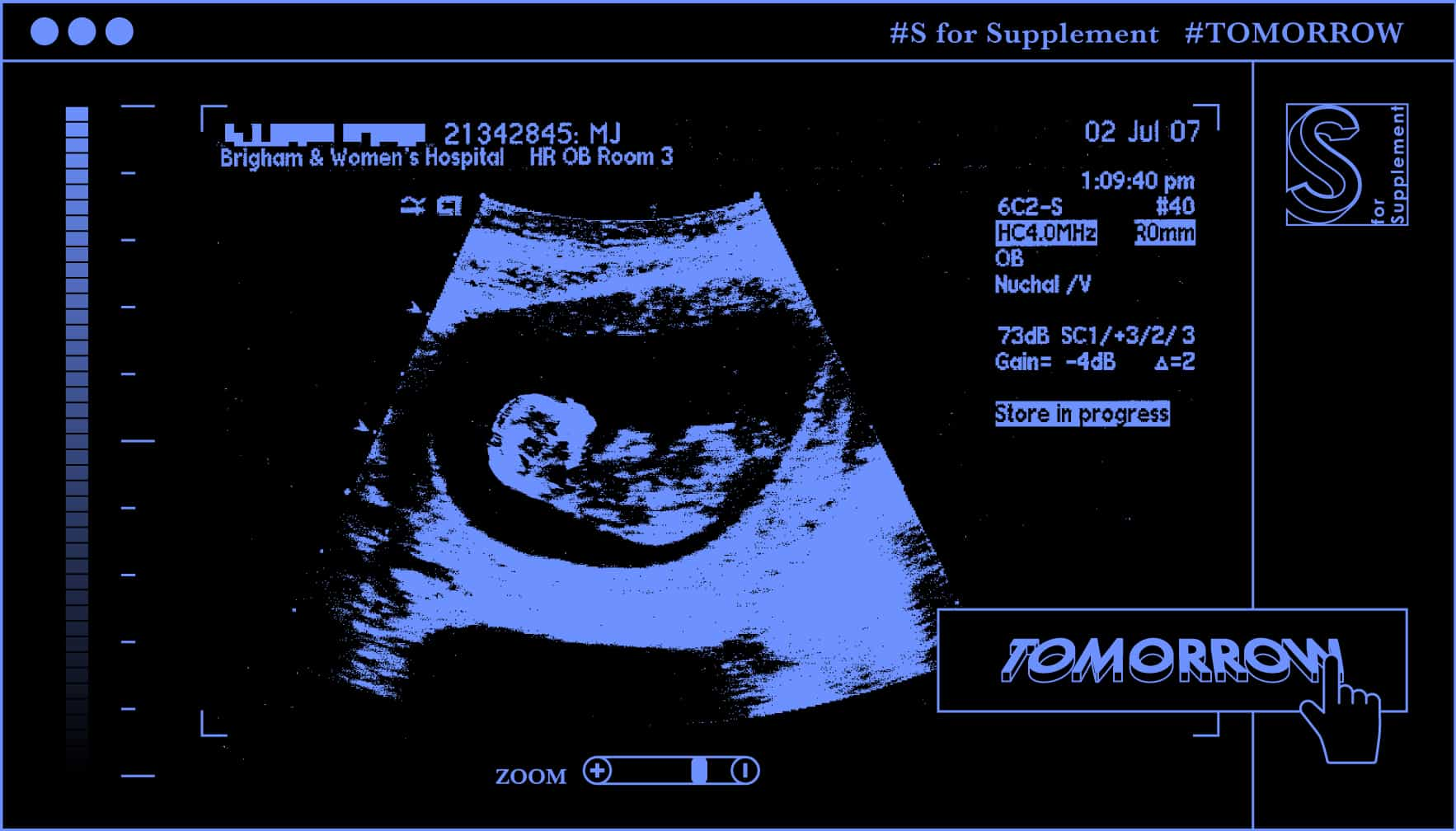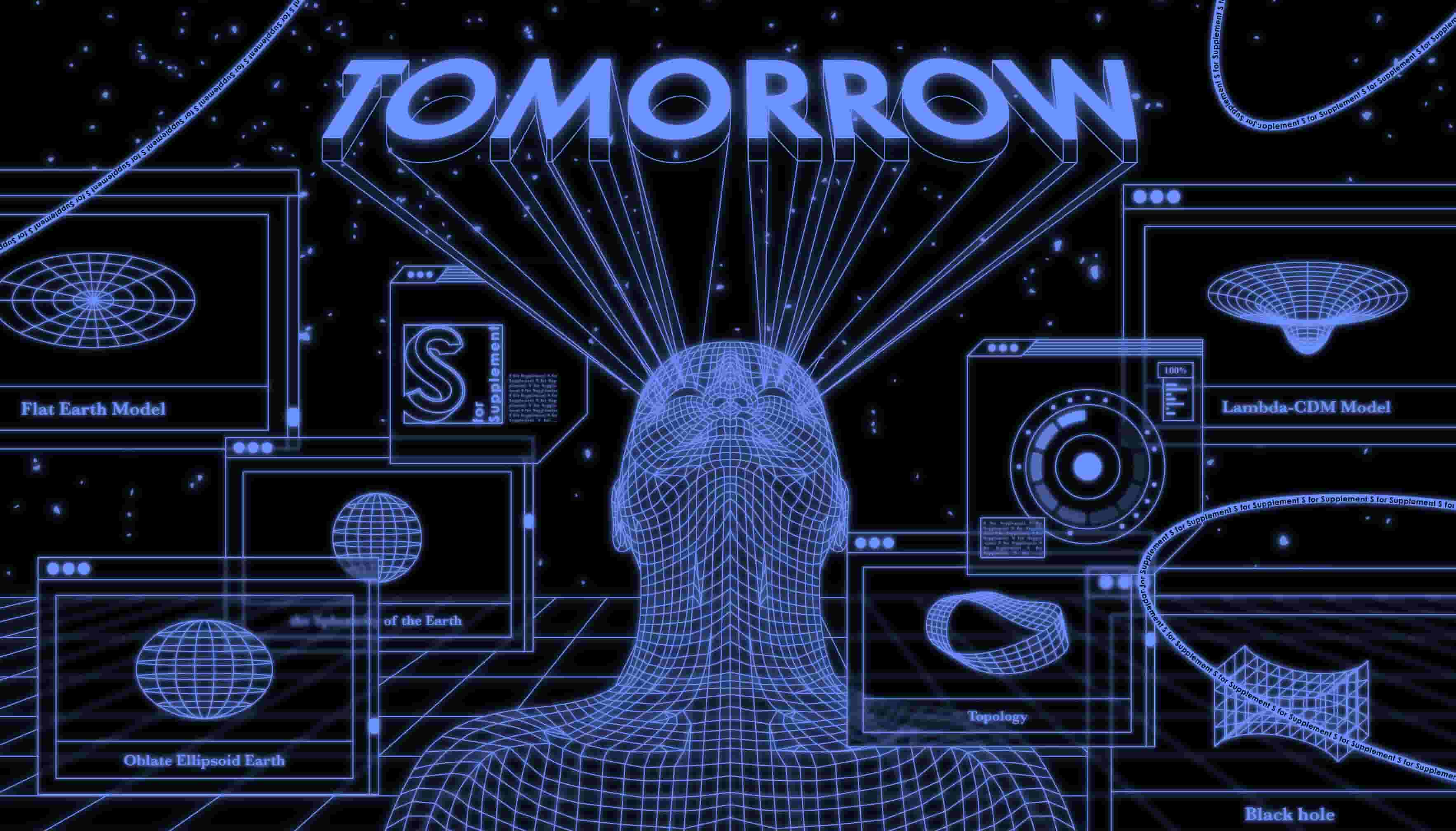一甲子前的懷孕婦女,沒什麼機會接受產檢超音波。
對媽媽來說,除非明顯感覺到胎兒異樣,否則懷孕過程就是順其自然;那時候的父親,因為看不到、接觸不到胎兒,不太清楚寶寶狀況,一般來說也是忙自己的事。醫生也說,懷孕啊,不過就是人生歷程之一,自然就好。
現在,去醫院產檢、照超音波,已是大部分懷孕婦女的共同經驗和回憶。
不少父親因為不想錯過孩子的第一張照片,也想知道孩子是男是女,於是從頭到尾陪著太太做產檢,和胎兒的連結比從前更深切。同時,醫生也不斷叮嚀,要吃好也要睡好,因為母親的健康就是胎兒的健康。
為了一張張超音波照片中正在長大的寶寶,媽媽忙著各種進補,管束自己的慾望,學習各樣課程,還要聽音樂做胎教。萬一透過超音波發現胎兒肢體可能畸形,父母還得仔細想想,是否應該進行人工流產。
超音波技術增加人工流產數量?
這個轉變,正是科技與道德(morality)交纏的示例。
1960 年代成熟的產檢超音波技術,首次把胎兒獨立呈現在我們眼前,把子宮變成背景,彷彿維持胎兒生命的太空艙;身為母親最大的責任,就是保持太空艙運作良好。
過去沒有人可以看到肚子裡的胎兒,若寶寶身體有缺陷,也只有生下來才知道;如今透過超音波,寶寶只要有任何缺陷,都清楚的呈現在每個人面前,再加上性別容易辨識,整體而言,產檢超音波似乎增加了父母面臨「應該墮胎嗎?」道德難題的機會 。

但如果我們就此認為,產檢超音波只會增加道德麻煩,那就錯了。
產檢超音波廣泛使用後 ,墮胎其實沒有比較容易。透過超音波看見胎兒的樣態、五官、動作,會大幅增加「它是個小生命」的感受,讓人工流產變成一個情緒上極度困難的決定。產檢超音波的照片,也讓父親得以「經驗」到胎兒,促使他更積極參與太太懷胎九月的過程,懷孕也因此變得不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人」的事情。雖然醫生越來越常對父母叨唸,但也拜現代醫學之賜,現在胎兒死亡率大幅降低,多數胎兒都能健健康康、順順利利誕生到這個世界來。
所謂道德邊界,是「物」和「人」共同決定的
科技和道德並非兩個互不相干的領域。當科技不斷影響人類的道德決定和行為時,道德就不再是「人」的專屬事務,「物」也參與其中。
在技術哲學(philosophy of technology)裡,這種科技的作用力被稱為「中介」(mediation)──人類一方面在既有的道德框架中設計、選擇、和使用科技,但另一方面,這些道德框架又會因為科技的效果而調整改變。
例如麻醉劑發明以前,人類感受疼痛的能力來自上帝賦予,也是「生而為人」的明證,過度避免疼痛如同剝奪某種權利,不符道德;如今,如果醫生不給病人施打麻醉就逕行開刀,多半會被送進道德懲戒委員會。
科技與道德邊界的模糊,暗示著物與人的「對稱」:人與物一樣的有活力(active)卻又一樣的安靜(inactive),兩者都能發揮影響力,但都不是決定性的。
如果兩者的關係是雙向而非單向的,那麼,在討論科技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時,主流的科技倫理學(ethics of technology)就顯得力有未逮:試圖在人與物之間劃下永恆的紅線,不斷用一種抵禦和捍衛的姿態來指責科技的「越界」,不只很多時候實屬徒勞,更會錯失或漏掉科技帶來的道德好處。
設想如果當時我們以「間接鼓勵墮胎」或「給予醫生掌控孕婦身體的權力」為由,極力叫停產檢超音波技術,那麼負責任的父親、緊密的家庭關係、重男也重女的雙親,很可能都不是今日所見、甚至未曾出現。
倫理迭代: Z 世代新隱私觀
這意味著,想要衡量或預期未來科技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或「道德衝擊」,應該更注重和聚焦在這種「科技」與「道德」的雙重變化。
當 Google Glass 在 2013 年釋出探索者版本時,試用者的評價和討論並非一味指責,反之,他們開始追問:被別人的 Glass 拍到算是失去隱私嗎?我們在公共場合也會被其他人看到甚至記住,不是嗎?Glass 的確紀錄了我的出行路線、購買物品、和會面朋友,但這些有不得洩漏的價值嗎?

另一方面,Google 也開始研擬和提出使用 Glass 的「禮儀守則」,建議在什麼樣場合和狀況下、用什麼樣的方式使用它,才不致讓人覺得被侵犯。透過 Google Glass,設計者和使用者都在重新思考、定義、和協商什麼才是隱私,還有隱私的價值為何。
話說回來,2000 年以後出生的世代,對於隱私並沒有前人的堅持和恐慌。
成長在社群媒體最蓬勃發展的時代,他們多半已經習慣生活在「半公開」的狀態下,用抖音(Tik Tok)、Instagram、Facebook 分享日常活動,展示並塑造自己的身份認同。或許,這樣更符合網路社群平台的原意:網路世界本來就是公共場域,而非私人空間。作為緊緊與「公共」相連的人類,如何行動和互動,並從中成長茁壯,才是這群 Z 世代的關心所在。當許多人還在擔心網路侵犯隱私問題時,他們早已遨遊其中,羽翼豐厚地展翅飛翔。
人類會比 A.I. 遵守道德準則嗎?
人與科技透過互動、不停調整邊界的「道德動態」(moral dynamic),使得主流的科技倫理學窒礙難行、窮於追趕。
自駕車(autonomous car)問題時亦是如此。我們似乎認為自駕車 AI 必須能夠解決「電車難題」(兩個孩子、三個老太太、一位孕婦,應該撞誰?)才能允許上路、廣泛使用──換句話說,主流科技倫理學期望自駕車可以處理倫理問題。
然而,問題在於,面對緊急情況,人類會比自駕車更能做出正確決定嗎?很多時候,駕駛遇到緊急狀況,腦中只有「一片空白」,連決定都無法做。
交通的安全和順暢,有賴遵守法規的駕駛和行人,缺一不可,當駕駛已經換成不會違反行車規則的行車 AI ,卻仍不幸發生車禍,我們可以追問:不道德的肇事者究竟是自駕車還是行人?有沒有可能,當自駕車廣泛使用後,反而能促使某些人更遵守規定,轉化當前「行人最大」卻有時略顯傲慢的態度?
預測科技對社會的影響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預言科技的「倫理衝擊」更是困難,因為我們的倫理標準和判斷會隨著我們跟科技的互動而變化。使用「此刻」的倫理框架,來替可能採用另一種倫理框架的「未來」做決定,不只不公平,更可能間接帶來恐懼、封閉、和敵意。我們需要的,已經不是 ethics of technology,而是 ethics “with” technology。
從原子科學轉到歷史再轉到社會學最後落腳哲學的學術人,想寫動人散文最後總會變成論說文的寫作者,荷蘭湍特(Twente)大學技術哲學博士,個人部落格:blog.hungch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