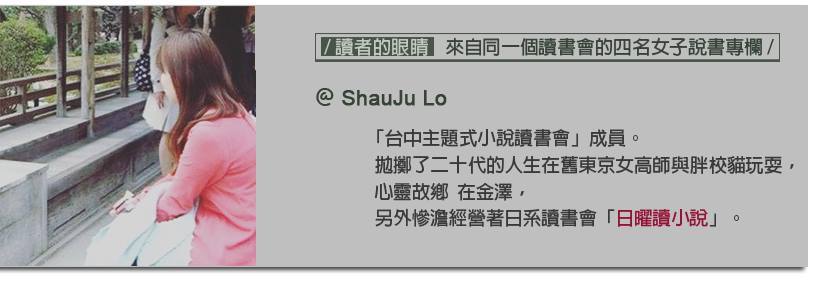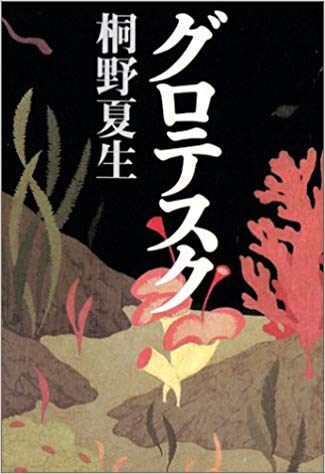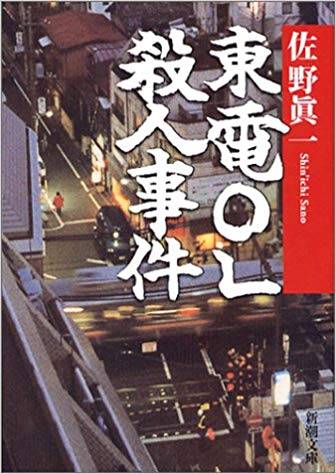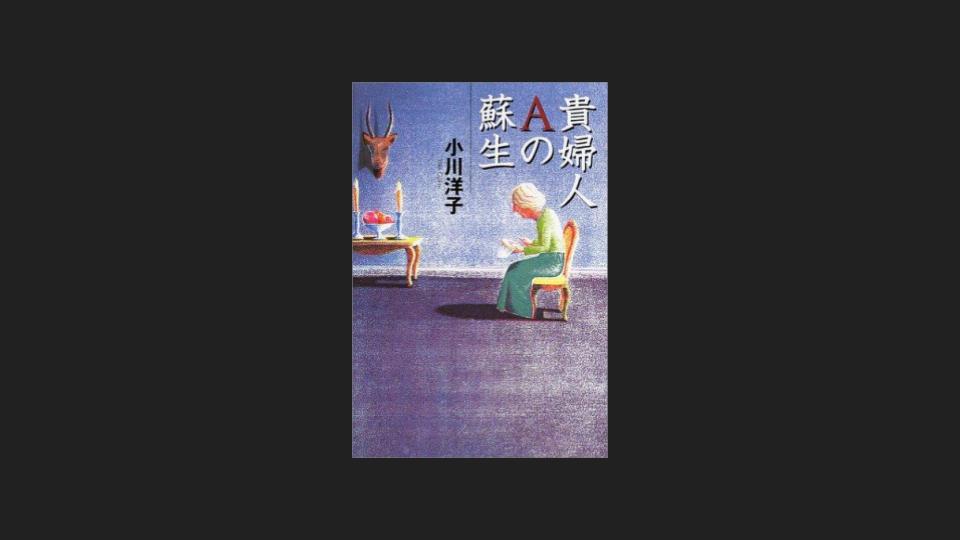關於「少女無敵」
桐野夏生的長篇小說《異常》,情節有些驚悚又帶著獵奇胃口,取材自轟動日本社會的殺人案件,甫推出便受到注目,但究竟寫得好不好則有待討論,放在「少女無敵」主題其實很吃虧。畢竟這個主題的三本選書中,前有谷崎潤一郎的《癡人之愛》(專欄回顧:「少女、娼婦與大文豪──讀《痴人之愛》」),下一回等著接棒的是納博科夫的《蘿莉塔》,《異常》夾在兩本大宗師的代表作中間,立刻顯得遜色。起碼在我心中,這本《異常》實在不能算是桐野夏生最好的作品,然而話又說回來,在「少女無敵」這個主題脈絡裡放進一本《異常》,卻又或許是最適合這部小說的位置。在進入下一回所謂「蘿莉控」的起點、少女幻想的超級大作《蘿莉塔》之前,不妨先透過《異常》這本作品,窺探一下你所不知道的(或許也沒有人真的知道),神秘女子花叢底下的暗影。
桐野夏生《異常》
「我怎麼能不干涉。因為,這會玷污你的靈魂。做這種事是不對的。」「靈魂不會因為賣春就被玷污。」聽到賣春這個字眼,木島氣得聲音顫抖。「那只是你沒發覺。一定會玷污,你的靈魂被玷污了。」(中略)木島啞然凝視著我的臉。他大概做夢也想像不到,我怎麼會連這種事都知道吧。「那的確很可恥,可是沒有玷污靈魂」。「為什麼?」「因為這是勞動的報酬。(略)你身為女性並不是你自己選擇努力得來的。只是湊巧,你天生就是一個美麗的女性而已。利用這一點生活會玷污靈魂。」「我並不是在利用。這跟老師你兼差一樣。」「怎麼會一樣,你的工作是打從根本傷害喜歡你的人耶。這樣以後誰也不會愛你,你也無法愛別人。」這倒是個嶄新的想法。我的身體是我的,照理說不屬於任何人。想愛我的人,就得連我的身體都掌控才甘心嗎?如果愛是如此不自由的東西,那我一輩子都不想嘗試。(中略)「欸,老師。你要不要買我?」——出自「百合子的手記」
《異常》一書取材自轟動日本社會的殺人事件,在桐野夏生開始執筆前,已經有大批報紙新聞爭相報導,還有紀實文學作家展開一連串訪查,並推出了相關書本。打著以女性作家之筆剖析女人私密的小說《異常》,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連載。
通稱「東電 OL 殺人事件」的那件兇殺案件,是這樣子的:一個站在街頭,以低廉價格拉客的低階流鶯,被發現陳屍在一幢老公寓裡。這樁發生在社會底層的常見悲劇原本不該吸引太多注目,但隨後,受害者的身家背景逐漸明朗,強烈的反差立刻引爆騷動。原來受害者不但出身名門大學慶應,家世背景優渥,還是頂尖企業在性別平權運動的腳步下,引進的第一批試驗性總合職女社員,薪資待遇極佳。白天的社會精英,夜晚的街頭妓女。窺探她為何遇害,挖掘(或想像)她為什麼選擇這樣的夜晚差事,一口氣讓整個日本社會狂熱起來。
對於這起事件,臺灣讀者並不陌生的《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一書中,也特別花了兩個章節討論。該書作者上野千鶴子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整理了在一連串騷動中,日本社會如何以男性本位的目光觀看或評論這件事,同時也嘗試理出那個年代的女性,可能共同背負何種困境。書中,上野千鶴子把相關解釋與各種書籍討論整理得非常清楚,並且針對各家盲點多有鋒利的評論,裡面當然也提到了桐野夏生的《異常》。
作家桐野夏生,如同這個年代的日本女性作家,作品量多,常聚焦於描寫過往男性作家的世界裡,少有舞台的女人的掙扎或犯罪心境。如同這方面的翹楚角田光代一樣,她擁有名氣與書迷,作品則稍嫌良莠不齊。我非常喜歡她拿下直木賞的作品《柔嫩的臉頰》,該書描寫一個被生活困住的女人,為尋求出口而投入一段外遇,卻付出慘痛代價——她的小女兒離奇消失,於是她開始了一場漂流,尋找她的女兒,也尋找她自己。相對於此,《異常》面對的評價則複雜多了。
《異常》紮實的上下冊兩本文庫共八百多頁,故事分為七章。其中四章加上最後一小段終章,是無名敘事者「我」的自述。敘述她有一個怪物一般美貌的妹妹百合子,敘述「我」拚命考進的貴族女校如何畸形,敘述學校裡遇見的兩個友人,一個是讓人不忍卒睹的「只要我努力教」派的可悲信徒佐藤和惠,一個是以成績作為生存戰略的溫和女孩美鶴。整個上半冊文庫的場景,幾乎都圍繞在那所名門女校。「我」形容那裡:「要說現實是什麼,就是學生之間的差別待遇。並不是和誰都可以交朋友,社團活動也有分等級,是一個主流和支流之間界限分明的社會。這種現象的主要源頭,當然就是差別意識。」對她們來說,那裡就是現實世界的縮影,直到離開學校後也一直影響著她們。
而交錯在「我」的敘述之間,安排了三個章節的手稿紀錄,分別出自三個角色之手。第一份手稿來自妹妹百合子,她紀錄著自己一生因為超凡外貌,自幼吸引、誘惑男人而後賣春的經歷。另外一章是中籍殺人嫌犯的自白書,裡面詳述了他與自己妹妹的奇異曖昧的關係,還有從中國偏鄉出發,為求生存一路到日本,最終犯案的心路歷程。最後,則是「我」的高中同學——佐藤和惠的賣春日記。佐藤和惠的角色藍本,就是東電 OL 殺人事件的受害者。
清一色第一人稱敘事的寫作手法,構成《異常》的主要和弦。自述或手稿的告白式第一人稱,理當最為坦承,但《異常》裡每個人口中的話都和其他人明顯矛盾。每個人各說各話、無法互相理解地隔絕,或者是出於自保機制而扭曲了現實。這樣的行文特色,除了反映人物心理上的偏執——包括對「美」與「醜」、對「性慾」與「肉體」、對「社會階級」與「自我認同」——之外,或許也和本書題材來源——也就是捕風捉影的八卦新聞性格有關。從頭到尾滿是怨憤與自我欺瞞的敘事者「我」,她使用的對話文體更彷彿在對意圖窺探八卦的讀者透露秘密。而這一份揭秘般的文章特質,或許正是導致《異常》讓上野千鶴子頗有不滿的原因之一。
面對漫長篇幅的《異常》,讀者抱著對「東電 OL 殺人事件」的期待打開書頁,首先讀到的卻是女校階級社會的漫長描寫。少女間彼此的角力,面對霸凌與同儕壓力的獨特生存戰術,其中當然有令人共鳴的精彩描寫,逼迫讀者看見自己可能也不願承認的一面。但反過來看,完全聚焦並刻意強化女校生活的心機與階級的情節,卻似乎又有種說不出的不對勁。敘事者「我」對於美醜的執著,以及後半段和惠化為流鶯的描寫,也讓人有類似感觸。濃厚沈重的險惡人心云云固然是桐野夏生的作品調性,但如同上野千鶴子在書裡寫的,這部作品有些陳述稍嫌陳腐。對於矚目的焦點,也就是受害者動機的解剖是否真的足夠深入?是否迫近了這起事件的真相,或道出了某一份奇妙的女性心理?恐怕也都要打上一個問號。取材自轟動新聞的這部小說,打從連載當初便承受著期待,期待一個女性作家揭露出一些神秘、且不為外人(其實就是男性)知的女人心性。或許滿足讀者、觀眾(不論是書內或書外)的好奇心,從頭到尾都是這本書的主軸之一也說不定。
於是這本書堆了滿滿的險惡人心,推了滿滿的赤裸而不潔的性愛描繪,陰溼沈重的場景與人物讓閱讀本書成為一場不十分愉悅的體驗,也引來獵奇趣味的批評。然而,全書充斥的骯髒、惡意與難堪,卻讓我彷彿感受到藏在文字後面的,桐野夏生的一絲挑釁。整部作品都帶有一份表演味——不論是桐野夏生刻意為之的反諷,或是連作者自己也不禁隨著嗜血媒體起舞的結果。以誇飾、強調的方式,呈現一場演出,演出觀眾期待的所謂「女人」,演出新聞報章裡繪聲繪影追逐的「女人」的形貌。如同日本媒體對於「女作家會如何探求,同為女性的受害者心中那份黑暗面」抱有期望,《異常》誇張且「赤裸裸」的描寫手法,彷彿正面回應這些期待。振筆疾書外界期盼看見的「女人之間的勾心鬥角」、「女人對美的執著」、「女人渴望的性魅力的認可」。為了滿足整的社會的八卦慾望,《異常》彷彿一份虛偽的告密信,揭露讀者期待看見的秘密。不但不寫實,反而還有些超出現實。
回到「少女」這個主題。「少女」之所以特別,在於背後要求的清純、潔淨、無性——唯有觀看者(或往往身兼保護者)擁有對她的性予取予求的特權。「少女」必須清純但性感,同時對自己的性感一無所知。關於這一類的少女想像,不論是上一回的《癡人之愛》也好,下一回的《蘿莉塔》也好,最後的結尾都落在少女幻想的破滅(當然《癡人之愛》的讓治,或許是得其所願也說不定)裡。雖然《異常》一書中,和惠和百合子成為路邊流鶯時,已經年近中年,但整本書從她們的少女時代講起,不論是敘事者「我」、和惠、百合子,還是暗示最後走上類似奧姆真理教團,牽連進恐怖攻擊事件的美鶴(這點當然加深了新聞小說的特質),都彷彿還沒走出少女時代的那間女校。她們面對的困境始終是相仿的。只有美鶴或許最後擁有了一點救贖的希望。
在「少女無敵」這個主題裡,選進桐野夏生的《異常》,為的就是那一份女作家筆下,每一個抱著「惡意」求生的少女的模樣。還有那赤裸到幾乎令人反胃、毫無一絲美化意圖的,關於性的各種描寫。不論是骯髒的環境、難以讓人喜愛的身形與姿態描述,那是沒有一絲浪漫氣息,純粹慾望,甚或意圖性地獸化行為。讀來令人不快,讀來令人不適。做為因為禁忌而成形的性感符號,「少女」,彷彿永遠是被凝視(或被性幻想)的對象。當高階菁英的賣春或者神秘女校花叢,淪為另一種讓社會集體發情的存在,那麼《異常》在吸引關注與窺視目光的同時,也用最暴力最具污染性的文字、手段狠狠地回擊、打翻了這一缸少女幻想的貪婪。像是在嘲笑著那些興趣本位的嗜獵目光:「你想要看少女的性,那我就讓你看個夠、看個飽、看到反胃、看到吐吧。」不論是刻意或偶然,《異常》一書在回應日本社會的窺視期待之餘,彷彿也給予了一個充滿惡意的回擊。